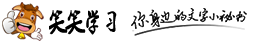欢迎来到98聘
精心挑选《关于网络的演讲稿作文》相关文章文案。(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9-03 12:49

写作核心提示:
以下是一篇关于网络的演讲稿,以及撰写此类演讲稿时应注意的事项:
"演讲稿:拥抱网络,理性前行"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拥抱网络,理性前行”。
网络,这个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它像一把双刃剑,既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也带来了不少挑战。
"首先,网络为我们提供了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 只需动动手指,我们就可以轻松地获取海量的信息,了解世界各地的新闻动态,学习各种知识技能。网络打破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学习、工作、娱乐。
"其次,网络也为我们提供了便捷的沟通方式。" 通过社交媒体、视频通话等工具,我们可以与远方的亲朋好友保持联系,分享彼此的生活点滴。网络让我们的人际交往更加丰富多彩。
"然而,网络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网络信息良莠不齐,虚假信息、网络谣言层出不穷,容易误导人们的判断。过度沉迷网络,也会影响我们的学习和生活。网络成瘾、网络暴力等问题,都值得我们警惕。
"因此,我们应该如何拥抱网络,理性前行呢?"
"第一,要树立正确的网络使用观念。" 我们要认识到网络是一把双刃剑,要善于利用网络的优势,避免网络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二,要提高信息辨别能力。" 面对海量的网络信息,我们要学会甄别信息的
张瑞敏中欧演讲:我眼中的互联网
2014年8月23日,张瑞敏参加了在山东青岛举行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之大师讲堂”,将海尔10年的实践浓缩为1个小时的演讲。
演讲以三个关键词为导向,着重讲到了互联网的三个颠覆,海尔探索的三个试错以及需要直面的三个矛盾。
以下为演讲全文。
张瑞敏中欧演讲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中欧20周年的庆典活动,但是,我绝对不是大师,只是搞企业的。搞企业这么多年,我的体会就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可以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搞企业这么多年,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剩者为王。”今天为什么用“互联网时代管理模式的探索”这个题目?因为过去我们中国企业基本上属于追赶型:改革开放初期学习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TQM),后来学习美国的六西格玛,然后是所有欧美先进的管理模式。尽管到今天为止,可能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管理模式都不奏效了,现在必须去打造新的管理模式。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挑战”就是没有可以照着学习的目标,比如全面质量管理完全照搬日本的,现在照谁的?没了。去年,美国管理学会(AOM)第73届年会在佛罗里达州中部的奥兰多市召开,大会我做演讲。在午餐会时,我第一次感受到,美国很多顶级商学院的教授都在从理论上探讨“互联网时代应该怎么做?”,他们问我在实践中是怎么做的。过去,我们到美国去,他们都是说怎么怎么办就行了。当然,这也是个很大的机遇。而且,现在大家都在探索。我相信,海尔现在的探索是蛮有意义的。今天的演讲,按美国著名的营销顾问西蒙·斯涅克(Simon Sinek)的“黄金圈理论”分为三个小题目: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why);想清楚了之后怎么做(How);最后就是做什么(what),也即具体的落实规划。做好了之后再回到为什么,不断循环往复,日省吾身。为什么要做互联网时代管理模式的探索?因为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每个企业的成功都是时代的产物。如果你不能跟上时代,就会被时代淘汰。处在互联网时代,就只能跟上互联网时代。在传统经济时代所有成功的做法,今天可能都不适用了,所以只能是按照互联网时代的精神和现实来做,必须改变自己。怎么做?就是探索创新,具体就是试错、纠错。最后,做什么?首当其冲的就是直面遇到的所有困难和矛盾,很多悖论。“Why”: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
在海尔的字典里,没有“成功”这两个字。其实,所有企业的成功都只不过是踏上了时代的节拍,踏准了就成功了,正所谓“台风来了猪都会飞”。所以,有的人成功了,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成功。但是,我们是人,不是神,不可能永远踏准时代的节拍,就像冲浪能永远冲在最高峰吗?不可能。所以,问题就变成如何才能真正赶上这个时代的节拍。那些百年企业是如何做到“基业长青”的?我认为,百年企业就是通过“自杀”重生——你不能“自杀”,就会被“他杀”,被时代所“杀”。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DJIA)有一个诞生一百周年的庆典,但能够来参加这个庆典活动的只有美国的GE。所以,只能我们去适应时代,时代不可能适应我们。现在最有说服力的案例就是手机:一开始摩托罗拉是老大,很快诺基亚超越它,后来苹果又超越诺基亚。为什么?时代使然。摩托罗拉是模拟时代的代表,诺基亚则是数码时代的代表,摩托罗拉的被超越在本质上是被数码时代淘汰了,而诺基亚则被互联网时代淘汰了。总之,时代发展太快,谁也抗拒不了时代的发展,只能去顺应它。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为什么?因为流过脚边的水已经不是原来的水,而是新的水。时代也是这样。如果时代改变了,今天成功的模式在明天就不合适了。所以,对我们来讲,怎么踏准时代的节拍非常重要。就现在而言,就是要怎么样踏准互联网时代的节拍。互联网时代颠覆了传统时代的一些理论,尤其是奠定了现代企业管理的基础理论的分工理论。1776年,亚当·斯密在其出版的《国富论》的第一章即以“论分工”为题。斯密举了一个经典例子:一个工人没有受过制针培训,且不熟悉制针使用的机器,无论如何努力,也许他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针。但是,如果把制针分为抽丝、拉直、切断、削尖、磨光、安针头等大约十八道不同工序,每道工序由不同的工人操作,则会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每个工人平均一天课做几千根针。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体系有三位先驱:弗雷德里克·泰勒基于动作研究的“科学管理”;德国人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或他自己所说的官僚制,也即今天常见的金字塔式组织结构;法国人亨利·法约尔提出的关于组织内部的一般管理理论——认为管理有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五大管理职能,以及五大职能要不断再平衡,实质是让五大管理职能不断增减。但是,在互联网时代,这三位先驱的理论都被颠覆了。首先,互联网带来了零距离。德鲁克有句话说,互联网带来了零距离,这是它最大的影响。零距离首先意味着泰勒的科学管理不灵了。为什么?零距离要求从以企业为中心转变为以用户为中心。用户的需求都是个性化的。泰勒的科学管理是大规模制造,现在则要从大规模制造变成大规模定制。其次,去中心化,没有领导。谁是员工的领导?不是他的上级,而是用户,员工和用户之间要直接对话。这就把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颠覆了。为什么美国汽车商没有竞争过丰田?因为美国汽车制造商有14个层级,而丰田要少得多。现在,互联网时代的企业应该是没有什么层级。第三,分布式。所有资源不是在内部,而是在全球,这就颠覆了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为什么一定要在内部来做?为什么不可以吸引全球的资源?加拿大人唐·泰普斯科特和英国人安东尼·威廉姆斯撰写的《维基经济学》有句话说得好,“全球就是你的研发部”。总之,如果还想抱着原来那套不放,是肯定不可能的,时代使你必须要改变。“How”:在商业模式创新中的探索试错
关于探索,我主要讲三点:战略、组织和薪酬。为什么讲这三点?首先,战略和组织对企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美国企业史学家钱德勒有一句话,企业成长取决于两个变量,一个是战略,一个是组织。如果战略和组织不清楚,企业就没法成长。战略是什么?战略不是目标,不是“我要成为全国第一”、“我要做到多少多少万级,多少多少亿级”……成为第一不是战略,能够找出成为第一的路径,这才是战略。今天,怎么找出符合互联网时代要求的路径,这才是战略。战略必须要变,要变成符合互联网时代的要求。战略应该服从于时代,组织从属于战略。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第一,战略服从于时代取决于领导人能否使战略符合时代。如果企业领导都不能做到,底下的人怎么知道往哪走?!第二,战略找准了以后,组织更难了,就像头转向东边了,而身子没有转过去,能走吗?没法走。战略
海尔首先要实现战略的转移,从以企业为中心转移到以用户为中心,具体我们叫“人单合一双赢”战略:“人”是员工,“单”是用户价值。将每个“人”和他的“用户价值”连接起来,其实很难。德鲁克指出,每个企业都要问自己:我的客户是谁?我给客户创造的价值是什么?很多人不上来。不能说做鞋的就是卖给买鞋的。问题是为什么人家要买你的?这是差异化的问题。所以,真正要是找到自己的战略,不是这么简单。海尔几万人,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用户,这个很难。比方说,有很多部门找不到用户,我就在生产线上,我就制造,但是市场上谁要?不知道;财务人员说我就是记账的,只要合规就行了,管你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就在推进这个转变,要把人员先解放出来。在金字塔型结构里,员工是听上级的,上级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但现在,每个员工都要找到自己的用户,要变成创业者,而且可以寻找社会资源来创业。举个例子,“水盒子”,其功能是监控自来水质变化并改造自来水,就是员工从“金字塔”里被解放后创造出来的,最后必须变成一个创业团队,这个团队一共是五个人,自己掏出45万元来入股,当然海尔占大股。不仅如此,他们还找了英国和美国的资源进来,也持有一定的股份,就完全变成一个社会化的企业了。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希望三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在全国创造出一个第一,最引领的目标。在这个前提下,由上级公司回购他们,他们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所有的资源都是找自社会的。企业不需要像过去那样,自上而下给你下达任务,怎么怎么做……这非常复杂。因此,变成一个社会化结构,开放的一流资源都可以满足。海尔有句话,“我的用户我创造,我的‘超值’我分享”。全国的居民,能不能变成你的用户?“我的用户我创造”;“我的‘超值’我分享”,比如说将来企业10倍、15倍回购它,超值他们可以分享。总之,传统的管理要素有三个:管理的主体、管理的客体和管理的手段。管理的主体是管理者,管理的客体被管理者,管理的手段是各种管理方法去控制他。现在海尔的理念是“企业即人,人即企业”。“企业即人”即企业中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创业者,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创客”,企业只是创业平台,让每个人都能够创业。“人即企业”,每个人能够创造非常大的企业,做得越来越大。企业要由管控组织变成创业平台,员工由执行者变为创客。组织
原来的组织,简而言之,就是一个串联的、非常复杂的流程:干一件事有好多不同的内部组织来签字、通过等等,流程非常长。现在,所有的资源围着用户转。原来是研发完了给制造,制造完了给营销,现在都围着用户同时实现。这就是迭代的概念,它和原来的开发模式——“瀑布式开发”完全不一样。研发研究了很多,“流”到制造“台阶”去,制造制造好了“流”到营销“台阶”,营销再“流”到市场上,但是到那个时候行不行?过去我们学习日本。日本式研发是研发出来之后送到市场上的产品必须是完美无缺、无懈可击的,所以时间非常长。现在这种办法不行,必须根据用户的要求马上推出产品,再根据他们的意见来修改。硅谷有句话,“如果你投放市场的第一代产品不能够使你感到羞愧的话,那你应该感到推出得太晚了。”例如,“水盒子”推出去之后,马上就有很多用户感兴趣,同时也进来很多资源,有一个英国的资源进来之后说他可以做得更好,第二代(的体积)是第一代的五分之一。所以,现在不是在家里关起门来自己想,而是要根据用户的需求来做。美国人格哈拉杰达基(Jamshid Gharajedaghi)在《系统思维》中提到,组织转换有三个模式逐渐发展:从无思想的机械模式到单一思想的生物模式,最终变成复杂的多思想的文化模式。“无思想的机械模式”:机械论的观点,时间、背景基本上在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人首先提出机械论,把宇宙看作是一个机器,自己就合理运转;组织都是一个机器,不需要有思想,架构好了就自己运转。所以,在工业化初期,从小作坊变成机械化工厂,从手工织布到自动织布机,效率非常高。“单一思想的生物模式”:很多组织都有机器了,竞争就看谁有思想了,就像一个人,四肢再发达,也要靠大脑。企业也一样,不管做得好坏,就是靠领导;企业的领导人就是救世主,很多企业把希望寄托在领导人身上。“多思想的文化模式”:一个组织是一个社会组织,这个社会组织是整个大的组织当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内部有很多的小组织,每个人就是一个组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关键在于,怎么样把每个人的能力都发挥出来,把每个人变成创业者,而不是因为是企业的一把手,所以说了算,大家都得听我的。薪酬
薪酬太重要了,因为它是企业的一个驱动机制——薪酬怎么做,大家就会往哪个方向走。按照国外的说法,薪酬不应该叫领工资,而应该叫收费——领工资是企业给员工的,是对员工劳动工作时间的报酬;而收费是收用户的价值成果对员工的体现。也就是说,不是应该是企业付费,应该是用户付费。过去,我们请IBM帮助我们做“宽带岗级薪酬”,把整个薪酬定为十级,每一级又分为几等,有点像职务报酬。这种方式不可能把大家的积极性都充分发挥出来。现在,我们自己把它改为“两维点阵表”:横轴基本上是和一般企业一样,我们叫做“企业价值”,就是市场成果。简而言之,就是创造顾客的。其实,顾客和用户不是一个概念,应该分开——“顾客”和企业是一次性交易,我做的产品你买了,你给我付费,我给你产品,然后不再有联系;“用户”不是,用户是我和你永远有交互的,你今天买了,给我提了意见,我不断改进。所以,横轴上基本上是顾客,纵轴上是用户,我们叫网络价值。梅特卡夫定律指出,网络价值与网络规模的平方成正比。网络的规模是什么呢?网络的规模就是网络的节点,和网络连接用户的多少。企业内部应该是一个扁平化的组织,外部则是和市场、用户相连接。连接的用户有多少?有多少能成为你的粉丝?这就是网络的价值。所以,在横轴上的指标,比如利润率,是纵轴的必然结果,二者是因果关系。有些网络企业亏损,但是市值或估值非常高,就是因为它连接了非常多的用户。因此,企业内部考核就是三点:一、迭代,能不能和用户交互,不是关起门来做产品,而是和用户交互出来;二、拐点,梅特卡夫把拐点也叫做转折点,进到转折点就会产生网络效应,它是倍数增长的;三、引领。我们原先从国际化公司引进的360度评价体系也弃用了。当初,我就说可能在中国文化里行不通,因为如果是大家都是同僚,因为关系、人情,最后评价的结果都是差不多。结果表明,真的不行,于是把它改成用户评价。过去,用户评价用了一个很笨的办法,有很多的人专门来收集用户的意见,然后给你评价。比方说,服务人员电话跟踪,物流人员怎么样?但是,总免不了会造假。海尔的物流有9万辆卡车在全国,但是这9万辆卡车当然不是海尔的,每台车的司机和安装工,至少两个人,9万辆车合计至少18万人。有人质疑海尔裁员了,其实这些都不在海尔花名册上,如果算上,光这部分就18万人。他们每天接到的订单是海尔通过信息系统下的,薪酬是海尔根据用户服务的态度、服务的好坏开给他的。但是,海尔怎么知道服务得好还是坏?通过网络。我们有一个“按约送达、超时免单”,规定7点钟送到,超过了货就不要钱了,这个对他是最大的制约。原先,“免单”他自己并不赔钱,而且会相互推诿,现在大家结成利益共同体,罚款自己出,声誉和质量就提高了。为什么阿里巴巴找到我们进行合作?所有做大件物流的好像现在还没有敢做这个承诺的。我们从2012年推出这个承诺,到今天一共送了300多万单货,赔了多少?赔了102笔,赔了万分之零点几。目标:“三化”
最后,海尔在商业模式创新中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三化”:企业平台化、员工创客化、用户个性化。企业平台化是大势所趋,必须这么做。钱德勒在《规模和范围》中分析道,美国、德国、英国是当时世界上工业三强?它们为什么强,因为都有很多大的企业,寡头在控制,通过规模效应和范围经济使得别人没法进来。这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原动力,现在互联网时代原动力是什么?平台。所有企业如果不是做平台,做大有多大作用?零售业,很大的连锁店,一个电商起来就把你冲垮了;工业也是一样,今天做得挺大,但是明天就很难说,3D打印起来之后,我们会怎么样?也许我们不行。总而言之,如果不做平台,肯定不行。平台就是生态圈,如果说平台是自演进,那永远没有边界。简单地说,企业平台化就是使企业一下子让全球的资源都可以为你利用。海尔有句话,“世界是你的人力资源部”。太阳计算机系统公司联合创始人比尔·乔伊质疑科斯定理:“大部分聪明的人实际上都在为他人工作。”想一想,怎么可能把全世界最聪明的人都弄到你的公司?但是,如果我是一个平台,就可以整合全球最聪明的人来服务,当然前提是有用户。员工创客化。这个创客是什么?按照克里斯·安德森写的那本《创客》所说的,创客就是个性化和数字化的结合。过去,我想创造一个东西非常难,但是现在利用互联网,我都可以创造。现在有这个条件了,所以要让员工都可以去成为创客。用户个性化。现在的用户需求千差万别,随时在变,怎么去捕捉它呢?而且,进入到移动时代,就如美国人查克·马丁写的《决胜移动终端》里所说的:他们是“在购物”(always are shopping),不是“去购物”(go shopping),所以企业只能不断和他交互,交互不好马上就会被打倒,因为移动购物时的每一个感受都可以马上成为全球的实时新闻直播。有很多企业垮在这上面,一个不满意发到网上去,马上被冲垮了。当然话说回来了,如果他非常满意,那也不得了。因此,用户个性化已经和过去不是一个概念了。最后,康德有一句话,人是目的,不是工具。无论是谁,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把自己和他人作为工具,因为人自身就是目的。我有一次在欧洲演讲时,底下有人提问说最大的课题就是跨国并购文化的融合问题。我说,其实这个是伪命题。世界各国的文化肯定都不一样,但本质都一样,每个人都希望体现个人的自身价值,如果你把他当成工具,当成生产线上的一个零件,无论哪个国家的人都不会高兴;如果你把他当作目的,体现他的自身价值,怎么都可以。我们兼并了亏损几年的日本三洋,八个月止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日本人是年功序列工资,每个人服从上级——日本文化是儒家文化的延伸,唯尊是从,只要是上级,我就要听你的命令。日本战败之后,美国的麦克阿瑟说了一句话,日本有全世界最优秀的士兵,但是有全世界最糟糕的将军;收购日产的卡洛斯·戈恩也说了一句话,日本有全世界最好的工人,但是有全世界最糟糕的管理者。互联网时代,员工为什么要听上级的?上级不是用户,上级不是市场。总之,不管到哪,人是目的,不是工具,这是非常关键的,这也是海尔在做互联网时代的转型时的一个基本准则。离开了这一条,怎么做,可能都不一定能做出来。“What”:创新探索中需直面的悖论
网络作为舆论平台的基本特征
风评起自清议,流行于汉末魏晋时期。在信息不够畅通的时候,皇帝要想在民间拔擢真正的人才,只能依靠社会舆论。于是针对品德和才能品藻人物既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爱好,也是一项重要的选官办法。风评越好,呼声越高,他的名字被朝廷提及的可能性越大,他就越有希望谋个官职,兼济天下。当然,古代的舆论要比现在文雅,那个时候往往会形成对一个人的综合判断,这种判断凝炼成一两句抽象的、文学性的语句,比如“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傀俄若玉山之将崩”(评嵇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评曹操)。在那个时候,这种看似含糊的的写照就构成了一个人的名誉底座、一种形象品牌得以迅速传播。在由熟人关系网连接起来的乡土社会中,舆论往往比法制更能起到收拾人心、维持秩序的作用,不仅如此,它还大大降低了当权者选人、用人的试错成本,就连朝廷也要忌惮三分。
近代国家凭借高效的交通体系和官僚体系,将公权力深入到社会的每根毛细血管。但舆论仍然蕴藏着深厚的社会力量。尤其是在民主和法治尚不够完善的国家,舆论起到不可或缺的民主监督的作用。只不过,从熟人之间的口耳相传到报刊和公共演讲再到今天的互联网,承载舆论的平台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舆论本身的变化,无论是表达内容还是社会效应。网络作为一种舆论阵地和监督平台,呈现出哪些有趣的特点?又存在哪些难以察觉的隐患?在我看来,网络区别于口头或文字相传的舆论,其最明显的特点当然是丰富性。网络世界最不缺的就是话题,这些话题大到国家政策小到文娱八卦,应有尽有。而且这些话题往往是最新、最全的。只要愿意,每个人都可以以极小的成本获取所有公开的资讯,在这一点上人人平等。我们几乎感觉不到自己与世界的距离,可以说,直到进入网络时代,个人才真正自觉地参与到历史当中。但信息的丰富性同时也带来了超强的流动性。话题很多,但每一个话题也很快被另外的话题淹没。一个社会事件发生并传到你这里,正当你搞清楚来龙去脉,准备深入思考和评论时,话题往往已经远去。所有的思考、辩论到最后几乎都是虎头蛇尾。一个话题从酝酿到消退往往只有一个星期左右。一个星期仅仅够我们了解事件梗概,仅仅够煽动社会情绪,我们只能在走马灯似的热搜榜上疲于奔命,没有精力去反思社会病症、更没有精力去追踪和监督事件后续。一些本应发人深省的事件就这样被裹挟着冲上热搜旋即被迅速淡忘,我们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失去集体反思的重要机会。网络世界的残酷性就在于有价值的、沉重的话题需要和大量肤浅的、口水式的话题同台竞争,来吸引人们的关注。网络作为舆论平台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匿名性,我知道当然不是真的匿名。但是在网络这个舆论池里,网民的发言发生在虚拟世界,而发言结束后他又回到现实世界,这种场域上的割裂使得网民很难意识到自己刚才敲的字已经流向了一个公众的、交互的空间,在他看来就好像看了一页书做了一个不够严肃的批注或笔记一样。这种匿名性使得网络发言的心理成本和准入资格都降低到极致,言论自由和平等也实现到了极致。好处就是我们更有勇气去说话,但坏处也显而易见,那就是极易从言论自由滑向言论的无政府主义,由辩论堕落成网暴。辩论和网暴的区别不在于攻击方向的对错,而在于表达方式和内容本身。舆论是讲道理的,是对事不对人的,它的目的是为了辨别一个道理或原则出来,以为未来类似的事情提供参考。但网暴则是对人不对事的,原始的正义感混杂着粗糙的情绪,全部被毫无顾忌地倾泻出来,施暴者不仅没有伤害别人的负罪感,反而有种替天行道的快感。这已经不是辩论更不是批判了,而是赤裸裸的施虐和犯罪 。刚才说过,舆论具有难以替代的审视或审判功能,它在中国民主不够完善的社会中起到重要的民主监督的代偿作用,但是中国的网民们迟早会惊恐地发现,失速的舆论本身才是现代社会戾气的化粪池。网络的第三个特点是操控性。古代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说法,因为每个人发表言论的平台都是自己的嘴和腿,他跑到哪说到哪,虽然传播范围有限,但是自由,对于政府来说管控难度比较大。所以自古以来,了解舆情是历朝历代政府的重要职责,《诗经》和乐府诗有一大部分都是政府为了了解舆情专门设置采诗官从民间采来的诗歌和民谣。而网络则是一个扁平的平台,每个人的声音都有可能被迅速传播,不受空间限制。但问题就是每个人发表言论基本都在网络这同一个平台。如果有超个体的绝对力量参与进来,那么网络空间就难免会产生曲率。最容易影响舆论平台的绝对力量就是政府和资本,对于这两种力量而言,网络并不只是一个自由的舆论平台,它也可以是一个积极的宣发平台。对于政府而言,他可以借助网络宣传国家政策和政府形象。对于资本而言,它可以利用网络巨大的流量来宣传自己的产品甚至塑造消费理念。网络是自由之地,权力和资本当然也可以参与,但是网络平台并不是天然形成的,也是人为搭建起来的,所以自然会受到两种绝对力量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二位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参与者,而是一定程度上的操控者,而且相比于古代,这两种绝对力量只需要操控网络平台,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调整舆论风向,管控成本远远低于古代。网络作为舆论场最后一个特征是偏差性。一定要注意:网络并不是现实世界如实的反映。西方在400年前就高呼“启蒙”,中国也是从100年前就喊出“开启民智”。但在任何舆论场中——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发言成本如此低廉的网络世界,沉默的永远是大多数。有的人没有能力组织自己的想法,有的人没有兴趣参与舆论,有的人则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和表达。能够清晰表达出自己意见的永远是少数人,能够让自己的声音被别人听到的更是凤毛麟角。人类文明史已经五千年了,但时至今日,思考和表达仍然是一个奢侈品。旁观者、倾听者——这才是舆论场中最大的基数。要想了解这个世界,你只能深入群众,除此别无捷径可走。不过我仍然坚信那句话:潮退之时,自然会发现谁在裸泳。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了不起的西西弗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