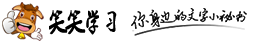欢迎来到98聘
写一篇《我的家乡作文50字》小技巧(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10-26 13:41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50字的关于家乡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字数限制":严格控制字数在50字以内,避免超字。 2. "核心内容":明确作文的核心内容,如家乡的特色、你的感受等。 3. "简洁明了":用简洁的语言表达,避免冗长和复杂的句子。 4. "情感真挚":表达对家乡的真实情感,让读者感受到你的热爱和思念。 5. "结构完整":确保作文有开头、中间和结尾,结构完整。
以下是一个示例:
我的家乡是一个美丽的小镇,有清澈的河流和绿树成荫的街道。每当夜幕降临,家家户户的灯火通明,温馨而宁静。我深爱着我的家乡,这里是我成长的摇篮。
我50岁回到家乡,才知那棵老槐树下藏着父亲未言的诺言
车子停在村口,再往里就开不进去了。
路被岁月啃得坑坑洼洼,像一张老人干瘪的脸。
我下了车,关门的声音在寂静的午后,显得格外突兀,像一块石头砸进了深潭里。
司机探出头,问我,真就送到这儿?
我点点头,递给他一张钞票,说,不用找了。
他瞅了瞅这荒凉的村口,又瞅了瞅我这一身与这里格格不入的西装,眼神里带着点同情,或者说,是看傻子一样的怜悯。
车走了,卷起一阵黄土,呛得我咳嗽起来。
土腥味里,夹杂着一种腐烂的草木气,还有……一种久违的,被我遗忘了三十年的味道。
是槐花的味道。
虽然已经过了季节,但那股子淡淡的、若有若无的甜香,还是固执地钻进了我的鼻子里。
它像一把生了锈的钥匙,猛地一下,捅开我记忆的锁。
我站在那儿,一时竟忘了迈步。
五十岁了。
我在镜子里看过自己,眼角有了细密的纹路,头发也开始不听话地冒出银丝。在城市里,在那个被玻璃和钢筋水泥包裹起来的世界里,我是一个还算成功的商人,别人叫我“总”。
可站在这儿,我什么都不是。
我只是一个离家三十年的,胆怯的儿子。
脚下的皮鞋,踩在松软的土路上,发出一种沉闷的、不情愿的声响。
我一步一步,朝记忆里的那个方向走。
路两边的老房子,大多都塌了,墙壁上爬满了野藤,黑洞洞的窗口像一只只窥探的眼睛。
偶尔有一两户还住着人,门口坐着的老人,眼神浑浊地看着我这个陌生人,像看一棵从没见过的树。
他们不认识我了。
我也快不认识这里了。
但那棵老槐树,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它就立在我家老屋的院子门口,比我记忆里更苍老,更巨大。
树干粗壮得像一头沉默的巨兽,皮肤是深褐色的,布满了沟壑,有些地方的树皮已经脱落,露出里面苍白的木质。
繁密的枝叶遮天蔽日,在地上投下一大片浓郁的阴凉。
风一吹,满树的叶子沙沙作响,像是在低声诉说着什么。
我站在这棵树下,感觉自己一下子变小了。
回到了那个穿着开裆裤,整天在树下打滚的年纪。
父亲就常常坐在这棵树下,靠着树干,手里拿着一杆长长的旱烟,吧嗒吧嗒地抽着。
烟雾缭绕,我看不清他的脸。
其实,就算没有烟雾,我也很少能看清他的脸。
他总是不苟言笑,眉头像是用刻刀刻上去的,永远拧着。
他很少跟我说话。
我们之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大概就是他吼我的:“滚回来吃饭!”
声音粗粝,像砂纸磨过木头。
我怕他。
从小就怕。
他的手很大,很粗糙,手掌上全是老茧,摸在脸上,像被锉刀刮过一样。
我小时候调皮,没少挨那双手揍。
屁股上火辣辣的疼,是我童年里最深刻的触觉记忆。
所以,我拼了命地想逃离。
逃离这个小山村,逃离那间昏暗的老屋,逃离他那双永远沉默却又充满压迫感的眼睛。
十八岁那年,我考上了大学,是村里第一个。
走的那天,他还是没说什么话。
只是默默地帮我把行李扛到村口,塞给我一沓被汗水浸得有些潮湿的钱。
钱是零零碎碎的,一块的,五块的,十块的。
我能想象出,他是怎么一张一张,从那些卖掉粮食、卖掉家里老母鸡的钱里,攒出来的。
我没敢看他的眼睛。
我怕看到不舍,更怕看到我一直以为的,那种如释重负的冷漠。
我头也不回地上了车。
车开动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他像一尊雕像一样,还站在那棵老槐树下。
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和那棵树融为了一体。
这一走,就是三十年。
三十年里,我回去的次数,屈指可数。
一开始是学业忙,后来是工作忙,再后来,是生意忙,家庭忙。
总有忙不完的理由。
其实我知道,那都是借口。
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电话里,永远是那几句。
“嗯。”
“知道了。”
“钱够用。”
“挺好的。”
沉默,永远是沉默。
像一堵看不见的墙,横在我们父子之间。
母亲还在的时候,她会是我们的传声筒。
“你爸昨天还念叨你,说天冷了,让你多穿点。”
“你爸给你晒了你最爱吃的干豆角,让我给你寄过去。”
可我听着,只觉得那是一个模糊的、符号化的“父亲”,跟我没有太多真实的连接。
母亲走了。
几年前,在一个很平常的春天。
我赶回去的时候,她已经闭上了眼睛。
葬礼上,父亲一夜之间,好像又老了十岁。
他的背更驼了,像一张被拉满了的弓,再也直不起来。
他还是没怎么说话,只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灵堂的角落里,抽着旱烟。
烟雾比以前更浓了。
我处理完后事,公司有急事,待了三天就匆匆走了。
临走前,我塞给他一张卡,里面有几十万。
我说,爸,想吃什么就买,别省着。
他没接,只是摆了摆手,含混不清地说了句什么。
我没听清。
或者说,我没想去听清。
我逃也似的离开了。
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的联系,就只剩下每个月我打到那张卡里的钱,和偶尔接通的,只有沉默的电话。
直到半年前,邻居三叔打来电话。
他说,你爸,走了。
走的时候,很安详。
就坐在那棵老槐树下,手里还捏着那杆冰凉的旱烟。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甚至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买的机票,怎么回的家。
我只记得,当我再次站到那座老屋前时,那棵老槐树下,空了。
那个沉默的、固执的身影,再也不会出现在那里了。
我像个提线木偶一样,办完了所有的丧事。
没有眼泪。
一滴都没有。
我以为,我的心,早就在三十年的城市风霜里,变得坚硬如铁了。
可为什么,现在,站在这棵树下,我的眼睛会这么酸?
酸得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蛰了一下。
我伸出手,轻轻触摸着粗糙的树干。
冰凉的,坚硬的。
就像父亲的手。
我绕着树干走了一圈,脚下踩着厚厚的落叶,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
我看到树根底下,有一块地方的土,颜色似乎比别处要新一些。
像是……被人翻动过。
一个荒唐的念头,毫无征兆地冒了出来。
我被自己这个念头吓了一跳。
怎么可能?
我摇了摇头,想把这个可笑的想法甩出去。
可它就像一颗种子,一旦落进脑子里,就开始疯狂地生根发芽。
我鬼使神差地走回老屋。
屋子里空荡荡的,蒙着一层厚厚的灰。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尘土和霉味混合在一起的奇怪气味。
阳光从破了洞的窗户纸里照进来,在空气中切割出一条条光柱,无数的尘埃在光柱里飞舞。
一切都还保持着父亲在世时的样子。
那张他睡了几十年的硬板床,床头的墙上,还贴着我小时候得的奖状,早已泛黄卷边。
桌子上,摆着一个相框。
是家里唯一的一张全家福。
照片里,我大概七八岁,咧着嘴笑,缺了一颗门牙。
母亲温柔地抱着我。
父亲站在我们身后,表情一如既往地严肃,但眼神里,似乎有那么一丝……我从未读懂过的东西。
我拿起相框,用袖子擦去上面的灰尘。
照片的玻璃后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相框的背板。
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条,掉了出来。
纸很旧了,是那种小学生用的作业本纸,上面的字,是用铅笔写的,歪歪扭扭,是我的笔迹。
“我的愿望:长大后,要当一个木匠,像爷爷一样,做出世界上最好看的木鸟。”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攥住了。
疼得我喘不过气来。
木匠。
爷爷是个木匠,十里八乡都有名。
他会做很漂亮的桌椅板凳,会做精巧的梳妆盒,更会做活灵活现的木鸟。
我小时候,最喜欢待在他的木工房里。
空气里永远飘着好闻的木头香气。
锯子“滋啦滋啦”地响,刨花像卷曲的浪花一样飞溅出来。
爷爷的手,像有魔法一样,能把一块块呆板的木头,变成有生命的东西。
他给我做过很多木鸟。
有的站在枝头唱歌,有的张开翅膀要飞翔。
我把它们当成最宝贵的玩具。
我也学着他的样子,拿着小刀,在木头上乱刻。
爷爷总会摸着我的头,笑着说,我们家小远,有天赋。
可父亲,却极力反对。
我第一次跟他正面冲突,就是因为这件事。
那天,我拿着自己刻的第一只像模像样的木鸟,兴冲冲地拿给他看。
他看了一眼,一把夺过去,狠狠地摔在地上。
木鸟的翅身,摔成了两半。
“不准你弄这些没用的东西!”他冲我咆哮,眼睛瞪得像铜铃,“当木匠有什么出息?你爷爷一辈子累死累活,换来了什么?一身的病!”
“我就是要当木匠!”我哭着冲他喊。
“你敢!”
他扬起了手。
那是我第一次,没有因为害怕而退缩。
我梗着脖子,倔强地看着他。
他的巴掌,最终还是没有落下来。
他只是把地上的碎木块,一脚踩得更碎,然后转身进了屋,再也没出来。
从那天起,我们之间的墙,更高了,也更厚了。
我不再碰那些木头和刻刀。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
我要考出去,我要离开他,我要去一个他再也管不到我的地方。
我做到了。
我以为我赢了。
可现在,捏着这张泛黄的纸条,我只觉得自己输得一败涂地。
我把纸条重新折好,揣进怀里,它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着我的胸口。
我冲出屋子,在墙角的杂物堆里,找到了一把生了锈的铁锹。
我走到那棵老槐树下。
就是那块新土。
我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槐花的余香,似乎更浓了。
我开始挖。
铁锹铲进土里,发出沉闷的“噗嗤”声。
泥土很湿润,翻出来,带着一股清新的腥气。
我从没干过这种活。
我的手,习惯了签文件,敲键盘,握酒杯。
铁锹的木柄,磨得我手心生疼。
很快,就起了水泡。
水泡被磨破了,钻心地疼。
可我停不下来。
我像疯了一样,机械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
挖,铲,扔。
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来,滴进眼睛里,又涩又疼。
我不知道挖了多久。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月亮升起来了,清冷的月光,透过槐树的枝叶,洒下斑驳的,像碎银子一样的光影。
“当”的一声。
铁锹好像碰到了什么硬东西。
我的心,猛地一跳。
我扔掉铁锹,跪在地上,用手去刨。
指甲缝里,塞满了湿冷的泥土。
一个四四方方的,用油布包裹着的东西,露了出来。
我的手,在发抖。
抖得厉害。
我小心翼翼地,把那个东西从土里捧出来。
很沉。
我解开外面缠着的麻绳,一层一层地剥开油布。
油布已经有些腐朽了,但包裹得很严实,里面的东西,没有受到丝毫的潮气。
是一个木盒子。
盒子没有上锁。
我颤抖着,打开了盒盖。
那一瞬间,我的呼吸,停滞了。
盒子里,静静地躺着一只木鸟。
不,那不是一只简单的木鸟。
那是一件艺术品。
它通体是用一整块金丝楠木雕成的,木质细腻,在月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
鸟的羽毛,根根分明,每一根都雕刻得无比精细,仿佛能随风颤动。
它的姿态,是展翅欲飞的。
头微微昂起,眼神锐利而又充满渴望,仿佛下一秒,就要挣脱这木头的束缚,冲向天际。
我见过很多名贵的艺术品,见过很多大师的杰作。
但没有一件,能像眼前这只木鸟一样,让我感到如此震撼。
它是有生命的。
我能感受到,雕刻它的人,把自己的灵魂,都刻进了这块木头里。
我伸出手,想去触摸它,又怕自己的粗鲁,会惊扰了它。
我的指尖,轻轻地,落在了鸟的翅膀上。
温润,光滑。
我能感觉到,指尖下,那流畅的,充满力量的线条。
这是……谁做的?
爷爷去世很多年了。
村子里,也再没有手艺这么好的木匠了。
难道是……
一个我不敢相信的念头,像闪电一样,劈中了我的大脑。
我把木鸟从盒子里拿出来。
在它的下面,还有一封信。
信封已经泛黄,上面没有写字。
我抽出里面的信纸。
信纸是那种最便宜的草纸,很粗糙。
上面的字,是用钢笔写的,笔迹很重,有些字,甚至把纸都划破了。
那是我再熟悉不过的,父亲的笔迹。
歪歪扭扭,像个小学生。
他没什么文化,勉强认识几个字。
我从来没想过,他会写信。
我的眼睛,像被蒙上了一层水雾,字迹开始变得模糊。
我用力地眨了眨眼,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下去。
“远儿: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大概已经不在了。
别难过。
人老了,总有这一天。
这辈子,爸对不住你。
爸是个没本事的男人,嘴笨,也不会说话,只会发脾气。
我知道,你从小就怨我。
怨我打你,怨我不让你学木匠活。
其实,爸不是不让你学。
你爷爷的手艺,十里八乡,谁不夸?
可他到头来,得到了什么?
累了一辈子,一身的病痛。
冬天手上的冻疮,烂得能看见骨头。
夏天被木屑扎了,发炎流脓。
我怕啊。
我怕你也走这条老路。
我不想让你跟我一样,一辈子待在这穷山沟里,跟泥土打交道。
我想让你走出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吃好的,穿好的,不用再受苦。
所以,我逼你读书。
你摔了书包,说不想念了,我揍你。
其实,我的心,比你还疼。
你考上大学那天,我一个人,跑到后山,大哭了一场。
我高兴啊。
我的儿子,有出息了。
你走了以后,这个家,就空了。
你妈天天念叨你。
我也想你。
可我不知道跟你说啥。
拿起电话,就变成了‘嗯’‘啊’。
我恨自己这张笨嘴。
你妈走了以后,我一个人,更不知道该干啥了。
白天,我就坐在这棵槐树下。
晚上,我就睡不着。
我就想起了你小时候,说要当个木匠。
我就把 你爷爷留下的那些工具,都翻了出来。
我开始学着做。
一开始,做得很难看,四不像。
手也被刀子划得到处是口子。
可我停不下来。
我好像,只有在做这个的时候,才觉得,离你近一点。
我花了整整五年。
才做出了这只鸟。
我找了村里最好的木头。
我想,我的儿子,他要飞,就要飞得最高,最远。
就像这只鸟一样。
我把它埋在树下。
我想,也许有一天,你会回来。
也许,你会发现它。
也许,你看到它,就能明白,爸……不是不爱你。
只是,爱的方式,太笨了。
远儿,别怪爸。
如果有下辈子,爸一定,好好跟你说话。”
信,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像决了堤的洪水,汹涌而出。
我抱着那只木鸟,跪在地上,嚎啕大哭。
哭得像个迷路的孩子。
三十年的委屈,三十年的隔阂,三十年的怨恨,在这一刻,土崩瓦解。
我以为他不懂我。
我以为他看不起我的梦想。
我以为他冷漠,无情。
原来,他什么都懂。
他只是用他那笨拙的、沉默的方式,爱着我。
他把我的梦想,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
他用他那双被农活磨得粗糙不堪的手,花了五年的时间,为我雕刻出了一个飞翔的梦。
而我呢?
我给了他什么?
冰冷的钱,和更冰冷的沉默。
我甚至,没有在他生前,好好地叫他一声“爸”。
我甚至,没有在他临终前,陪在他身边。
他走的时候,该有多孤独?
他坐在那棵老槐树下,手里捏着冰凉的旱烟,是不是还在等我回来?
是不是还在想,那个不孝的儿子,什么时候,才能明白他的心?
“爸……”
我哽咽着,对着空无一人的院子,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
声音在夜色里,传出很远,又被风吹散。
没有人回应。
只有槐树的叶子,在沙沙作响,像一声声温柔的叹息。
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
直到月亮,挂上了中天。
直到我的眼泪,流干了。
我站起身,把那个空了的木盒子,和那封信,重新放回坑里,用土埋好。
我捧着那只木鸟,走回了老屋。
我点亮了那盏昏黄的油灯。
灯光下,我仔仔细细地看着手里的木鸟。
我发现,在鸟的底座,还刻着一行很小很小的字。
字刻得很浅,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赠吾儿,任高飞。”
我的心,又一次被狠狠地刺痛了。
任高飞。
他放手让我飞翔,却一个人,默默地承受了所有的孤独和牵挂。
他像那棵老槐树一样,扎根在这里,用他全部的生命,为我撑起一片可以远航的天空。
那一夜,我没有睡。
我就坐在那张硬板床上,抱着那只木鸟,坐了一整夜。
我好像,要把这三十年亏欠的陪伴,都补回来。
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给公司的助理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接下来一个月,所有的事情,都由他处理。
我要休假。
挂了电话,我走出了老屋。
朝阳的光,给整个村子,都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
我走到院子角落里,那个早已废弃的,爷爷曾经的木工房。
推开门,一股浓郁的木头和灰尘的味道,扑面而来。
里面堆满了各种木料和工具,上面都落了厚厚的一层灰。
我看到,靠墙的木架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套崭新的雕刻刀。
刀刃在晨光里,闪着寒光。
旁边,还有一堆雕刻失败的,奇形怪状的木鸟。
有的断了翅膀,有的歪了脑袋。
我可以想象出,一个佝偻着背的老人,在这间昏暗的小屋里,就着微弱的灯光,一次又一次,笨拙地,固执地,雕刻着。
他的手上,该添了多少新的伤口?
他的眼睛,该花了多少心血?
我走过去,拿起一把刻刀。
刀柄上,还有着温润的触感。
我拿起一块木头。
学着记忆里,爷爷的样子。
也学着,我想象中,父亲的样子。
我开始雕刻。
我的动作很生疏,很不熟练。
第一刀下去,就划破了手指。
鲜红的血,一下子涌了出来。
我把手指含在嘴里,那股铁锈般的腥甜,让我无比清醒。
我没有停。
我继续刻。
一刀,一刀,又一刀。
木屑纷飞。
阳光照在我的身上。
我好像,看到了很多年前,那个蹲在爷爷身边,满脸好奇的小男孩。
我也好像,看到了几年前,那个孤独地坐在这里,为儿子雕刻梦想的,沉默的父亲。
我们三代人的身影,在这一刻,仿佛重叠在了一起。
血脉,传承,爱。
这些我曾经嗤之以鼻的东西,在这一刻,变得无比清晰,无比滚烫。
我在老屋,住了一个月。
我没有再穿那身笔挺的西装。
我换上了父亲留下的,洗得发白的粗布衣裳。
我每天,除了简单的吃饭,就是待在那间木工房里。
我把那些工具,一件一件,擦拭干净。
我把那些木料,分门别类,整理好。
然后,我就雕刻。
我不知道自己想刻什么。
我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和我的父亲,和我的过去,进行一场迟到了三十年的对话。
我的手上,布满了伤口和老茧。
我的心,却前所未有的,平静。
我不再是那个在商场上,需要戴着面具,说着言不由衷的话的“总”。
我只是一个儿子。
一个正在学习,如何去理解和爱自己父亲的,笨拙的儿子。
一个月后,我离开了村子。
走的时候,我带走了那只父亲为我雕刻的木鸟。
我也带走了,我自己雕刻的第一件作品。
那是一只很丑的小鸟,翅膀一边大一边小,眼睛也刻歪了。
但我把它,和父亲的那只,放在了一起。
我把它们,摆在了我城市里,那个豪华的办公室里,最显眼的位置。
很多人问我,那是什么。
那么贵重的金丝楠木艺术品旁边,怎么会放一个那么粗糙的东西。
我总是笑着,不。
他们不会懂。
那只完美的木鸟,是父亲对我深沉的爱,和无言的期盼。
而这只丑陋的木鸟,是我对他的,迟到的回应,和永远的忏悔。
从那以后,我每个月,都会回一次老家。
我会去那棵老槐树下,坐一坐。
跟他说说我最近的生活,我的烦恼,我的快乐。
虽然,他再也不会我。
但我知道,他听得到。
他的爱,就像这棵老槐树的根,早已深深地,扎进了我的生命里。
无论我飞得多高,多远。
这里,永远是我的根。
我开始学着,放慢自己的脚步。
我不再为了生意,去参加那些无聊的酒局。
我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我的家人,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今年十五岁,正处在叛逆期。
他喜欢打游戏,喜欢说一些我听不懂的火星文。
我们之间,也像曾经的我跟父亲一样,有很多的隔阂。
以前,我只会粗暴地没收他的手机,冲他发火。
现在,我会试着,坐下来,听听他的想法。
我会笨拙地,学着玩他喜欢的游戏。
虽然,我总是被他嘲笑“菜”。
有一天晚上,他半夜还在房间里打游戏。
我推开门,没有像往常一样发火。
我只是给他,端去了一杯热牛奶。
他愣住了,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惊讶。
“爸,你……”
我摸了摸他的头,说:“早点睡,别太累了。”
我转身离开的时候,听到他在身后,用很小的声音,说了一句:“谢谢爸。”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湿了。
我突然明白了。
爱,从来都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
它不需要华丽的语言,也不需要贵重的礼物。
它只是,一杯深夜里的热牛奶。
它只是,一句笨拙的,却发自内心的关心。
它只是,一只藏在老槐树下,沉默了许多年,却依然闪着光的,木鸟。
父亲,谢谢你。
谢谢你用你的一生,教会了我,如何去爱。
虽然,这堂课,我迟到了三十年。
但还好,我终于,学会了。
现在,我的办公室里,摆着三只木鸟。
一只,是爷爷留下的,古朴而充满智慧。
一只,是父亲雕刻的,深沉而充满力量。
还有一只,是我和儿子,一起完成的。
它歪歪扭扭,甚至有些可笑。
但它的翅膀上,刻着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每当阳光照进来,三只鸟的影子,会投在墙上。
它们仿佛在告诉我,生命,就是一场爱的接力。
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
永不停歇。
而我,会带着这份沉甸甸的爱,继续往前走。
飞向,更高,更远的天空。
我知道,无论我飞到哪里,回头看,那棵老槐树,那个沉默的父亲,永远都在那里,看着我。
他的目光,就是我心里,最温暖的光。
美文丨我的故乡我的根
文/吴巧玲
有一个地方,总让我牵挂和眷恋,是我每有闲暇便想回归的去处,那就是我出生的故乡——长峪铺。
“从前我们穷山窝,山高水冷石头多,如今开辟了大寨田啦,山坡上种起了矮子禾哇。依儿哟依儿哟……”小时候听到的这首常德丝弦,总觉得就是描绘长峪铺的。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留存着太多关于长峪铺感天动地的故事,有关于改土的、关于办学的、关于缺水的、关于乡情的……
“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不是等来的要来的。”这是母亲黄炳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母亲就是长峪铺大队(现在叫“村”)的“领头羊”,带领乡亲们开山凿岩,战天斗地。
为将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地”变成“三保地”,乡亲们不向恶劣的自然条件低头,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想尽一切办法找土造地。还记得为了挖出自家房屋里的熟土填充到公家地里,乡亲们将家具都腾挪到外面禾场上,一切为公,无怨无悔;还记得外公常带着童年的我上山,在石缝里一点一点地往外掏黑土;有的人为了掏石缝里的黑土,指尖都抓破了流血了……因了这些童年记忆,以致于成年后第一次读到艾青的那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一下子就能触痛我的内心。
七、八十年代的长峪铺学校办得红火,两层火砖楼的中学部是靠师生们肩挑背扛,齐心协力建成的,加上几幢平房小学,颇具规模。那时方圆几个大队的学生都来求学,有的年级还有两个班,校舍不够,部分小学班就安排到学校的周边农家或搭建简易校舍。记得那时的师资队伍也很厉害,连慈利县一中有的优秀老师都被“挖”来长峪铺教书,学生也很多,一派兴隆景象。
我的小学三年级是在学校旁边王德信家的堂屋读完的,四、五年级是在花家凸山顶两间茅草房读完的,也就是现在的花果山,原是一个乱石岗,后来乡亲们硬是将一个个大石开凿,一担担砂土从山下六公里外的溇江边挑上山,改造成了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梯田。我上花家凸读书时大约十岁,一开始登山喘粗气,后来习惯了,上坡如履平地,下山一阵风。记得坐在低矮的教室里,看着外面梯田上美丽女知青快乐劳动的身影,那时的天空是那么蓝,那时的人脸上笑容是那么纯真……这些画面构成我人生最初的风景。
我六岁启蒙时是在学校本部读书,走到龙虎天坑旁边,便要横过干溪沟沿岸走一段。当时的干溪沟,每逢下大雨,便山洪奔涌,外公担心我被山洪冲走,常用背篓背我上学。也记得外婆曾带我到沟底捡拾各种形状的鹅卵石当玩具。后来乡亲们在沟上搭建拱桥,改造良田,干溪沟两岸堆满的石头掩盖了小路,我和小伙伴们练就了在石头上跳跃前行的本领,锻炼了平衡力。也有石头不稳,失重摔倒的时候,但正是那跌跌撞撞的童年生活磨砺了我的意志。那时干溪沟两边都回响着叮叮当当打钢钎的声音,一片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一般都是由女人掌钢钎,男人则高高抡起大锤狠劲砸下,女人的手掌经常会震起血泡。幼小的我常站在路边呆望着他们打钢钎,非常担心大锤砸伤女人的手,好在从未看到这样的情形,于是便暗暗敬佩这些大人们有本事!这支队伍里,有本大队的农民,有下放的知识青年。再后来,又来了增援队伍,那是来自全县的团委书记和民兵营长,以及各大队社员,他们在县委发出“远学大寨,近学长峪铺”的倡导下,都先后加入了长峪铺改天换地的进程。也记不清过了多久,干溪沟拱桥建成了,上面铺土了,一层层的良田错落有致,好气派!大人们再也不用担心孩子们上学被山洪冲走了,实现了“上面种地,下面跑水,打起仗来做战备”的美好愿景。
那时的人们对党和人民的情怀,都体现在一言一行中。记得母亲有次无意中说起,她为搞“两季三熟”旱粮试验田,长期蹲点住在中心生产队。有天晚上,一觉醒来,但见皓月当空,大地透亮,她披衣起床到生产队麦田又割了几垅麦子,内心充满着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总有使不完的劲。
长峪铺,就这样在人们不懈的拼搏中,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南方大寨”。一层层整齐的梯田垒起来了,一个个池塘修起来了,供生活用水的支农池建好了,还有两座水库及引水沟渠,靠日夜奋战完成了。我亲眼所见,为开山放炮,有的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那忙碌的工地上,常常夜深了,人们还在临时架设的电灯照射下来回奔忙,挑土、打硪,乡亲们唱着富有节奏的打硪歌,也就是劳动号子:“各位同志啊哦嗨/你笑呵呵啊哦嗨/我们大家呀哦嗨/来比赛呃哎嗨哎咳哟哟。”一唱众和,边打边唱,动作协调,充满信仰,那是我人生最初听到的原生态音乐,多年以后还常在耳畔回响。
让我怀念的还有大队部的舞台,经常有乡亲们和知青自编自导的文艺节目,表演给前来长峪铺参观取经的客人观看。这些节目大都土得掉渣,但原汁原味,令人回味。乡亲们一个个或一家家登台,表演的节目有唱山歌,或三句半,或打渔鼓筒。我那时也是小演员,我们唱的歌跳的舞以及道具,都是学校老师自编自导自制的,好不喜庆热闹!因为通常是利用课余时间或晚上排节目,几岁的我不敢走夜路回家,便常在学校周边的人家留宿、吃饭,去的最多的是小伙伴柴从英家,她母亲李梅香是报厅生产队的队长,也是全大队唯一的女队长。那时物质生活虽不富足,但乡亲们人心齐,泰山移,除了不怕苦不怕累,还对人热情,没有私心,纯朴的民风一直延续至今,这也是令很多外来客人感怀的地方。
有了土地,还需要水来灌溉。长峪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滴水贵如油。记忆最深刻的是小时候洗脸,脸盆里盛一点点水刚好能打湿小毛巾,洗完脸的水再洗脚,洗脚水再喂牲口。每家的毛巾都是色如泥巴,没清过水。找水的艰辛后人不知,也难以复制,必须记载。难忘周末的清晨,天刚蒙蒙亮,外婆就挑着一担空木桶,领着我去岩板沟守浸水,去晚了便要排队。外婆把我送到沟边后,就转身回家忙活去了。我守在岩板沟旁的大石上,等待山泉透过泥石层慢慢渗出,要过很久很久才能用小搪瓷杯舀上一点水,而且杯里一半是泥沙。我在光秃秃的石板上或坐或躺,寂寞地遥望蓝天白云,听小鸟歌唱。心想什么时候,我们这里才能像山下江边人家那样不愁用水呢?那种渴望、那种期盼曾填满我幼小的心灵。
以至于多年后我会在省城想办法帮村里筹一点经费修建水池和修路,或发动同事朋友们资助一些家庭贫困但成绩好的学生。二十多年来象信差和摆渡船一样,来来往往,不曾停歇。虽然微不足道,也不愿与外人道,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儿时那些难以忘怀的记忆。
只是不知什么时候,原来的大队部、知青房、还有花家凸山顶的茅草房教室已寻不出踪影,可能是那种土砖房本容易风化吧!现在的村支书王生龙告诉我,几年前一批老知青回访长峪铺,望着已是荒草萋萋的旧址,黯然神伤,无言失落。但跟着从前带过知青的大队科研队长王文德、刘守元到村里转上一圈后,看到现在的长峪铺已是村容整洁环境美,人民生活富足,又无不欣然而归。
如今我虽在省城工作,但每逢节假日,都喜欢回长峪铺小住。与乡亲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才有回家的感觉,也才有根的踏实。在故乡的山里走一走,看一看,想一想,是我最轻松愉悦的时刻。我曾在诗作《山行》里记录我内心真实的河流:
……
你看那白云
已习惯百年孤独
但仍有千秋明月
依依照它归途
如今我只觉得红尘
任何地方的优游
都比不上故乡
山里的自由行走
……
常回故乡走走,常与乡亲交流,心灵得到洗礼,情感得到升华,总感到自己幸运,总是难以忘记根本。深感长峪铺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决心和精神可歌可泣,应该说给后人听,留给后人看,代代传承。
文档上传者
热门标签
相关文档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