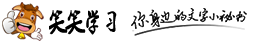欢迎来到98聘
写作《哥哥打妹妹作文》小技巧请记住这五点。(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11-02 23:26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哥哥打妹妹”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这能帮助你写出一篇更深刻、更有见地的文章,而不仅仅是简单的事件叙述:
1. "明确写作目的和中心思想:" 你想通过这篇作文表达什么?是谴责暴力行为?探讨家庭冲突的根源?分析人物性格(哥哥和妹妹)?反思成长过程中的矛盾?还是表达某种复杂的情感(如爱恨交织)? 确定一个清晰的主题或中心思想,这将贯穿全文,指导你的选材和表达。
2. "选择合适的视角和叙述方式:" "视角:" 你是以谁的口吻来写? "妹妹的视角:" 会侧重于受伤、委屈、恐惧、对哥哥的复杂情感(可能又怕又有点依赖)。 "哥哥的视角:" 可能会侧重于冲动、愤怒、无奈、或者试图解释的原因(即使理由不充分)。 "第三者的视角(如父母、旁观者):" 可以更客观地描述事件经过,并可能介入评论或反思家庭环境。 "选择一个主要视角,并保持一致。" 如果需要,可以在文中 subtly 地切换,但要小心处理,避免混淆读者。 "叙述方式:" 是平铺直叙地讲故事,还是带有情感渲染?是客观冷静
小学生作文《我的哥哥》火了,哥哥气得脸都绿了,老师却捧腹大笑
小学生的思想总是很跳跃,他们有很多新奇的想法,家长和小学生在交流的时候,会觉得“摸不到头脑”,在很多问题上不会按照大人的思维和逻辑,但正因为这样,小学生在写作文上,可真是不一般。
不得不说小学生的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虽然他们写作文的字数并不是很多,也没有太多的文采,但却让大人都要“甘拜下风”了,内容过于真实,也只有他们敢描述出来了。今天跟着笔者,我们一起来看看小学生是怎样发挥无穷的想象力,写出这些让人忍不住笑的作文吧!
小学生作文《我的哥哥》火了,哥哥气得脸都绿了,老师却捧腹大笑!
小学生们可以说是“童言无忌”,总是看见什么就说什么,这样的做法,让家长们感觉到很尴尬,这位小学生因为考试没有考好,所以爸爸想要拿扫把打他,本想要反抗,突然想到老师说过要学会关心父母,真是叫人笑出眼泪了,这位小学生关心爸爸也要看场合啊。
小学生们其实是非常有爱心的,他们骨子里很单纯善良,也非常喜欢小动物,因为妈妈的一句谎言,让这位小学生信以为真,作文题目《怀孕》,内容中描述,以为“亲嘴就会怀孕”,有一天他吃东西,刚好小狗过来抢,无意间就亲了小狗,过了几个月小狗下崽了,这个小学生暗暗发誓,一定要照顾好这“她们娘几个”,真的是责任感爆棚,相信老师看完要笑的合不拢嘴了,小学生真的是太可爱了。
这位小学生的作文是《我的哥哥》,本想夸赞医学生的哥哥是很勤奋好学的,并且白天还帮忙做兼职在肉店卖肉,晚上到医院去实习,没想到结尾处有反转,在哥哥帮忙给病人推进手术室时,被一位老妇人误以为是“杀猪的”,还很慌张的问:“你要把我推到哪去?”,这样的作文让老师捧腹大笑,学生们写作文的的源泉真的是来源于生活,评价哥哥真的是不一般,哥哥在这位小学生的作文中,真的是形象都没有了,是被哥哥看到作文内容,相信要被气得脸都要绿了!
小学生作文《我的哥哥》火了,哥哥气得追着打,老师却笑到捧腹,其实在所有的家庭教育中,不仅仅是父母是影响我们的人,兄弟姐妹,像这样小学生的哥哥,也会影响到他的成长,相信他和哥哥的感情一定很不错。
从这些小学生的作文中,也能够看出写作文的流畅度还是很好的,前后有反转,内容也很精彩,不过对于很多低年级的学生,想要写出流畅度很高的作文却有些难。
低年级的小学生,应怎样写出更流畅的作文?
内容和题目要相符合,不要跑题,很多低年级的学生,因为写作文练习的比较少,所以总是会出现跑题的情况,小学生们一定要多练习,尝试去写作文,这样在长期的练习下,才能让文章的内容和题目更匹配。
作文有架构,能够反转,增加逻辑性,小学生的想象力是很丰富的,但是逻辑性却比较差,小学生在刚开始写作文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流水似的叙述,但是慢慢的积累和练习后,小学生可以让自己的作文更加有架构,能够前后反转,让作文内容更加精彩,整个作文读起来更加流畅。
从这些小学生的作文中能够看出,内容是非常清奇的,非常具有幽默感,而作文及其幽默的写作方式,也是很吸引人的。
小学生作文内容精彩,幽默感会让作文更加分
笔者认为,流水式的作文会很空洞,即使运用了很多的修辞方法,但也难以达到很好的阅读效果,不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小学生多采用幽默诙谐的方式进行写作,会让作文更加有内涵,更精彩。
就像小学生作文我的哥哥,其实除了叙述之外,是非常具有幽默感的,小学生能够把最平常的生活,通过诙谐的语言描述出来,真的是值得学习和继续培养的,幽默感会让作文更加分,希望家长和老师都能重视这个方面的培养。
笔者寄语:题材来源于生活,希望每个家长都能支持小学生,能够帮他们检查作文的流畅度,在语言上,能够让他们用更加幽默诙谐的语言描述出来,作文会更加精彩,相信通过家长和老师的培养,他们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文,学习到更多的写作要点和知识。
今日话题:你觉得这些小学生作文写得怎么样?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遭哥哥扇两耳光后,湖南女子瘫痪20年,父母看录像后崩溃
“强,勺子有点烫。”
我微微偏过头,嘴唇碰了一下勺沿,又缩了回来。
他“哦”了一声,手腕一抖,把勺子撤回去,放在嘴边吹了吹,又试了试温度,才重新递到我嘴边。
米粥熬得烂熟,里面有剁得细碎的青菜末,是我能下咽的东西。
这样的场景,二十年了,几乎没什么变化。
我,林薇,躺在这张床上二十年了。
我哥,林强,在床边照顾我二十年了。
我们家在湖南一个山坳里,日子就像门前那条小溪,看着在流,其实年年都是那个样。
二十年前,我十七岁,是村里学习最好的姑娘,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所有人都说,我们林家要飞出个金凤凰了。
那时候,我哥也才二十岁,高大,能干,是家里唯一的壮劳力。
我们的生活,原本应该像村里其他人一样,他娶妻生子,我上学远嫁,逢年过节,再拖家带口地回到这个小院里。
可这一切,都在那个夏天的午后,被两声清脆的响声,彻底打碎了。
如今,我三十七,他四十。他还没娶妻,我也没能离开这张床。
他每天给我喂饭,擦身,端屎端尿。他的手,原本是拿锄头镰刀的,现在却比村里任何一个女人都懂得怎么照顾人。
他的背,也从二十年前的笔直,变得有些佝偻了。
村里人说,林强真是个好哥哥,为了妹妹,把自己一辈子都搭进去了。
我听着,心里没什么滋味。
好吗?我不知道。
我只记得,那两巴掌扇在我脸上的力道,火辣辣的,带着他所有的力气。
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的时候,就在床上了。脖子以下,没了知觉。
医生说,是高位截瘫。
原因,家里人说,是我和我哥吵架,他推了我一把,我摔倒了,磕到了颈椎。
“推了我一把”,这是爸妈统一的口径。
我哥默认。
我也默认。
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最后的一幕,就是他扬起的手。至于后面是怎么倒下的,我完全没有印象。
二十年,这个“事实”就像一口大钟,罩在我们家每个人心上。沉重,密不透风,谁也不去敲响它。
我们就这样,过着一种外人看起来相安无事,甚至有点感人的日子。
直到我侄子小军,放暑假从县城回来。
小军是我哥唯一的念想。他没结婚,就把我大伯家的儿子过继过来,当亲儿子养,供他上学。
小军今年上高一,学校布置了个作业,叫《寻访家庭的记忆》,让他回家找找老物件,写一篇作文。
这孩子,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
最后,在阁楼一个积满灰尘的木箱子里,翻出来一堆东西。
有我小时候的奖状,我爸的旧烟斗,还有一台很老旧的DV机,和几盘磁带。
“爸,这是什么?”小军举着那台砖头一样的机器,献宝似的跑下楼。
我哥正在给我按摩萎缩的小腿肌肉,闻声抬头看了一眼,眼神滞了一下。
“哪儿翻出来的?都坏了。”他说。
“没坏,我看了,好像还能用。”小-军-兴-致-勃-勃,“姑,这里面会不会有你小时候的录像啊?”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
那台DV机,我记得。
是我远在广东打工的表叔,有一年过年带回来的稀罕玩意儿。那年,我们家特别热闹,亲戚都聚在一起,表叔拿着机器到处拍。
后来他回广东,东西太重,就留在了我们家,说下次回来再拿。
再后来,我们家出了事,谁还有心思去管这个东西。
没想到,二十年了,它还在。
“强,要不……看看?”我开口,声音有些干涩。
我哥的手停了。
他没看我,也没看小军,只是盯着那台黑色的机器,眼神很深,像结了冰的湖面。
我妈从厨房出来,看见那东西,脸色也变了。
“看什么看,都多少年的东西了,早放坏了。”她走过来,想从小军手里拿走。
“妈,没坏,我刚试了。”小军不肯松手,“老师说要找有纪念意义的东西,这个正好。”
“一个破机器有什么纪念意义的!”我妈的声音有些尖。
我爸坐在门槛上抽烟,吧嗒吧嗒的,烟雾缭绕。他回头看了一眼,皱着眉,没说话。
家里的空气,一下子就僵住了。
小军是个聪明的孩子,他看看我哥,又看看我妈,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但他还是坚持:“爸,我就看看,看完就收起来。”
我哥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同意。
最后,他却缓缓地点了点头。
“看吧。”
他说。
电视是那种老式的大屁股彩电,我哥找出连接线,捣鼓了半天,终于把DV机连上了。
按下播放键,一阵雪花点之后,画面跳了出来。
是二十年前,我们家的堂屋。
画面有些晃动,色彩也泛着黄,但一切都那么清晰。
画面里,我爸还很年轻,头发乌黑,正和几个叔伯喝酒划拳,满面红光。
我妈端着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从厨房出来,脸上带着笑,还在数落我爸少喝点。
然后,镜头一转,拍到了我。
十七岁的我,穿着一件粉色的新棉袄,正坐在小板凳上,给我的小侄女梳辫子。我的脸颊红扑扑的,眼睛亮得像有星星。
我看着画面里的自己,那个鲜活的,能跑能跳的女孩,感觉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我的眼眶有点发热。
小军在一旁小声说:“姑,你那时候真好看。”
画面继续播放,是过年的热闹场景,拜年,放鞭炮,孩子们在院子里追逐打闹。
表叔的声音在画外音里响起:“来,小薇,对着镜头说个新年愿望。”
镜头对准了我。
我有点害羞,但还是大声说:“我希望今年能考上北京的大学!”
说完,我还做了个加油的手势。
画面里的每个人都在笑,都在鼓掌。
我哥也出现在镜头里,他站在我身后,高高大大的,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笑得一脸宠溺。
那一刻的他,眼神清澈,没有一丝阴霾。
我看着电视,心口像是被什么堵住了,喘不过气。
磁带还在转动,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热闹的画面结束了,镜头似乎被随意地放在了堂屋的柜子上,对着屋里。
可能是表叔随手一放,忘了关机。
画面里没人了,只有空荡荡的屋子,和外面传来的隐约的鞭炮声。
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地过去。
我们都以为,这盘带子就到这里结束了。
小军正要去按快进,我爸突然开口了。
“等等。”
他的声音很沉,像一块石头。
我们都愣住了。
画面里,天色好像暗了下来,屋里的光线变得昏黄。
然后,有人走进了镜头。
是我妈。
她走进来,收拾桌上的残羹冷炙。
接着,我爸也进来了,他好像喝多了,走路有点晃。
再然后,是我和我哥。
我们一前一后地走进来,两个人的脸色都不太好。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了上来。
我记得,那天晚上,吃完年夜饭,我和我哥因为一件事吵了起来。
为了我上学的事。
那年我高三,学习成绩很好,老师说我努努力,考个重点大学没问题。
但家里的条件,很紧张。
我哥那时候在跟一个师傅学木工,刚出师,还没挣到什么钱。家里所有的开销,都靠我爸种那几亩薄田。
我哥的意思是,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高中毕业就够了。他想让我读完高中,就去广东打-工,挣钱帮衬家里。
而他,想用家里的积蓄,去开个小小的家具作坊。
我当然不同意。
上大学,走出这个山沟,是我从小的梦想。
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吵起来的。
电视画面里,没有声音,但能看到我们两个人的嘴在不停地动,脸涨得通红,手上还比划着。
我看到十七岁的自己,一脸倔强,脖子梗着,毫不退让。
我看到二十岁的林强,眉头紧锁,眼神里有不耐烦,也有焦急。
然后,我爸妈也加入了争吵。
我妈在中间劝,我爸则站到了我哥那边。
他指着我,嘴里说着什么,情绪很激动。
我看到画面里的自己,哭了。
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掉,但我还是不肯低头。
争吵越来越激烈。
突然,我哥猛地站了起来。
他冲到我面前,扬起了手。
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
客厅里,一片死寂。
小军张着嘴,呆呆地看着电视。
我妈的脸,白得像一张纸。
我哥的身体,绷得像一块石头。
电视里,那只手,重重地落了下来。
“啪!”
一声脆响。
虽然录像没有声音,但那一瞬间,我仿佛听到了。
我被打得一个趔趄,头偏向一边。
然后,是第二下。
“啪!”
更重。
我看到画面里的自己,捂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哥。
然后,我转身就往外跑。
我哥似乎想来拉我,但被我甩开了。
我跑得很快,很急,像是在逃离什么。
就在我跑到门槛的时候,脚下不知道被什么绊了一下。
我的身体,失去了平衡。
整个人,直直地向后倒去。
我的后脑勺,重重地磕在了堂屋里那张八仙桌的桌角上。
那张桌子,是老榆木做的,桌角又尖又硬。
我看到画面里的自己,像一个断了线的木偶,软软地瘫倒在地。
一动不动。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
电视机里,画面定格在我倒下的那一瞬间。
客厅里,死一般的寂静。
我能听见自己急促的心跳声,一下,一下,撞击着胸膛。
原来……是这样。
原来,不是他推的我。
是我自己,跑的时候,绊倒了。
那致命的一下,是磕在了桌角上。
二十年了。
我一直以为,是那两巴-掌,或者他接下来的推搡,让我变成了这样。
我恨他,也怨他。
这二十年的禁锢,这二十年的青春,这二十年不能自理的狼狈,都源于他那两下没有控制住的怒火。
可现在,这个被遗忘了二十年的镜头告诉我,不是。
至少,不全是。
那两巴-掌是引子,但真正毁掉我的,是那一次意外的摔倒。
是一个谁也预料不到的,该死的意外。
我缓缓地转过头,看向我哥。
他的脸,已经没有一丝血色。
嘴唇在微微颤抖,眼睛死死地盯着电视屏幕,像是要把它看穿。
他的身体,在发抖。
那种抖动,从他的肩膀,一直传到他放在膝盖上的手。
我妈“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整个人瘫坐在地上,用手不停地捶打着自己的胸口。
“作孽啊……作孽啊……”她反复念叨着。
我爸的烟,掉在了地上。
他佝偻着背,双手抱着头,发出了野兽一样压抑的呜咽。
小军吓坏了,他看看电视,又看看我们,不知所措。
“爸……妈……哥……”我开口,声音嘶哑得不像自己的。
我想说点什么。
我想说,没关系。
我想说,我不怪你了。
但我说不出来。
因为,我的心里,乱成了一团麻。
有震惊,有茫然,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巨大的悲凉。
二十年。
我们一家人,都活在一个被简化了的“真相”里。
我哥是“凶手”。
我是“受害者”。
爸妈是无奈的“旁观者”。
我们用这个简单粗暴的标签,定义了彼此,也禁锢了彼此。
我哥用二十年的付出来赎罪。
我用二十年的怨恨来惩罚他。
爸妈用二十年的沉默和偏袒,来维持这个家的平衡。
现在,真相大白了。
可我们,谁都没有感到解脱。
那晚,谁都没有吃饭。
我妈病倒了,躺在床上,不说话,也不睁眼。
我爸一个人,在院子里坐了一夜。
小军被吓得不轻,第二天一早就找了个借口,回县城学校了。
家里,只剩下我和我哥。
他给我喂了晚饭,擦了身。
整个过程,一言不发。
他的动作,还是和以前一样熟练,但却像一个没有灵魂的木偶。
晚上,他坐在我的床边,没有像往常一样离开。
我们就那么沉默地待着。
房间里,只有窗外虫鸣的声音。
“哥。”我先开了口。
他身体震了一下,抬起头看我。
灯光下,我才看清,他的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
“我都看到了。”我说,“是……我自己摔倒的。”
他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没发出声音。
眼泪,却先从他那双粗糙的,布满皱纹的眼角,滚了下来。
一个四十岁的男人,一个撑起这个家二十年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他没有嚎啕,只是无声地流泪,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对不起你……小薇……我对不起你……”他哽咽着,一遍遍地重复着这句话。
“不怪你。”我说。
我说的是真心话。
当我知道真相的那一刻,心里那块压了二十年的大石头,好像突然就松动了。
怨恨,就像是扎在我心上的一根刺。
现在,这根刺,被拔了出来。
虽然伤口还在,但那种日夜折磨的疼痛,减轻了。
“是我不好……我不该跟你吵……更不该动手……”他用手背胡乱地抹着眼泪,“如果那天……如果我没打你……你就不会跑……不跑,就不会摔倒……”
他把所有的责任,还是揽到了自己身上。
我看着他,这个我叫了三十多年“哥”的男人。
二十年前,他也是个有梦想的年轻人。
他想开个家具作坊,当个小老板,娶个漂亮的媳-妇,过上好日子。
可是,因为我,他的一切都成了泡影。
他把最好的二十年,都耗在了我这张床边。
他的人生,从我倒下的那一刻起,也跟着一起瘫痪了。
“哥,都过去了。”我轻声说。
他摇着头,泪水滴落在他满是老茧的手上。
“过不去……小薇,过不去的……”
我知道,他过不去。
那两巴-掌,是他心里的魔鬼,折磨了他二十年。
即使现在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一场意外,他也无法原谅自己。
因为,是他,点燃了那场意外的导火索。
那盘录像带,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放出了真相,也放出了我们一家人,压抑了二十年的所有情绪。
我妈病了一场,好了之后,像是变了个人。
她不再整天唉声叹气,也不再用那种愧疚又怜悯的眼神看我。
她开始尝试着,和我聊天。
聊一些以前我们从不触碰的话题。
“小薇,妈对不起你。”有一天,她给我梳头的时候,突然说。
我从镜子里看着她。
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
“那天……你和你哥吵架,你爸吼你,其实……我们是怕了。”
“怕?”
“怕你真的考出去,就再也不回来了。”她叹了口气,“村里好几个女娃,上了大学,就嫁在了城里,几年都不回来一次。我们……我们就你和你哥两个孩子,要是你走了,你哥又……我们老了,可怎么办?”
我愣住了。
原来,是这样。
他们不是不希望我好,他们只是害怕失去。
那种根植于土地的,对未知的恐惧,对亲人离去的恐惧,让他们做出了最保守,也是最自私的选择。
“你哥说,想开个作坊,我们觉得,这是个实实在在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比你那个上大学的梦,要稳当。”
“所以,你们就向着他。”
“是。”我妈点头,眼泪掉了下来,“我们想着,委屈你一下,等家里条件好了,再补偿你。谁知道……谁知道会出那样的事……”
我闭上眼睛。
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慢慢地撕开,很疼,但又有一种释然。
我终于明白了。
那场争吵,不只是为了学费,不只是为了谁的前途。
那是一场,固守与远行,现实与梦想的战争。
而我,成了这场战争里,最无辜的牺牲品。
我爸也变了。
他不再整天闷着头抽烟。
他开始学着,照顾我。
他会推着轮椅,带我到院子里晒太阳。
山里的阳光很好,暖洋洋的,照在身上很舒服。
他会指着远处的山,告诉我,哪个山头有野杜鹃,哪个山头有野板栗。
这些,都是我躺在床上,看不到的风景。
有一次,他推着我,在院子里停下。
“薇薇。”他叫我的小名,声音有些沙哑。
我“嗯”了一声。
“爸……没本事。”他说,眼睛看着远方,“如果爸有本事,能挣很多钱,你们兄妹俩,就不用争了。”
“你想上学,就去上。你哥想开作坊,就去开。”
“都怪爸……没用。”
他低着头,肩膀在微微耸动。
我看到,有浑浊的液体,滴落在他脚下的黄土地上。
这是一个中国式父亲,最沉重的道歉。
他把所有的根源,都归结于自己的无能。
我伸出手,想去拍拍他的背。
可是,我的手,抬不起来。
我只能说:“爸,不怪你。”
真的,不怪。
在那个年代,在那个贫瘠的山村,他们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只是,他们的爱,带着那个年代的局限,带着他们认知里的狭隘。
他们用他们以为对的方式,爱着我们,却无意中,造成了最大的伤害。
而我哥,林强。
他话变得更少了。
但他看我的眼神,变了。
以前,他的眼神里,是沉重的责任,是化不开的愧疚,是日复一日的麻木。
现在,他的眼神里,多了一些别的东西。
是一种……很轻,很软的东西。
像羽毛,像云彩。
他会给我讲,他在外面听来的笑话。
虽然一点也不好笑,但我还是会配合地弯弯嘴角。
他会从山上,采来野花,插在我床头的瓶子里。
红的,黄的,紫的,给这个灰暗的房间,添了一点色彩。
有一天,他从镇上回来,带回来一个包裹。
打开来,是一堆书。
有小说,有诗集,还有一些关于旅行的杂志。
“你以前,不是最喜欢看书吗?”他说,把一本书放在我的枕边,“以后,我念给你听。”
那天下午,他就坐在我的床边,用他那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给我念海子的诗。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洒在他身上,也洒在我身上。
我静静地听着,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
二十年了。
我以为,我的世界,就只有这间屋子,这张床,这方天花板。
我以为,我的人生,早就死了。
可是,当他念出那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仿佛真的看到了那片海。
蓝色的,无边无际的。
有海鸥在飞,有浪花在唱歌。
原来,我的心,还没有死。
它只是被怨恨和绝望的尘埃,覆盖了太久。
现在,有人,正小心翼翼地,帮我把那些尘埃,一点点擦去。
日子,还在继续。
我依然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
我哥依然守在床边,照顾我的饮食起居。
我们家的那口大钟,还在。
但它不再密不透风。
真相,像一道光,从裂缝里照了进来。
虽然刺眼,但也带来了温暖。
我们开始学着,面对那道伤疤。
不再掩饰,不再逃避。
我们开始学着,原谅。
原谅别人,也原谅自己。
有一天,村里的媒人,又来我们家了。
是给我哥说亲的。
对方是邻村的一个寡妇,带着个孩子,人很本分。
以前,媒人也来过几次,都被我哥和我爸妈,用各种理由回绝了。
我知道,他们是怕我没人照顾。
我哥,也觉得自己不配拥有幸福。
这次,媒人走后,我哥坐在我床边,闷声不响。
我看着他,说:“哥,去见见吧。”
他猛地抬头看我,一脸错愕。
“挺好的。”我说,“你……也该有个家了。”
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
“我没事。”我抢在他前面说,“有爸妈在呢。而且,你娶了嫂子,家里还多个人,不是更热闹吗?”
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轻松一点。
“小薇……”他叫我的名字,声音里带着颤抖。
“哥,你已经给了我二十年了。”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剩下的日子,为你自己活吧。”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眼圈,慢慢地红了。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后来,我哥和那个女人,结了婚。
婚礼很简单,就在我们家院子里,摆了几桌酒席。
那天,我很开心。
我让嫂子给我化了妆,穿上了我最好的一件衣服。
我坐在轮椅上,看着我哥,穿着一身新西装,胸口戴着大红花,满脸笑容地给客人敬酒。
那一刻,我感觉,他身上那副背了二十年的沉重枷锁,终于被卸了下来。
他,终于可以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去生活,去爱,去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了。
嫂子是个很好的人。
她不嫌弃我,把我当亲妹妹一样照顾。
她会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会陪我聊天,解闷。
她带来的那个孩子,叫小石头,很懂事,会叫我“小姑”。
家里,因为她们母子的到来,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有了笑声,有了烟火气。
我爸妈的脸上,也多了很多笑容。
我哥的那个家具作坊,也终于开了起来。
就在我们家旁边,搭了个棚子。
每天,我都能听到里面传来“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和刨木花的“沙沙”声。
那声音,很好听。
像是在奏响一曲,关于新生的乐章。
有时候,我哥会把他做好的小玩意儿,拿给我看。
一个木头的小鸟,一个可以转动的风车。
他的手艺很好,东西做得活灵活-现。
他说,等以后挣了钱,就带我出去看看。
去北京,看天安门。
去看我当年,最想考的大学。
我说,好。
我知道,这可能只是一个遥远的梦。
我的身体,也许一辈子都离不开这个小山村。
但是,没关系了。
我的心,已经自由了。
那盘被遗忘了二十年的录像带,像一场迟来的审判。
它审判了我们每个人的过错,也给了我们每个人救赎的机会。
它让我们明白,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它只会像毒药一样,侵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所有人都活在痛苦的深渊里。
只有爱和宽恕,才能让我们从泥潭里走出来,重新看到阳光。
现在,我每天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鸟叫,闻着院子里的花香,听着作坊里的敲打声,还有小石头追逐打闹的笑声。
我的世界,依然很小。
但我的心里,却很满。
我知道,生活给了我一副烂牌。
但我的家人,用他们的爱,努力地,想陪我打好这副牌。
这就够了。
至于未来会怎样,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从今天起,我要像海子诗里写的那样。
做一个幸福的人。
关心粮食和蔬菜。
即使我没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
但我的心里,已经春暖花开。
文档上传者
热门标签
相关文档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