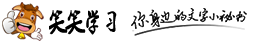欢迎来到98聘
手把手教你写《离别作文300字》,(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11-03 22:31

写作核心提示:
离别,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经历。当我们与亲朋好友、同学老师告别时,心中总会有不舍与感伤。然而,离别也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它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的相处时光,也让我们学会坚强与独立。
在写关于离别的作文时,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 真实情感:离别作文最重要的是表达真情实感。我们可以回忆与离别对象之间的美好时光,表达对他们的感激和不舍之情。同时,也要展现出面对离别的坚强与成熟。
2. 具体事例:为了让作文更加生动,我们可以举一些具体的事例来支撑我们的观点。比如,回忆与离别对象一起度过的难忘瞬间,或者他们对我们成长的影响等。
3. 积极态度:虽然离别带来了感伤,但我们也要展现出积极的面对态度。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聚,我们要相信与离别对象在未来的某一天还会再见。
4. 简洁明了:离别作文不需要过于冗长,我们要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达我们的情感和观点。同时,注意作文的结构和逻辑,让读者能够清晰地理解我们的意图。
总之,写一篇关于离别的作文,我们要注重真实情感、具体事例、积极态度和简洁明了的表达。通过这些注意事项,我们可以写出一篇感人至深、令人难忘的离别作文。
28年陪伴换300字告别:她比我们想象的更清醒
看到翁帆那篇简短的悼文时,我正喝着半凉的咖啡。手指悬在屏幕上方顿了三秒——这不像当代互联网的作风。在这个连分手都要发九宫格长文的时代,她用三行字就道尽了28年的晨昏。
忽然想起民国时的陆小曼。当年徐志摩坠机后,这位被骂"红颜祸水"的才女,默默整理了整整20箱遗稿。而今天同样站在舆论漩涡里的翁帆,选择用最克制的文字作别。不是寡情,恰是看透了表演式悲伤的虚妄。
我们总习惯用字数丈量深情。仿佛悼文必须泣血千行,眼泪必须浸透九宫格,才算对得起一段感情。可真正经历过生死离别的人都懂:最痛的伤口往往最沉默。就像我读者群里那位失去丈夫的姐姐说的:"真正的悲伤是凌晨三点惊醒时,伸手摸到的半边空枕头。"
翁帆这份反常的简短,反而让我看见婚姻最本真的模样。没有晒过生日礼物,没炒作过"爷孙恋"细节,连最后的告别都像他们被拍到的那些散步照片——他拄着拐杖慢慢走,她配合着放慢脚步。爱情从来不需要向外界自证,就像深海里的珍珠不需要向沙滩证明光芒。
评论区有人刻薄地说:"看吧,果然没感情。"但更多人在问:"要怎么才能像她这样,在风暴中心保持体面?"或许答案就藏在那300字里:当潮水退去,所有标签都会被冲散,留下的只有两个灵魂真实的共鸣。
此刻我望着办公桌上和先生的合照,突然理解为什么有些爱情不需要解释。就像你永远不会问大海为何蔚蓝,不会质疑月光为何皎洁。有些陪伴,本就是超越语言的默剧。
母亲与大姨不来往,那天她和舅舅突然到访,竟是来告别
大姨走后,母亲在厨房里站了很久,对着一锅没炖烂的酱肘子,一句话也没说。锅里翻滚着浓郁的香料气,却怎么也盖不住屋子里那股子散不掉的、生分的味道。
二十年,足够一个孩子长大成人,也足够让姐妹间的怨怼,长成一堵密不透风的墙。这堵墙就砌在我家的客厅里,平时看不见,摸不着,但只要谁无意中提起“大姨”两个字,它就立刻浮现出来,冰冷,坚硬,带着刺骨的寒气。
我从小就在这堵墙的阴影下长大,习惯了母亲提到她唯一的姐姐时,那瞬间沉下来的脸和紧抿的嘴唇。我以为这堵墙会一直矗立到天荒地老,直到她们中某一个人的生命尽头。
可那天下午,墙塌了。或者说,是被我舅舅,用一种近乎粗暴的方式,硬生生砸开了一道裂缝。一切,都得从那个闷热的周六说起。
第1章 不速之客
那个周六的午后,空气黏稠得像化不开的麦芽糖。老旧的立式风扇有气无力地摇着头,送来的风也是温吞的。我妈王秀英正在厨房里忙活,准备做她最拿手的红烧肉,浓郁的酱香混着八角的味道,从厨房门缝里丝丝缕缕地钻出来,是我从小闻到大的、属于家的安稳气息。
我窝在沙发里,一边刷着手机,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她说话。
“妈,下周我同学结婚,在城西那个挺有名的酒店,你说我随多少份子钱合适?”
“你同学?就是那个上大学时总来咱家蹭饭的小姑娘?”我妈的声音隔着油烟机的轰鸣传来,有点模糊,但语调里的精明劲儿一点没少。
“对,就是她,李晓雯。”
“人家都结婚了啊……时间过得真快。”她感慨了一句,然后话锋一转,“关系好就多给点,五百吧,别让人家觉得咱小气。要是关系一般,三百也过得去。”
我笑了笑,正准备回话,门铃突然响了。
“叮咚——叮咚——”
声音很急,透着一股不容拒绝的催促。我和我妈都愣了一下。我们家是老式居民楼,街坊邻里都熟,有事都是直接在楼下喊一嗓子,很少有人这么正式地按门铃。
“谁啊?这时候来。”我妈关了火,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一脸狐疑地朝门口走去。我也好奇地站起身,跟在她身后。
猫眼里看出去,我妈的身体瞬间僵住了。
她没有开门,而是转过头,脸色复杂地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却没发出声音。那眼神里有震惊,有抗拒,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慌乱。
“谁啊,妈?”我忍不住问。
门铃又响了起来,比刚才更有力。
我妈深吸了一口气,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猛地一下拉开了门。
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我的舅舅王建国,他一脸焦灼,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看见我们,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而他身后,那个微微侧着身,眼神躲闪,局促不安地抓着自己衣角的人,是我只在旧照片里和别人口中熟悉,却在现实生活中隔绝了二十年的——我的大姨,王秀敏。
空气仿佛在开门的一瞬间凝固了。
风扇的嗡嗡声,窗外马路上的汽车鸣笛声,邻居家的电视声,所有声音都像被按了静音键。我只能听见自己心脏“怦怦”的跳动声。
大姨比照片上老了很多,也瘦了很多。两鬓已经斑白,眼角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深深地刻在那里。她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碎花衬衫,看上去很憔悴,眼神里带着一种长年累月的怯懦和疲惫。
我妈就那么堵在门口,像一尊石像,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的目光越过舅舅,直直地落在大姨身上,那眼神冷得像数九寒冬的冰凌子。
“姐……”舅舅的声音干涩而沙哑,他推了推大姨的胳膊,“快,叫人啊。”
大姨的嘴唇哆嗦着,目光从我妈的脸上艰难地移开,落到我身上,扯出一个微弱的、讨好的笑:“是……是陈静吧?都长这么大了……”
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种不确定的试探。我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却不知道该叫她什么。那两个字在舌尖上盘旋了二十年,早已变得陌生而沉重,我根本叫不出口。
“有事?”我妈终于开口了,声音平板,听不出任何情绪,却比任何疾言厉色都更让人心寒。
舅舅连忙上前一步,陪着笑脸:“姐,你看这大热天的,能不能……让我们进去说?就几句话,说完就走。”
我妈没说话,只是侧了侧身子,让出了一条仅供一人通过的缝隙。那姿态,不像是在请客,倒像是在海关放行,充满了审视和不情愿。
舅舅如蒙大赦,赶紧拉着大姨挤了进来。
屋子里的气氛因为这两个不速之客的闯入,变得更加压抑和诡异。我妈转身走回厨房,重新打开了火,锅里瞬间发出“刺啦”一声巨响,像是她压抑了许久的怒气找到了一个宣泄口。
我尴尬地站在原地,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小静,倒杯水给你舅舅和你……大姨。”舅舅看着我,眼神里带着恳求。
我“哦”了一声,逃也似的去了厨房。
厨房里,我妈背对着我,肩膀绷得紧紧的,她用锅铲用力地翻炒着锅里的肉,那架势不像在做饭,倒像是在跟谁置气。
“妈……”我小声叫她。
“倒你的水去!”她头也不回地打断我,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火气。
我不敢再多说,默默地倒了两杯凉白开。端出去的时候,我看到大姨正局促地坐在沙发边缘,双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笔直,像个等待宣判的犯人。她不敢看四周,只是低着头,盯着自己那双有些磨损的布鞋。
舅舅坐在她旁边,不停地用手搓着大腿,脸上的表情既焦急又无奈。
我把水杯放在他们面前的茶几上,发出了轻微的“叩”的一声。大姨的身体明显地抖了一下。
客厅里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只有厨房里传来越发响亮的锅铲碰撞声。那声音一下一下,像重锤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但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今天,这个家维持了二十年的“平静”,就要被彻底打破了。
第2章 沉默的墙
沉默像一张无形的网,笼罩着整个客厅。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最后只能选择在离他们最远的单人沙发上坐下,假装低头看手机,耳朵却竖得老高。
舅舅端起水杯,一口气喝了大半杯,像是要借此给自己壮胆。他清了清嗓子,试图打破这令人窒息的僵局。
“小静啊,最近工作怎么样?还顺利吧?”他没话找话地问我。
“挺好的,舅舅。”我干巴巴地。
“那就好,那就好。年轻人,事业为重。”他点着头,目光却不由自主地飘向厨房的方向。
大姨始终没说话,她只是偶尔抬起头,飞快地瞥一眼墙上挂着的全家福。那张照片是我十岁生日时拍的,照片上有我,有爸妈,有舅舅一家,甚至还有姥姥。唯独没有她和她的家人。那是一个明显的、刻意的空白。
我记得小时候,我曾经天真地问过我妈:“妈妈,为什么我们家没有大姨啊?”
当时我妈正在给我织毛衣,听到我的问题,手里的毛衣针顿了一下,差点戳到手指。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了,才缓缓开口,声音很低:“你大姨……她忙,顾不上我们。”
那是我第一次从母亲嘴里听到关于大姨的、唯一一句不带任何情绪的解释。但从那天起,我学会了不再追问。我知道,这是一个禁区。
随着我慢慢长大,从亲戚们零星的、讳莫如深的交谈中,我拼凑出了一个模糊的故事轮廓。似乎是跟姥姥生病有关,似乎又牵扯到钱,但具体是什么,没人愿意跟我这个小辈说清楚。
我只知道,从我记事起,母亲和大姨就已经是仇人了。逢年过节,我们只去舅舅家,从不去大姨家。家族的聚会,有我妈在,就绝不会有大姨的身影。她们像磁铁的两个同极,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强硬地排斥开,永远无法靠近。
这堵墙,是母亲亲手砌起来的。她性子刚烈,爱憎分明,一旦认定了什么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在她眼里,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中间地带。显然,大姨在她那里,被划进了永不原谅的“错”的那一边。
厨房里的火终于关了,我妈端着一盘红烧肉走了出来。她没有看沙发上的两个人,径直把菜放在餐桌上,然后解下围裙,对我说:“小静,吃饭了。”
说完,她就拉开椅子坐下,拿起筷子,仿佛客厅里除了我们母女,再没有其他人。
这是一种极致的无视,比任何恶毒的语言都更伤人。
舅舅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他猛地站了起来。
“王秀英!”他终于忍不住了,声音也大了起来,“你这是什么态度?你姐她……”
“我姐?”我妈冷笑一声,筷子在盘子里扒拉着,头也不抬,“我可当不起。我王秀英没这个福气,有这么个‘好’姐姐。”
“你!”舅舅气得嘴唇发抖,“都过去多少年了?你这脾气怎么就一点都没改?石头做的心也该捂热了!”
“捂不热。”我妈夹起一块肉,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每一个动作都透着刻意的冷静和疏离,“有些事,一辈子都过不去。王建国,你要是来给我上课的,那门在那边,不送。要是来认亲的,那你也找错地方了。”
“我们不是来跟你吵架的!”舅舅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哀求,“秀英,算我求你了,行不行?你就听我们说几句话,几句话就行!”
一直沉默的大姨,这时候终于有了动作。她颤抖着站起身,走到餐桌旁,离我妈两步远的地方站定。
“秀英……”她开口了,声音嘶哑得厉害,像是被砂纸磨过,“我知道,你恨我。这些年,我……我对不起你,更对不起妈。”
我妈咀嚼的动作停了下来。她缓缓抬起头,二十年来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正式地看着她的姐姐。
她的眼神里没有了刚才的冰冷,取而代 ઉ的是一种更复杂的情绪,像是一潭深不见底的湖水,表面平静,底下却暗流汹涌。有怨,有恨,但似乎还有一丝被深深掩埋的、不为人知的悲伤。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妈的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妈已经走了快十年了。你这句‘对不起’,是说给我听的,还是说给地下的她听的?”
大姨的眼圈瞬间就红了,泪水在浑浊的眼球里打着转,却倔强地不肯掉下来。
“我知道晚了……什么都晚了。”她哽咽着说,“可有些话,要是不说,我怕……我怕就再也没机会了。”
“没机会?”我妈挑了挑眉,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怎么,你也要走了?去哪儿啊?是准备跟你那个宝贝丈夫一样,躲到天涯海角,让我一辈子都找不着人吗?”
这句话像一把淬了毒的刀,狠狠地插进了大姨的心口。
她的脸色“唰”地一下变得惨白,身体晃了晃,几乎要站不稳。舅舅赶紧上前扶住她。
“王秀英!你说话别太过分!”舅舅是真的怒了,他指着我妈,手指都在发抖,“你知不知道她……”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妈猛地把筷子拍在桌上,发出“啪”的一声脆响,把我吓了一跳,“我只知道,当年妈躺在病床上,每天都要花大笔的钱续命的时候,她王秀敏在哪儿!我只知道,我低声下气去求她,让她把妈留下的那点救命钱拿出来的时候,她是怎么说的!”
我妈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积压了二十年的怒火,终于找到了一个缺口,喷涌而出。
“她说钱被她男人拿去做生意周转了,过两天就还!结果呢?两天又两天,直到妈闭眼,我都没看到一分钱!连她的人影都没看到!”
“王秀英,你告诉我,这是姐姐做得出来的事吗?那是咱妈!亲妈!”
最后几个字,她几乎是吼出来的,声音里带着泣血般的悲愤。
客厅里,一片死寂。只有我妈粗重的喘息声。
而大姨,在听到这些话后,那强忍着的泪水,终于决堤了。她没有嚎啕大哭,只是无声地流着泪,泪水顺着她深刻的皱纹,一道道地滑落,滴在胸前的衣襟上,晕开一团团深色的水渍。
她张了张嘴,似乎想解释什么,却只发出了几声破碎的、不成调的音节。
看着眼前这一幕,我心里堵得难受。我知道,那堵看不见的墙,今天算是彻底被撞开了。墙后的景象,是如此的鲜血淋漓,不堪入目。
第3章 迟到的真相
“不是那样的……秀英,不是你想的那样……”大姨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却微弱得像风中的烛火,随时都可能熄灭。
“不是哪样?”我妈的情绪已经失控,她站起身,双眼通红地瞪着大姨,“是我记错了,还是你失忆了?那一笔笔的医药费单子,现在还压在我箱子底!我一个人跑上跑下,求爷爷告奶奶,借遍了所有亲戚朋友,你在哪儿?你王秀敏,我的好姐姐,你在哪儿?!”
“我……”大姨被问得节节败退,脸色愈发苍白。
“姐,你别说了!”舅舅突然打断了我妈,他扶着大姨的胳膊,声音里带着一种绝望的疲惫,“让她说,让她自己说。”
他看向大姨,眼神里满是心疼和鼓励:“姐,说吧。都到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你再不说,就真没机会了。”
“没机会”这三个字,像一个开关,让大姨原本涣散的眼神重新聚焦。她深吸了一口气,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抬起头,直视着我妈的眼睛。
“秀英,当年的事,是我不对。钱……钱确实是被你姐夫拿走了。”她艰难地开口,每一个字都说得异常沉重,“他当时生意失败,被人追债,他说就用几天,有了钱马上就还。我信了他……我没想到,他拿着钱,就再也没回来。”
我妈冷哼一声,显然对这个解释嗤之以鼻。
“他跑了,你不会来找我吗?你不会告诉我实情吗?”
“我怎么说?”大姨的泪水流得更凶了,“我有什么脸说?那笔钱是妈的救命钱,是我亲手交给他的。他跑了,钱没了,我怎么跟你交代?怎么跟妈交代?我去找过他,我找了很久,可我找不到……我当时……我当时真的想死的心都有了。”
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无尽的悔恨和痛苦,那种绝望,即便是隔了二十年,依然能让人感同身受。
“所以你就躲着?妈住院你不来,甚至妈走了,你都没露面?”我妈的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但依旧充满了质问。
“我不敢……”大姨低下头,声音细若蚊蚋,“我怕看见你,我怕看见妈。我每天都在想,如果不是我,妈是不是还能多活几年……这份债,我背了二十年,秀英,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一闭上眼,就是妈躺在病床上的样子,就是你哭着求我的样子……”
她捂住脸,肩膀剧烈地耸动起来,压抑的哭声从指缝里漏出来,听得人心都碎了。
客厅里,只有她的哭声在回荡。
我妈站在原地,紧握的拳头慢慢松开了。她脸上的愤怒和嘲讽,也一点点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茫然和怔忡。她大概从来没有想过,在那个她恨了二十年的故事背后,还藏着这样一番隐情。
舅舅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递到我妈面前。
“姐,你看看这个吧。”
我妈迟疑了一下,还是接了过来。她展开那张纸,那是一张医院的诊断证明。
我凑过去看了一眼,上面的字像针一样扎进我的眼睛——“胰腺癌,晚期”。
名字那一栏,赫然写着:王秀敏。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妈也愣住了,她拿着那张薄薄的纸,手却在微微发抖。她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瘦弱、憔悴,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的女人。
“这……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她的声音干涩,完全没有了刚才的盛气凌人。
“查出来三个月了。”舅舅的声音低沉而悲伤,“医生说,……没多少时间了。化疗做了两次,人受不了,就不做了。她这几天,精神稍微好点,就一直念叨着,说想见你一面。说有些话,再不说,就带进棺材里了。”
“她怕你一辈子都恨着她,怕妈在底下也不安生。所以,姐,我今天就是绑,也要把她绑过来。你们姐妹俩的结,再不解开,就真的没机会了。”
舅舅的一番话,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千层浪花。
我妈呆呆地看着那张诊断证明,又看看大姨。她的嘴唇翕动着,似乎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二十年的怨恨,在这一张轻飘飘的纸面前,显得那么苍白,那么可笑。
你恨一个人,是因为她还好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还有恨的对象。可如果这个人,马上就要消失了呢?你那些刻骨的恨意,又该去向何方?
大姨似乎哭累了,她慢慢止住哭声,用手背擦了擦脸上的泪,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秀英,别听建国的。我今天来,不是来求你原谅的。”她看着我妈,眼神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我就是想来……跟你告个别。”
“当年的事,是我糊涂,是我懦弱。我没脸求你原谅。这二十年,你就当我这个姐姐已经死了吧。今天见过你,见过小静,我……我也就没什么牵挂了。”
她顿了顿,从随身带着的布包里,颤颤巍巍地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递给我妈。
“这个……你拿着。我知道,这点钱,跟当年妈的医药费比,什么都不算。这是我这些年打零工攒下来的,还有我儿子给我的。你……你就当是我,还给妈的吧。”
我妈没有接。
她只是死死地盯着大姨,眼睛里翻涌着我从未见过的复杂情绪。那里面有震惊,有悲伤,有悔恨,还有一丝丝的……心疼。
“你……为什么不早说?”许久,我妈才从牙缝里挤出这么一句话。
“说了……又有什么用呢?”大姨惨然一笑,“说了,妈就能活过来吗?说了,你失去的那些年,就能回来吗?秀英,错了我认。我今天来,真的,就是想再看你一眼。”
说完,她把那个手帕包放在了餐桌上,转身,蹒跚着向门口走去。
“姐!”舅舅急忙喊道。
大姨没有回头,她只是摆了摆手,拉开了门。
就在她一只脚即将迈出门槛的时候,我妈突然开口了。
“等一下。”
第4章 一锅酱肘子
大姨的脚步顿住了。她没有回头,只是僵硬地站在那里,背影在夕阳的余晖里被拉得很长,显得格外孤单和脆弱。
我妈看着她的背影,嘴唇动了动,似乎有很多话想说,但最终,千言万语都化作了一句。
“吃了饭再走吧。”
她的声音不大,甚至有些沙哑,但在寂静的客厅里,却清晰地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
大...姨的肩膀微微颤抖了一下。她慢慢地转过身,脸上满是泪痕,眼神里带着不敢相信的错愕。
舅舅也是一脸的惊喜,他激动地看着我妈,嘴里不停地说:“哎,哎,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嘛!”
我妈没有理会他们,她只是默默地转身,从碗柜里又拿出了一副碗筷,放在大姨刚才站过的位置旁边。然后,她走进厨房,不知道在翻找着什么。
客厅里的气氛,因为这突如其来的转折,变得有些微妙。尴尬和压抑依然存在,但那层坚冰之下,似乎有了一丝融化的迹象。
我赶紧站起来,拉着大姨的手,把她重新按回到餐桌旁的椅子上。“大姨,您坐,您坐。”
她的手很凉,也很粗糙,布满了老茧。我这才意识到,原来她这些年过得并不好。
舅舅也坐了下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像是打了一场筋疲力尽的仗。
很快,我妈从厨房里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硕大的猪肘子,还有一个砂锅。
“家里没什么菜了,就随便吃点吧。”她一边说,一边把猪肘子放进砂锅里,又加了水和各种调料,开火炖上。
我愣住了。那是我家只有在过年或者招待最重要的客人时,才会做的压轴大菜——酱肘子。
而且,是姥姥的方子。
我小时候最喜欢吃姥姥做的酱肘子,肥而不腻,软糯香甜。姥姥去世后,我妈研究了很久,才勉强做出了七八分相似的味道。她说,这味道,是留个念想。
今天,她竟然要做这道菜。
大姨看着我妈在厨房和客厅之间忙碌的身影,眼神也变得恍惚起来。她喃喃自语道:“是……妈做的那个酱肘子……”
“嗯。”我妈应了一声,没有回头。
那顿饭,吃得异常沉默。餐桌上只有三道菜,一道红烧肉,一道临时炒的青菜,还有就是那锅正在“咕嘟咕嘟”炖着的酱肘子。
谁也没有说话,只有碗筷碰撞的轻微声响。
我妈给我和大姨、舅舅都夹了红烧肉。大姨看着碗里的肉,迟迟没有动筷子,只是端起饭碗,小口小口地扒着白饭。
我看到,她的眼泪又一次掉了下来,一滴一滴,落进米饭里。
我妈看到了,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吃着自己的饭。
一顿饭,吃了将近一个小时。那锅酱肘子,因为炖的时间不够,还不够软烂。我妈用筷子戳了戳,皱了下眉,说:“还不行,得再炖会儿。”
饭后,舅舅说要先走,他公司还有点事。临走前,他把我妈拉到一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我看到我妈不停地点头,脸色凝重。
送走舅舅,屋子里就只剩下我们三个人。
我和大姨坐在沙发上,我妈在厨房里洗碗,水流的“哗哗”声,掩盖了客厅里的尴尬。
“小静,学习……还好吗?”大姨小心翼翼地找着话题。
“大姨,我已经工作好几年了。”我笑着说,想让气氛轻松一点。
“哦,哦,对,工作了,看我这记性。”她局促地笑了笑,“在哪儿工作啊?累不累?”
我们就像两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努力地进行着客套而生疏的对话。我跟她讲我的工作,讲我的生活,她就安静地听着,时不时地点点头,眼神里充满了慈爱和……愧疚。
我妈洗完碗,从厨房里出来,手里端着一盘切好的西瓜。
“吃吧。”她把果盘放在茶几上,自己也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她和大姨之间,隔着一个茶几的距离,不远,也不近。
“秀英,这些年……你一个人带小静,辛苦了。”大姨看着我妈,轻声说。
我妈拿起一块西瓜,咬了一口,没有看她。“不辛苦,我自己的女儿,应该的。”
“小静爸……他……”
“走了,好几年了。”我妈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别人的事,“肝癌,跟你一样。”
大姨的身体猛地一震,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没什么。”我妈又咬了一口西瓜,汁水顺着她的嘴角流下来,她用手背随意地擦掉,“人各有命,都是注定了的。”
她的平静,反而比任何激烈的情绪都更让人感到悲伤。我这才意识到,这些年,我妈一个人撑起这个家,到底经历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苦楚。
“对不起……秀"英,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大姨的声音里带上了哭腔。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我妈放下西瓜皮,终于抬起头,正视着她,“你能替他疼,还是能替我还债?”
她的语气依旧很硬,但眼神却软了下来。
“我不是怪你。我就是觉得……不值。”我妈的声音低了下去,“王秀敏,咱们是亲姐妹,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当年妈的事,钱是小事,你的人在哪儿?你哪怕回来,跟我说一句实话,跟我一起想办法,我们一起扛,天大的事儿也能过去。可你呢?你选择了躲。你这一躲,就是二十年。”
“你知不知道,妈临走的时候,还在念叨你的名字?她不恨你,她就是想你。”
“我恨你,不是因为钱,也不是因为你没照顾妈。我恨你,是因为你把我们当外人!你宁可一个人扛着,一个人躲着,也不愿意相信我们,不愿意回来!你觉得我们是会吃了你,还是会把你逼死?”
我妈越说越激动,眼圈也红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剖白自己的内心。原来,她恨的不是背叛,而是隔阂。她怨的不是无情,而是不信任。
大姨早已泣不成声。她捂着嘴,拼命地摇头:“我不是……我不是不信你们……我是没脸……我没脸回来啊……”
两个年过半百的女人,隔着一张茶几,相对而泣。
二十年的冰山,在这一刻,终于开始崩塌。
第5章 和解
厨房里,那锅酱肘子还在小火慢炖着,香气愈发浓郁,飘满了整个屋子,像一只温柔的手,试图抚平这迟到了二十年的伤痛。
哭过之后,客厅里的气氛反而没有那么紧绷了。我妈和大姨都沉默着,像是耗尽了所有的力气。她们不再看对方,只是各自望着虚空中的某一点,眼神里都带着一种如释重负后的疲惫。
我起身,给她们俩一人倒了一杯温水。
“妈,大姨,喝点水吧。”
我妈接过来,没说话。大姨颤抖着手接过水杯,对我说了声“谢谢”。
“姐,”我妈突然开口,声音还有些嘶哑,“你那病……真的没法治了?”
大姨捧着水杯,低着头,轻轻地“嗯”了一声。
“医生说,发现得太晚了。现在……就是熬日子。”她的语气很平静,仿佛在说别人的事。这种平静,比任何声嘶力竭的哭喊都更让人心碎。
我妈沉默了。她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看了很久。
“以后……有什么打算?”她问。
“没什么打算。我儿子想接我去他那儿,我不想去,不想给孩子们添麻烦。”大姨说,“我就想在老房子里待着,哪儿也不去。”
“一个人?”
“嗯。”
我妈又沉默了。她端起水杯,喝了一口,然后站起身,走到厨房门口,看了看那锅肘子。
“差不多了。”她说。
她把火关掉,用筷子捞出那个炖得酥烂的肘子,放在案板上。肉香瞬间在空气中爆炸开来,是那种久违的、带着记忆温度的香气。
我妈没有像往常一样把肘子切块,而是找了一个大盘子,把整个肘子完整地盛了进去,然后淋上锅里浓稠的汤汁。
她把盘子端到大姨面前。
“尝尝。”她说,“看还是不是妈那个味儿。”
大姨看着眼前的酱肘子,眼泪又一次涌了上来。她拿起筷子,夹了一小块颤巍巍的肉皮,放进嘴里。
肉皮入口即化,咸中带甜,正是记忆深处的味道。
“是……是这个味儿……”她一边嚼,一边含混不清地说,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我妈看着她,眼圈也红了。她自己也夹了一块,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
“盐……放多了点。”她说。
“没有,正好。”大姨说。
那一刻,她们之间不再有怨恨,不再有隔阂。她们只是两个都在思念母亲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儿。一盘酱肘子,成了连接她们过去和现在的桥梁。
“以后,别一个人待着。”我妈放下筷子,看着大姨,一字一句地说,“搬过来住吧。”
我愣住了。
大姨也愣住了,她猛地抬起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儿……地方大,你住我那屋,我跟小静挤一挤。”我妈的语气不容置疑,像是在宣布一个决定,而不是在商量,“我照顾你。”
“不……不行,秀英,这怎么行……”大姨慌忙摆手,“我这病……会拖累你的……”
“我乐意。”我妈打断她,“我老公我送走的,我妈我也送走的,不差你一个。王秀敏,我告诉你,这二十年,你欠我的,这辈子还不清了。下辈子,你也得给我当牛做马地还。”
她的话说得又硬又冲,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听着却想哭。
我知道,这是我妈的方式。她不会说软话,不会说“我原谅你了”,更不会说“姐姐我心疼你”。她只会用这种最笨拙、最强硬的方式,表达她的接纳和关心。
这是她们姐妹之间,独有的和解方式。
大姨看着我妈,嘴唇哆嗦了半天,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是拼命地点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那天晚上,大姨没有走。
我妈把她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换上了新的床单被罩。我帮着大姨整理她带来的那个小布包,里面只有几件换洗的旧衣服,还有一个小小的相框。
相框里,是年轻时的我妈、大姨和姥姥的合影。照片上的她们,笑得那么灿烂。
第6章 最后的时光
大姨在我家住了下来。
起初的日子,是充满了小心翼翼的。大姨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总是抢着干活,扫地、擦桌子,甚至想帮我妈做饭。但我妈总会板着脸把她按回沙发上。
“你给我老实待着!一身的病,还想逞能?”
大姨就不敢动了,只是坐在那里,目光追随着我妈忙碌的身影,眼神里充满了感激和依赖。
我妈的脾气还是那样,说话又冲又硬,但她的行动却无比温柔。她开始研究各种适合癌症病人的食谱,每天变着花样给大姨做好吃的。她会记得大姨吃药的时间,会扶着她在小区里慢慢散步,会陪着她看那些家长里短的电视剧。
她们的话依然不多,但屋子里的气氛却不再冰冷。有时候,她们会一起坐在阳台上晒太阳,一句话也不说,就那么静静地坐一个下午。阳光洒在她们斑白的头发上,有一种岁月静好的安详。
有一次,我下班回家,看到她们俩在看一本旧相册。那是我家的相册,里面有很多我小时候的照片。
“你看这丫头,小时候多胖,脸圆得跟个盘子似的。”我妈指着一张照片,对我大姨说。
“是啊,真可爱。”大姨笑着,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了,“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
“像我?她才不像我。我小时候可比她机灵多了。”我妈嘴上嫌弃着,嘴角却忍不住上扬。
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鼻子一酸,差点掉下眼泪。
我从没想过,有一天,能看到她们如此平和地坐在一起,谈论着过去。那堵隔绝了她们二十年的墙,真的消失了。
大姨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癌细胞的扩散让她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但她的精神状态,却比刚来的时候好了很多。她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眼神也不再是躲闪和怯懦的,而是充满了平和与坦然。
她开始给我讲她过去二十年的生活。姐夫跑了之后,她一个人打好几份工,拉扯着儿子长大。她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但她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
“那时候,就觉得没脸见人。尤其是没脸见。”她说,“觉得是自己把一切都搞砸了。越是这样,就越不敢回来。”
我问她:“那您恨过我妈吗?她那么多年对您不闻不问。”
大姨摇了摇头,笑了。
“不恨。我知道她的脾气。她就是那样,心里比谁都软,嘴上比谁都硬。她恨我,是因为她在乎我。要是不在乎,她连恨都懒得恨。”
我突然就懂了。原来,恨的背面,是爱。是因为爱得太深,所以无法容忍任何的背叛和隔阂。
大姨在我家住了三个月。
最后一个月,她已经下不了床了。我妈一天二十四小时地守着她,喂她吃饭,帮她擦洗,像照顾一个婴儿一样,无微不至。
大姨走的那天,是个晴朗的清晨。
她把我妈叫到床前,拉着她的手,说了最后一句话。
她说:“秀英,对不起。还有……谢谢你。”
我妈握着她渐渐冰冷的手,没有哭。她只是静静地看着她,看了很久很久,然后俯下身,在她耳边轻轻说了一句:“姐,不疼了,好好睡吧。”
大姨的葬礼上,我妈异常地平静。她没有掉一滴眼泪,只是有条不紊地处理着所有的后事。
我知道,她不是不悲伤。她只是把所有的悲伤,都埋在了心里。
葬礼结束后,我们回到家。家里还保留着大姨住过的痕迹,她的水杯,她的拖鞋,阳台上她坐过的那把藤椅。
我妈走进厨房,打开冰箱,拿出了一块猪肘子。
她像那天一样,开始默默地炖起了酱肘子。
这一次,她炖了很久很久,直到肉烂如泥,香气飘满了整个屋子。
她盛出两碗,一碗放在我对面,一碗放在自己面前。
我们俩谁也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吃着。
我尝了一口,味道刚刚好,不咸不淡,是我记忆中姥姥做的味道。
吃着吃着,我妈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一滴,两滴,落进碗里,和浓郁的汤汁混在一起。
她没有哭出声,只是任由眼泪无声地流淌。
我走过去,从身后轻轻地抱住了她。她的肩膀在微微颤抖。
“妈,都过去了。”
她点了点头,哽咽着说:“小静,妈就是觉得……可惜。二十年啊……要是能早点……早点说开,多好……”
是啊,多可惜。
人生有多少个二十年,可以用来置气,用来隔阂,用来等待一句迟到的“对不起”?
大姨走了,但她也留下了一些东西。她让我和我妈都明白了,家人之间,没有什么结是解不开的。最可怕的不是争吵和矛盾,而是沉默和逃避。沟通和理解,远比那可笑的自尊和固执重要得多。
从那以后,我妈好像变了一个人。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紧绷着,脸上的线条柔和了很多。她开始主动联系那些多年不走动的亲戚,甚至会笑着跟我舅舅开玩笑了。
我知道,是大姨的离去,彻底砸开了她心里的那堵墙。墙塌了,阳光才能照进来。
又是一个周末,我和我妈一起,又做了一锅酱肘子。
我们把肘子装在保温桶里,去了墓地。
在姥姥和大姨的墓碑前,我们摆上了两副碗筷。
我妈把肘子夹到碗里,轻声说:“妈,姐,吃饭了。尝尝我做的肘子,看还是不是那个味儿。”
山风吹过,松涛阵阵,像是在回应她。
我看着我妈的侧脸,阳光下,她的白发显得格外刺眼。我知道,她心里的那个结,已经彻底解开了。虽然代价是如此沉重,但终究,是和解了。
和死去的姐姐和解,也和那个固执了半生的自己,和解了。
文档上传者
热门标签
相关文档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