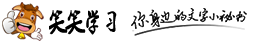欢迎来到98聘
3招搞定《海边作文结尾》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7-25 15:26

写作核心提示:
请求出错,状态码:0内容:
台湾小说家黄丽群:《海边的房间》结尾会让读者倒吸凉气
第一次见她是好几年前在台北了,在政治大学教书的同时也是非常好的作家朋友柯裕棻特意安排了一个饭局,请了一些朋友一起吃饭,席间就有丽群。我后来才知道,丽群与柯老师是死党中的死党。那次饭局上丽群话并不多,结束时她站起来我才吓一跳,没成想她个子居然那么高。台湾本省女生大多小巧玲珑,柯裕棻的个子已经算里面高的,我偷偷猜想那是因为她父亲是外省人,而丽群的个子比裕棻更高。丽群送了我一本她那时出版不久的新书《海边的房间》,扉页上写着“祝日日甜蜜”。
大约是过了两年左右,依然是台北,和天心老师闲聊台湾新生代作家时,她提到了黄丽群。“我很喜欢黄丽群的小说!”“很”字加了重音。回到北京后,我立即找出了《海边的房间》,连着几天读完,后悔为何没早一点读一读。这本书的其中一篇前言正是柯裕棻所写,那前言也写得极好,她已将我想说的全部涵盖其中——“资质秾艳幽美,可是那美里面暗暗渗着凉气。她的文字温煦如日,速如风雨。晴日静好的午后,还觉得太平岁月温暖快乐,一转眼,不知哪来的乌云罩顶,大雨倾盆落下。”
不管是丽群还是裕棻,在那次饭桌上见面时,谁都没有刻意提及这本短篇小说集有多好。她们只是将这样一本书递到我手里,完成一种交接仪式,不给人任何压力,亦不会事后跑来问阅读后的感受,这种礼貌与周到,反倒是在台湾作家那里我一次次体会到,却也担心他们会不会因此而失掉可能的聚焦与关注。
虽然扉页上写着“日日甜蜜”,但《海边的房间》里的每一篇小说都总让我读到结尾会倒吸一口凉气,她语言是俏皮的,但故事却总是让人们感觉到冰冷,这里面形成强烈张力,每一篇都好看,我总与人讲丽群的小说,是我视线所及,台湾年轻一代书写者里最好看的。她的小说和她的外表,真的是非常不一样呢(丽群是个长得很甜美的女生)。
读完书我立即给丽群发了一封邮件,说了我读这本书的一些感受,表达了强烈的赞叹,她礼貌道谢,言语中都是自谦。太多赞誉反而成了一件让她惶恐的事,她很多次公开表达“作家”的身份让她感到不安和尴尬。“我会觉得,如果没有办法写到像马尔克斯那样,就不能算会写。”
事实上,黄丽群和大多数台湾作家一样,并非全职写作,她曾经是一个时尚记者,现在也依然在媒体圈里工作,平日里常聚在一起的作家朋友非常少,几乎很少在“圈子”里露面。当然也有例外,今年5月丽群来了一趟北京,参加两岸作家的一个研讨会。这种活动她第一次参加,也算是“开了眼界”,对中国作协的运作机制她也是满满好奇。“在台湾,书写者如果是职业作家的话,不会有收入保障,我们都是各自求生。我觉得写作是面向自己的一件事,我似乎是为了解决我自己的内在拉锯、矛盾和不知所措。”在单向空间的活动上,她曾这样说。
活动间隙我将她与黄崇凯一起带出来闲逛半日,二人在三联书店各自扫货若干,而且都买了不少大陆作家的作品。闲谈间听到他们对大陆作家的许多评价反倒是让我很惊讶,首先是他们读得真的够多,不仅仅读名家,也读很多年轻的尚未出名的作品。其次是他们看这些作品的角度和我会有非常大的不同,比如在我眼里很多大陆作家作品里的文学性欠佳是短板,但是在丽群的眼中,很多作品里叙述的让她难以想象闻所未闻的故事已经够让她消化好久。很多时候,丽群提供给我了另一种新的视角去看待大陆的文学作品。而另外一方面,大陆作家愿意花工夫去研究台湾作家作品的人却并不多,在互相认识上,其实存在着某种不对等性。
那日在三联扫货完毕后,我们又一起在北京的胡同里乱走。丽群讲起自己祖母是北京人,只可惜自己与还在这边的亲戚已经不大有联系。她很爱猫,家里的猫已经养了近20年,每每见到四合院里有猫,她总会蹲下来和它们聊天说话。“哦,这样哦!”“好的,知道啦!”她如猫女般,猫也都对她恋恋不舍,似乎两个物种间已无语言差别。
就这样边吃边逛到晚上,将她送回酒店,中间崇凯因为缺觉先行回了酒店。我和丽群一路上依然聊文学,聊各自喜爱的作家,也聊各自不喜爱的作家。车子停在酒店门口,我们竟然又待在车子里聊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夜已深,不得不说再见。
《海边》:“父亲”作为一个角色,一种结构,一个象征
◎曹申堃
上月,由加拿大导演瓦吉·穆阿瓦德执导的作品《海边》作为北京人艺国际戏剧展受邀剧目,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的曹禺剧场上演。此前,该戏也在今年的乌镇戏剧节上与观众见面,收获了热烈反响。
赋予“老戏”新意涵
瓦吉·穆阿瓦德(WadjiMouawad)1968年出生于黎巴嫩。在他八岁时,为了躲避黎巴嫩内战举家移居法国,之后迁居加拿大蒙特利尔。穆阿瓦德著作颇丰,还是一位“多边形战士”,在各领域都有着不俗的成绩:他写过小说、广播剧,做过剧场作品,导演过电影,同时还是多栖演员;其戏剧剧本《焦土》曾被加拿大当红电影导演、执导《沙丘》系列的丹尼斯·维伦纽瓦改编成为《焦土之城》,并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海边》(Littoral)最初于1997年在美洲戏剧节上由魁北克的创作团队演出,2007年成为巴黎国立高等戏剧艺术学院学生的毕业作品;2009年,魁北克团队重新创作了新版本,以《海边》《焦土》和《丛林》三部曲形式在阿维尼翁戏剧节上呈现。2016年以来,穆阿瓦德在法国巴黎柯林国家剧院担任总监,此次来华展演的《海边》,正是由该剧院根据2009年出版的剧本于2020年推出的复排版本,时长将近三个小时。
这一版《海边》由两部分构成,前半部分主要围绕主人公威尔弗里德展开。自威尔弗里德一出生,父亲就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而父亲的去世,让父子不得不重新发生关联。他准备将父亲与早年去世的母亲一起合葬,但遭到舅舅的强烈反对。威尔弗里德这才了解母亲去世和父亲多年失联的原因。后半部分,深陷困扰的威尔弗里德决定将父亲的遗体运至故乡安葬,然而遥远的故乡已经满目疮痍,墓地人满为患,父亲的亲属也拒绝接受这具遗体。威尔弗里德自此携遗体开启一段旅程,途中遇到了经历着悲痛的、愤怒的年轻女孩西蒙娜。之后,许多同龄人加入到这个队伍中,这些女性每个人都经历着不同却又相似的现实,并将威尔弗里德死去的父亲视为她们每个人失去的亲人的象征。
穆阿瓦德最初创作《海边》时显然是基于他个人在战乱中的经历、见闻和思考。这出戏毕竟已有将近30年的历史,穆阿瓦德本人坦言自己并未想过要不断重启《海边》复排。然而在2020年,剧中父亲的死亡、故乡的尸横遍野似乎又被新的现实赋予了新的意涵。在这样的契机下,作为剧院总监的穆阿瓦德开始思考,是否能以这出“老戏”挽救剧场、悼亡逝者。
谦虚地对待未来
穆阿瓦德在为柯林国家剧院复排版《海边》撰写的缘起文章中说,“天使悄无声息的一步总是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到来,有时你不得不倾听它的脚步。生活在嘲笑我们,而我们能做的就是陪着它笑,或者至少不要太敏感。当下变得如此不稳定,这是我们必须学会热爱的现实。”饶是如此“热爱现实”,创作者本人肯定也没有想到,距离本次复排不到四年时间,这出戏又有了更加迫切的现实意义:巴以冲突让中东再次陷入兵燹,给人感觉情况并没有进步,以至于“常看常新”这个词不知道应该被视为一种对创作者先见之明的恭维,还是一种对世界的巨大讽刺。
“对未来要谦虚。我们不能对未来做过多的假设,而是要利用我们现有的一切,重新发现戏剧的特别之处。”应该说,《海边》之所以“历久弥新”,除了偶然的客观因素之外,也不乏很重要的主观创作因素作为保证:它并没有基于特定时间地点和历史事件进行书写,比如戏中从未指明“故乡”到底是哪里、“战争”到底指哪场。所以,观众既可以将《海边》锚定在20世纪40年代的欧洲,也可以把它揳入冷战的历史框架,抑或将其置入当下世界各地局部热战的语境,这样也就避免了将时代的特殊性放大到过分的地步——实现了某种对未来的谦虚。
不过这样一来,创作者也必须要考虑剧作本身是否会变得过于悬浮、轻佻,无法切中现实要害。于是,将目光锁定在个体的、真实具体的创伤性经历上,成为某种必然的选择。一方面,对于穆阿瓦德来说,似乎战争中更重要的并非是哪几方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观众要搞懂的也绝非是几股力量之间到底如何拉锯,而是具体的个体平民面对了什么样的生死离别,这种人道主义灾难在任何一场战争当中都是必然存在,却往往被忽视,也值得被书写的。另一方面,无论是戏的前半程中舅舅讲述的母亲去世的真相,还是后半程女性角色的歌唱、狂怒和大笑,都把女性面对的牺牲和结构性失声特别强调出来,为书写历史时容易出现的个体经验缺失提供了解决方案。因此我们可以说,《海边》既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既关乎时代中人的特殊命运,也的确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超越时代、国家的边界,抵达万里之外的观众,使他们有一些收获和共鸣。
观众获得创作者的
事实上,自从《海边》剧本出版以来,其他国家的剧院也在排演自己的版本,比如韩国世宗文化会馆就在今年年中上演了该剧。从演出资料上看,各版本的舞美都比较传统。但穆阿瓦德此次带来的版本几乎摒弃了一切非必要的舞美手段,以一种极其简约的方式呈现。首先,舞台设置简洁、透明,大幕拉开时是空无一物的“黑箱”,直到演员走上舞台,两两一组用白色胶带围出边框,演出区域才就此划定;接下来,服装和桌椅“从天而降”,迅速建立起假定性和扮演的原则。舞台空间和演员的身体成为两种本质性的剧场要素,其他一切只是对二者起到修饰的作用;环境和角色如同皮肤一样披罩在演员身上,在假定性的原则公式支配下,演员的身体可以随时剥离、进入。简而言之,穆阿瓦德不是要为观众营造某种完全确切可见的、沉浸可感的氛围,而是要让观众运用自己的想象,主动地参与到情境的创造之中。
同时他也意识到,这种假定性并不应该成为某种默认的、潜在的、操纵性的规则,它应该成为一种可以被言说的、透明化的机制,甚至可以被不时打破。比如在父亲的追悼会上,主人公威尔弗里德母亲一方的亲属悉数到场,女性家属纷纷走向舞台左侧,表示自己已经来到了墓地,而舅舅则站在台右,拒绝已经被舞台上的演员甚至观众共同认可的空间变换。立于台左的角色不断劝说,舅舅终于同意“来到”墓地,然而这一空间的变化并没有实质性地在舞台上通过舞美、服装道具的变化展现出来;相反,台上的一切纹丝未动,所有的变化只是发生在观众的脑海当中。在这样的方式中,观众获得了创作者的信任和,进而也可以顺畅地浸入之后的情节当中。
一连串人名被说出的意义
《海边》的后半段与其说是一场“奥德赛”,不如说更像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二者都是由集体创作、收集而成,都是由女性讲述,所有这些没有确定头尾的经历都是以连缀的形式进行组织,接着又被一个更外层的故事——威尔弗里德寻求安葬父亲的故事所包裹起来。在这里,“父亲”既是一个角色,也是一种结构,更是一个象征;“父亲”最终之所以获得某种平静,并非因为他被凝固在了确定的死亡之中,而是因为他的身上绑缚了无数个亡者的存在,是沉重的战争和苦难让他获得了无数倍的重量。如果说“土地+死亡”意味着分离,那么“海洋+死亡”则意味着一体。于穆阿瓦德而言,“安息”只能完成于一个更加宽大的、世界性的怀抱,在那里,人们不会基于不同的原因死去,他们只是因为苦难死去,而苦难也是每个人的必然宿命。
全戏结尾,当一连串的人名如潮水一般向观众涌来时,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人名本身对观众而言只是一串无意义的字符,但其被挨个说出,却有着十足的意义——它使得整部戏成为一段集体的、公共的记忆,成为一个必须完全经历的悼亡仪式,成为一座非物质的纪念碑。每个亡者的墓志铭是如此短小,但也如此确凿,他们的一生似乎足以被一句简短的话语所概括,因着这一句话的存在而十分渺小,也因着这一句话的存在而得到救赎与永恒。供图/北京人艺
文档上传者
热门标签
相关文档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