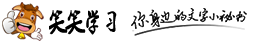欢迎来到98聘
写作《写老师外貌的作文》小技巧请记住这五点。(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11-18 08:57

写作核心提示:
下面我将为你写一篇关于描写老师外貌的作文,并在这篇作文后面附上写作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
"作文:我的老师——王老师"
在我们求知的道路上,遇到过许多老师,他们或学识渊博,或循循善诱,或热情洋溢。而在我记忆的长河中,王老师那独特的风采,总是清晰而温暖地印刻着。她不仅是我的授业恩师,更是我心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王老师大约四十多岁,中等身材,常年梳着一头利落的短发,看起来干练而精神。她的头发或许曾经乌黑,但岁月和工作的辛劳,在鬓角悄悄染上了一缕不易察觉的银丝,那是智慧的印记,也是她为我们付出的证明。她总是戴着一副轻薄的细框眼镜,镜片后面,一双眼睛显得格外明亮、透彻。那双眼睛,时而像深邃的湖水,平静地容纳着一切;时而又像闪烁的星辰,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和关爱我们的温度。她看我们的时候,眼神总是专注而温和,仿佛能穿透我们内心的迷茫,找到我们最需要的那份鼓励。
王老师的脸庞线条柔和,鼻梁挺直,嘴角总是微微上扬,带着一种令人安心的微笑。这微笑,像春风拂过,能瞬间化解我们学习中的焦虑和压力。她的皮肤略显苍白,或许是因为长期伏案工作的原因,
【五年级作文】邵菀然《“漫画”老师——我的吴老师》
【优秀作文展】“漫画”老师五年级上册二单元作文
【思维导图“画”作文——五年级作文】邵菀然《“漫画”老师——我的吴老师》(三十八)
老师,林妙可 - 妙妙妙桃李满天下《“漫画”老师》习作指导
妙笔生花,我会写: 我们知道习作一般要解决两个问题,即写什么和怎么写。“漫画”老师是本次习作的话题,意思是用文字突出老师的特点。 课标要求习作要做到内容具体、感情真实。本单元要素指出:结合具体的事例写出人物的特点。所以要结合具体事例来写。将抓特点、选事例、写具体、用夸张,四位一体,顺学而导,逐层推进,把老师“画”丰满,突出人物特点,突破教学重难点。《“漫画”老师》是统编教材五年级上册第二单元习作 “漫画”老师是统编教材五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的习作。我们知道习作一般要解决两个问题,即写什么和怎么写。“漫画”老师是本次习作的话题,意思是用文字突出老师的特点。所以,本次习作写什么?老师突出的特点。怎么写?课标高年段学段目标要求习作要做到内容具体、感情真实。本单元语文要素指出:结合具体的事例写出人物的特点。所以要结合具体事例来写。 突出人物特点是目的,结合具体事例是手段。因此,如何抓住老师的突出的特点?怎样把事例写具体?是需要突破的两个重要的问题。另外,既然是“漫画”老师,就不是一般地写老师,要运用夸张的手法,幽默的语言,突出老师的特点,要把老师“画”得丰满、鲜活、有趣。 漫画式的语言风格也是本次习作需要突破的又一个重要的问题。
掌握好方法,你就能把习作写得很精彩!01抓特点,选人物写作时要抓住最有特点的一个方面写,比如外貌描写,每个人的外貌都有与众不同的特点。通过外貌描写,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内心活动,千万不能面面俱到。
02定事情,显特色人物的特点要通过具体的事情来体现,事情的选择一定是与人物的特点一致的,比如上面觉得喜好独特,此处事情选择也要突出喜好独特这个特点,不能前后不一。
03重描写,表情感通过人物在事件中表现,如动作、语言、神态、心理活动等使它构成整个情节的最典型的部分,突显人物的特点,使文章显得生动真实,从而表达老师可爱又有趣的一面。
图文解读
思维导图思维导图又叫心智图,是把我们大脑中的想法用彩色的笔画在纸上。它把传统的语言智能、数字智能和创造智能结合起来,是表达发散性思维的有效图形思维工具。简单地说,思维导图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更加有效地将信息“放入”你的大脑,或者将信息从你的大脑中“取出来”。
教育部官网助推【思维导图】教学成果“双减”政策下,学校和家长更应该着重于培养学生思维导图学习能力。将思维导图真正融入生活,不仅要学习思维导图,而要生活在思维导图中!教育改革的本质不是学习目标减下去,是核心素质提上来!学习能力提升,学习效率提高! 把思维导图的思考方式变成自己的财富!思维导图把思考过程可视化!把思维导图画下来,就可以非常直观,清晰地看到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种思维能力在小学阶段刻意训练最好,在初中阶段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将所学知识分门别类地纳入大脑知识储备体系。 愿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喜欢、擅长的事情上有所坚持、有所成就,拿出勇气自我成长,每天遇见更好的自己。
“漫画”老师——我的吴老师 小学五年级 邵菀然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遇到过许多老师,他们如同繁星点缀在我的记忆天空中。然而,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我们现在的班主任——吴老师。 吴老师拥有一张瓜子脸,脸上镶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当她开心时,眼睛会弯成一道月牙,和谐极了!她的乌黑长发时而披散着,显得活力四射:时而高高扎成一个马尾,显得精明干练。她在夏天常常穿着美丽又大方的裙子,总是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 在课堂上,吴老师总是站在教室后方,专心致志地写教案或阅读一些富有哲理的书籍。午休时,她会一边品尝水果,一边观看平板电脑里的电视剧。看完电视剧后,她还会和父母视频聊天。课间时,她会给我们讲述她的旅行经历,讲得生动有趣。她也很喜欢拍照,总是在我们取得好成绩、参加升旗仪式或其他特别时刻时,留下珍贵的瞬间。 吴老师不仅是我们的班主任,还是一位即将成为母亲的女性。有一次,我在课堂上对一个知识点感到困惑,下课后我去请教吴老师。她耐心地和我讨论,一边讲解一边画图,还鼓励我:“如果还有不会的题目,随时来找我我喜欢和别人一起解决难题。” 吴老师不仅关注我们的学习,还关心我们的生活。有一次我生病请假,她打电话关心我的病情,告诉我不用担心课程,回校后会给我补课,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她。听到她温暖的关怀,我感到无比的力量。 吴老师就像一座灯塔,照亮我心中的方向:她如一缕春风,润物细无声;她更像一缕阳光,温暖着我们每一个人。我爱我的吴老师!
关注我们的作品学生作品,点击浏览:【优秀作文展】“漫画”老师(一)【优秀作文展】“漫画”老师(二)【优秀作文展】“漫画”老师(三)【优秀作文展】“漫画”老师(四)【优秀作文展】“漫画”老师(五)【优秀作文展】“漫画”老师(六)【优秀作文展】“漫画”老师(七)【优秀作文展】“漫画”老师(八)【优秀作文展】“漫画”老师(九)【思维导图“画”作文】“漫画”老师(十)【思维导图“画”作文】“漫画”老师(十一)【思维导图“画”作文】“漫画”老师(十二)【思维导图“画”作文】“漫画”老师(13)【思维导图“画”作文】谭奥《“漫画”老师》(14)【思维导图“画”作文】李墨轩《“漫画”老师》(十五)【思维导图“画”作文】姜奕西《“漫画”老师》(十六)【优秀作文展】“漫画”老师五年级上册二单元作文(十七)
【思维导图“画”作文——五年级作文】张梓佳《“漫画”老师》(十八)【思维导图“画”作文——五年级作文】周珈朵《“漫画”老师》(十九)【思维导图“画”作文——五年级作文】张诗杭《“漫画”老师——我的超人老师》(二十)【思维导图“画”作文——五年级作文】王欣然《“漫画”老师》(二十一)【思维导图“画”作文——五年级作文】李宣达《“漫画”老师——我的三原色老师》(二十二)【思维导图“画”作文——五年级作文】周唯《“漫画”老师——我的班主任老师》(二十三)【思维导图“画”作文——五年级作文】冯嘉瑞《“漫画”老师——我的“美”老师》(二十四)【思维导图“画”作文——五年级作文】吴邦赫《“漫画”老师——我的“三原色”老师》(二十五)【思维导图“画”作文——五年级作文】张钰涵《“漫画”老师——我的班主任老师》(二十六)【思维导图“画”作文——五年级作文】张奇《“漫画”老师——我的“美”老师》(二十七)【思维导图“画”作文——五年级作文】杨鸿安《“漫画”老师——我的班主任老师》(二十八)
【思维导图“画”作文——五年级作文】于皓轩《“漫画”老师——我的班主任老师》(二十九)【思维导图“画”作文——五年级作文】杨佳雯《“漫画”老师——我的“能”老师》(三十)【思维导图“画”作文——五年级作文】谷歌《“漫画”老师——我的班主任老师》(三十一)【思维导图“画”作文——五年级作文】刘艺涵《“漫画”老师——我的班主任老师》(三十二)【思维导图“画”作文——五年级作文】赵赫廷《“漫画”老师——我的“三原色”老师》(三十三)【思维导图“画”作文——五年级作文】王佳怡《“漫画”老师——我的班主任老师》(三十四)【思维导图“画”作文——五年级作文】王馨逸《“漫画”老师——我的班主任老师》(三十五)【思维导图“画”作文——五年级作文】王圣迪《“漫画”老师——我的“警察”老师》(三十六)【思维导图“画”作文——五年级作文】王丽娜《“漫画”老师——我的李老师》(三十七)
你若喜欢,别忘了点个在看哦 !点【在看】,和优秀且有趣的灵魂聊聊天,欢迎留言、点评。
那个爱穿白裙子的女老师,总在放学后叫我留下,说:你作文要加强
打开那本日记时,一股尘封的樟脑丸气味扑面而来。苏老师去世后,她的家人请我来帮忙整理遗物,说我是她最挂念的学生。我翻到夹着一片枯黄银杏叶的那一页,一行娟秀而又力透纸背的字,像一根烧红的钢针,瞬间刺穿了我三十年的记忆——“陈宇的作文还是那么灰暗,像他父亲出事那天的大雪。我必须把他拉出来,这是我欠他们家的。”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仿佛被重锤砸中。父亲出事……大雪……她怎么会知道?在我整个少年时代,那个总爱穿着一身白裙子,在放学后把我单独留下,用清冷的声音说“你作文要加强”的苏婉清老师,一直是我心里最怨恨的噩梦。可这一刻,这个噩梦的底色,似乎被这行字彻底颠覆了。而这一切,都要从我上初二那年说起。
01
这种丧气,完完整整地体现在了我的作文本上。别的同学写春天,是“春风像妈妈的手”,我写的是“化雪的泥路,脏得像我那双补了又补的球鞋”;别人写妈妈,是“最温暖的港湾”,我写的是“我妈那双被洗衣粉泡得通红起皱的手”。
班主任是个快退休的老头,对我这种“少年愁滋味”不闻不问,直到苏婉清老师作为新来的语文老师接管了我们班。她大概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是整个学校最亮眼的一道风景。她总喜欢穿一条洗得发白的棉布裙子,人长得清秀,像画里走出来的人,但眼神却总是清清冷冷的,带着一种和我这个年纪格格不入的疏离。
她来的第一周,就拿我的作文本在全班当反面教材。“这篇文章,辞藻够了,但思想是坍塌的。”她用指节叩了叩我的本子,发出沉闷的声响,“陈宇,放学别走,来我办公室。”
她看了,没说话,只是眉头皱得更紧了。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白瓷缸子,给我倒了杯热水,水汽氤氲了我的眼镜片。她说:“陈宇,你的眼睛,要往亮处看。”从那天起,“放学别走”成了我的专属魔咒。几乎每一天,我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学校的人。同学们都笑话我,说我是苏老师的“关门弟子”,背地里更是风言风语,说苏老师一个年轻女老师,老留一个半大小子,不知道图个啥。
我心里恨透了她。我觉得她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她一个城里来的、穿着干净白裙子的老师,怎么会懂我这种在泥地里打滚的孩子的苦?她让我写希望,写美好,可我的生活里,哪有这些东西?我越恨她,作文就写得越拧巴,越黑暗,像一种无声的报复。
02
那时的我,正是半夜都会饿醒的年纪。我妈为了省钱,晚饭总是稀粥配咸菜。那个鸡蛋,那个苹果,对我来说,就是人间美味。我一边狼吞虎咽,一边在心里骂自己没出息,怎么能被敌人的一点小恩小惠收买。可身体的饥饿感,却诚实地压过了心里的那点骨气。
有一次我得了重感冒,上课都昏昏沉沉的。放学后,她又把我叫到办公室,我以为又要重写作文,心里烦躁得不行。结果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拿出一个小小的酒精炉,用搪瓷缸子给我煮了一碗加了红糖和姜片的滚烫姜汤。她把缸子递到我手里,嘱咐道:“喝了,暖暖身子,今天不写了,早点回家。”
我捧着那个滚烫的缸子,看着里面翻滚的姜片,第一次没敢抬头看她的眼睛。那碗姜汤,辣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我不知道那是被姜辣的,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从那天起,我心里的怨恨,开始松动了。我发现,她虽然嘴上严厉,总逼我写那些我不愿意写的东西,但她看我的眼神,不像别的老师那样带着同情或者鄙夷,那是一种……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像是在看一块需要费尽心力才能雕琢成器的璞玉,既有严厉,又有藏不住的……疼惜?
我把作文本交给她的时候,心里做好了被痛批一顿的准备。可她看完后,久久没有说话。我偷偷抬眼看她,发现她捏着作文本的手指关节都发白了,眼圈红得吓人。她抬起头,声音沙哑地问我:“你……恨他吗?”我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她没再追问,只是把本子还给我,说:“重写。写他是个英雄,写他很爱你。”
那是我第一次公然反抗她。我梗着脖子说:“我不认识他!我写不出来!”她没有发火,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我完全看不懂的痛苦和挣扎。她疲惫地挥了挥手,让我走了。那是唯一一次,她没有逼我重写作文。
03
没想到,她听完后,斩钉截铁地否定了。“不行,不能写你妈妈。”她看着我,眼神前所未有的严肃,“陈宇,这次竞赛对你很重要,一等奖有五百块奖金,还能作为重点高中的特长生被优先考虑。你必须写一个……格局更大的东西。”
我气得浑身发抖,我觉得她简直不可理喻!我妈就是我身边唯一的光,这有什么格局不大?我跟她大吵了一架,把积压了两年多的怨气全都吼了出来。“你根本不懂!你凭什么否定我妈!”
她没有跟我吵,只是安静地听着。等我吼完了,她才轻声说:“我知道你妈妈很伟大。评审老师想看到的,不是个人的小情小爱,而是能照亮更多人的大爱。你听我的,这一次,就听我一次。”
交稿那天,我几乎是把作文本摔在她桌上的。我觉得那是我写过最虚伪、最恶心的一篇文章。可一个月后,消息传来,我的那篇《擎灯人》获得了一等奖。校长在全校大会上表扬我,五百块奖金用一个大红包装着,沉甸甸地塞到我手里。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也随之而来。
我的人生,仿佛真的被那篇我最鄙夷的文章,照进了一道刺眼的光。我去给她报喜,她还是穿着那身白裙子,站在窗边,夕阳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边。她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说:“路,是你自己走出来的。以后,要一直往亮处走。”
我那时候年轻,不懂她话里的深意。我只觉得,我终于摆脱她了。高中,大学,我拼了命地学习,离开了那个小县城,后来在大城市扎了根,成了一名记者。我写过很多报道,揭露过黑暗,也赞美过光明。我以为,我已经彻底走出了过去的阴影,成了一个能直面惨淡人生的人。而苏婉-清老师,也慢慢成了我记忆里一个模糊而矛盾的符号。直到我接到她因病去世的消息。
日记本在我手中,薄薄的几页纸,却重若千斤。我颤抖着手,继续往下读。
“今天看到陈宇交上来的作文本,心口像被堵住了一样。他写他父亲消失在一场大雪里。他不知道,当年那场雪,也埋葬了我的一生。正平,你看见了吗?这是他的儿子,他长得真像你啊,尤其是那股子倔劲儿。”
“正平”这个名字,像一道闪电劈进我的脑海。那是我父亲的名字,陈正平!我妈很少提,但我记得。我继续往下看,一段被泪水浸泡过,字迹已经晕开的文字,揭开了一个被时光掩埋了十年的残酷真相。
根据后来交警的勘察报告,吕浩当时完全可以向右猛打方向盘,那样他能活下来,但我爸会被撞得粉身碎骨。可在那千钧一发的瞬间,他选择了向左,猛地撞向了路边的护栏。他的货车翻下了路基,他当场死亡。我爸的拖拉机只是侧翻,但也因为撞击过猛,没能抢救回来。
事后,所有人都说我爸是事故的主要责任人,说那个叫吕浩的司机倒了八辈子血霉。吕浩的家人也来闹过,是我妈跪在地上磕头,赔光了家里所有的钱,才算了事。而苏婉清,作为吕浩的未婚妻,承受了所有的痛苦。
她在日记里写道:“所有人都说你爸是害死我爱人的人。可我整理浩子的遗物时,发现了他出车前给我写的信。他说,他最近总跑夜路,看到很多和陈正平一样的司机,为了多挣点钱,拿命在熬。他说,如果有一天真的出了事,别去怨恨对方,大家都是苦命人。浩子,你那么善良,我怎么能让你的善良,在你死后蒙尘?”
我的眼泪,终于决堤了。原来,她不是不知道我的苦,她比任何人都懂。她懂那种被贫穷和命运扼住喉咙的窒息感,因为她的爱人,和我的父亲一样,都是被生活活活累死的人。
她调来我们学校,看到我的名字,看到我作文里和我父亲如出一辙的灰暗与绝望,她害怕了。她怕我重蹈覆辙,怕我也被那种无望的生活拖垮。所以她才用那种近乎偏执的方式,逼着我去看、去写光明。
那些放学后的留堂,不是惩罚,是守护。那些鸡蛋和苹果,是她笨拙的温柔。那碗滚烫的姜汤,是她藏在冰冷外表下的心疼。她不让我写我妈妈,不是觉得我妈妈不伟大,她是怕那篇带着原生家庭苦难印记的作文,会让我被贴上“可怜”的标签,阻碍我走出去。她逼我写那个光芒万丈的英雄,其实是想告诉我,即使出身泥潭,也可以心向光明,你也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成为家里的擎灯人。
我合上日记本,紧紧地抱在胸口,仿佛能感受到她残留的温度。窗外,阳光正好,照亮了房间里的每一粒尘埃。我走到窗边,看着楼下孩子们嬉笑打闹。我终于明白,苏老师那条洗得发白的白裙子,不是什么文艺的点缀。那是她为自己穿的一身素缟,祭奠她逝去的爱人;那也是她为我点亮的一盏心灯,干净、纯粹,照亮了我后来所有的人生。
老师,谢谢你。你的作文,我读懂了。这一次,不用重写。
文档上传者
热门标签
相关文档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