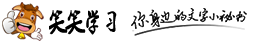欢迎来到98聘
如何写《我的名字作文400字》教你5招搞定!(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11-25 00:16

写作核心提示:
这是一篇关于你名字的400字作文,以及写作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作文: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是 [你的名字]。它不是什么特别华丽或罕见的名字,但对我来说,它承载着家人沉甸甸的期望和独特的意义。我的父母给我取这个名字,一定经过了很多考虑,它不仅仅是一个代号,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
从字面上看,[你的名字] 由 [简单解释名字的构成,例如:两个汉字组成,第一个字“X”意为XX,第二个字“Y”意为YY]。“X”字代表着 [解释第一个字的意义,例如:坚韧、光明、智慧等],而“Y”字则象征着 [解释第二个字的意义,例如:温柔、广阔、顺利等]。合在一起,父母希望我能够 [将两个字的意义结合起来,阐述期望,例如:成为一个内心坚韧、性格温柔的人,或者拥有光明的未来,并且一生顺利]。这简单的几个字,蕴含着他们对我的美好祝愿。
随着我慢慢长大,我开始更加深刻地体会这个名字带给我的力量。当我遇到困难想要退缩时,“X”字所代表的 [再次提及第一个字的意义,例如:坚韧] 就仿佛在耳边提醒我,要像名字一样,勇敢面对。当我与人相处时,“Y”字所蕴含的 [再次提及第二个字的意义,例如:温柔] 也让我学会了理解和包容。
名字,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也是与生俱
陆登,潞州这是我死前第七天的日记而我只想把同袍的名字刻进石头
第六日·夜半,残灯如豆
风从箭孔灌入,吹得案上军报哗哗作响。
我数了数 remaining 的守军
四百三十一人。
能站的,三百;能战的,不足两百。
厨房来报:最后一锅马皮汤熬好了,分给伤兵。
有个小卒问我:“将军,朝廷还会派援吗?
我没答。
窗外月色惨白,照着城下层层叠叠的敌营火光,像地狱开了门。
我把名字写在木牌上,藏进墙缝。
不是怕死,是怕
我死了,没人记得他们也死过。
第五日·晨,雪
昨夜下雪了。
好极了。
雪能掩盖尸臭,也能让敌军弓弦失灵。
我带着最后两队人巡城。
走到东角楼,老伍长李敢突然跪下:
将军,我家三辈从军我儿昨日阵亡,尸首还在护城河边。
他没哭,只说:“请准我今晚去背他回来。
我点头。
夜里,我亲自带人出城。
我们在尸体堆里翻找,冻僵的手一个一个摸脸。
找到时,那孩子脸上覆着雪,嘴角竟似笑着。
我们把他背回来,和父亲葬在同一坑里。
土埋到一半,李敢忽然吼了一声:“陆登!你不许死!你要活着告诉天下我们打到了最后一刻!
我哭了。
这是我守城九十二天,第一次哭。
第四日·午,火起
西门塌了半丈。
金兵蚁附而上。
我率亲兵持长矛堵缺口,一杆枪断了,换刀,刀折了,捡死人手里的继续砍。
有个年轻士兵被箭射穿肩胛,还死死抱住旗杆不放。
他说:妈我想回家但不能倒
旗没倒。
他也没再说话。
我下令烧民房,拆梁为檑木。
百姓无怨。
有位老妇把自己门板扛来,说:“烧吧,只要陆将军还在城头。
那一刻我知道
这城能守这么久,不是因为我多能打,
而是民心未冷。
第三日·子时,绝粮
最后一袋糙米分完。
每人三勺煮糠水。
医官来报:重伤者十七人,无药可救。
他们集体求死:“将军,给我们一碗毒酒,别拖累兄弟。
我不肯。
他们自己爬到城墙边,说:“等金兵上来时,我们跳下去,砸个窟窿。
半夜,我听见他们在哼军歌。
调子走得很远,但一句没漏:
“男儿赴国难,何须裹尸还
我坐在大堂,翻开名册,把他们的名字一个个抄下。
纸不够了,就写在墙上。
墨没了,就用血。
第二日·黄昏,降书至
完颜斜烈遣使送信:
“若开城,保你富贵;若死守,破城之日,鸡犬不留。”
我回了一封:
“陆登在此,尔等可来取头。
附赠使者一把断刀是我第一个砍死金将时所用。
使者惊退。
我对左右说:“他们不懂。
我不是要守住这座城。
我是要让他们记住——
有些汉人,骨头是弯不了的。
第一日·黎明,焚书
我烧了所有军务卷宗,只留一本:
《殉难将士录》,记四百三十一人姓名、籍贯、父母妻儿。
命亲兵王五缒城而出,直奔汴京。
他跪地痛哭:“将军不走,我也不走!”
我一脚踢他下城:“滚!把名字送出去!不然老子做鬼也不饶你!”
火光中,我看见他消失在雪地里。
当日·午,城陷
门破时,我已穿戴整齐:
红袍、玉带、金印、佩剑。
坐于公堂正位,目视大门。
金兵涌入,见我端坐不动,竟无人敢上前。
良久,一员大将进来,摘盔,单膝跪地:
“将军忠烈,天下共仰。请受我一拜。”
我说:“要杀便杀。”
他摇头:“我们敬英雄。请你自裁,全尸而葬。”
我拔剑,划过咽喉
未死,再割。
血流满案,意识渐昏。
最后看到的,是墙上那一片血写的名单。
风吹烛灭前,我笑了。
他不是大将,
只是个守土的小官。
他没有改变历史,
却定义了什么叫‘中国人’。
陆登死了。
可每当山河破碎时,
总有人想起那个雪夜里,
坐着等死的红袍身影
然后,挺身而出。
#陆登 #忠烈 #冷门英雄 #守城战 #气节 #历史真相 #中华脊梁
我把自己写进了历史,成了教科书上的一个名字
我外甥把新学期的历史教科书扔到我面前时,我正在给我那盆半死不活的君子兰浇水。
“舅,你出名了。”
他语气平淡,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我眼皮都没抬。
“出什么名?小区棋牌室冠军又登报了?”
“不是,”他翻开书,指着其中一页,“这次是正经出名。”
我的目光顺着他那根啃得坑坑洼洼的指甲看过去。
《晚明危局与士人风骨》章节。
一段印刷体的宋体小字,安静地躺在页面底部。
“关于顾衡降清一事的传统观点,长期以来将其定性为变节行为。然而,青年学者陈驰经过多年考证,于2012年发表《顾衡别传考》,颠覆了这一论断。他提出的证据链表明,顾衡实为诈降,意图策反……”
陈驰。
我的名字。
我感觉手里的水壶有点重。
君子兰的叶子被水珠压弯了腰。
“酷不酷?”外甥一脸“快夸我”的表情,“我们历史老师还专门讲了你的事,说你特牛,一个人挑战了整个学术界。”
我没说话。
我只是盯着那个名字。
陈驰。
两个冰冷的汉字,像两枚钉子,把我牢牢钉在了历史的书页上。
我成了教科书上的一个名字。
一个脚注。
一个考点。
我突然觉得有点想吐。
这事儿得从十二年前说起。
那年我二十六,历史系研究生,混吃等死。
毕业论文的题目还没定,导师刘教授天天在办公室里对我吹胡子瞪眼。
“陈驰!你到底想干什么?啊?研究宋代蹴鞠的商业化运作?你以为你是写网络小说吗!”
刘教授是国内晚明史的泰斗,我报他门下,纯属当年分数凑巧。
我对晚明那段历史,说实话,没什么感觉。
太压抑了。
一群人,明知道船要沉,还在甲板上吵架,或者闷头喝酒,或者干脆直接跳海。
我喜欢更轻松点的,比如唐诗宋词,风花雪夜。
但没办法,学位得要。
那天我又被刘教授骂了个狗血淋头,垂头丧气地滚进图书馆的故纸堆里。
我决定破罐子破摔。
不就是晚明史吗?我找个最没争议的、最铁板钉钉的题目,随便扒拉点资料,凑够字数,赶紧滚蛋。
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顾衡。
顾衡。
晚明史上最著名的汉奸之一,板上钉钉的那种。
崇祯十七年,京城陷落,他开彰义门迎李自成。没过多久,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他又第一个剃发易服,跪迎多尔衮。
《明史》给他定了性:“首鼠两端,毫无气节,士林之耻。”
完美。
就他了。
写这么个人,绝对不会出错,资料又多,还好写。
我从书架最底层抽出落满灰尘的《明季北略》,准备开工。
然后,我看到了那句话。
就在写顾衡开门降顺的那一页,页边的空白处,有一行极小的、用毛笔写的蝇头小楷。
字迹已经很淡了,几乎辨认不出。
我凑得很近,鼻子都快贴到纸上,闻到一股陈腐的霉味。
“衡之罪,非降,乃信也。”
意思是,顾衡的罪过,不是投降,而是轻信。
我愣住了。
这本《明季北略》是图书馆的馆藏善本,民国时期的版本,谁会在上面乱写?
而且这口气,不像随手涂鸦。
更像是一声叹息。
一声来自遥远时空的,不甘的叹息。
我当时脑子一抽,鬼使神差地,把这句话记在了我的笔记本上。
我没意识到,这个小小的举动,像一颗石子,投入了我那潭死水般的人生。
涟漪,就这么开始了。
我开始对顾衡这个人产生了那么一丝丝,就一丝丝的好奇。
我把所有能找到的关于顾衡的史料都搬到了我的小桌子上。
《明史》、《清史稿》、《甲申纪事》、《石匮书后集》……
堆得像一座小山。
我看了一个星期。
看到的,全是骂他的。
骂他无耻,骂他谄媚,骂他反复无常。
所有的记载,都指向同一个结论:这个人,坏透了。
我有点失望。
看来那行小字,八成就是某个愤青的胡言乱语。
我准备放弃了,把材料还回书库,老老实实写我的“论顾衡的变节与晚明士人精神的崩塌”。
多安全,多稳妥。
就在我收拾东西的时候,一张纸从一本叫《燕都旧闻录》的野史笔记里掉了出来。
那是一张借书卡,非常老旧,纸都泛黄了。
上面有好几个人的名字。
最后一个名字,是刘教授的。
时间是,三十年前。
这没什么稀奇的,刘教授是搞晚明史的,看过这本书很正常。
奇怪的是,我在刘教授的名字旁边,看到了一个极淡的铅筆印。
那是一个问号。
就画在记载顾衡轶事的那一页旁边。
我心里咯噔一下。
刘教授,三十年前,也对顾衡产生过怀疑?
我拿着那张借书卡,敲开了刘教授办公室的门。
他正在喝茶,看我进来,眉头又拧成了疙瘩。
“论文题目想好了?”
“还没。”我把借书卡递过去,“刘老师,我就是想问问您,您三十年前看这本书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顾衡这个人,有点奇怪?”
刘教授接过借书卡,看了一眼,眼神微微一动。
但他很快恢复了平静。
“小孩子家家,别胡思乱想。”他把卡片扔回给我,“顾衡的案子是铁案,翻不了。你与其把时间浪费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不如多看看正史。”
“可是……”
“没有可是!”他声音严厉起来,“陈驰,我带你,是希望你能走正道,做扎实的学问!不是让你去搞什么翻案文章,哗众取寵!”
我被他训得哑口无er。
我看得出,他不是在敷衍我。
他是在警告我。
我走出办公室,心里那点好奇的小火苗,非但没被浇灭,反而烧得更旺了。
刘教授,他到底在隐瞒什么?
我决定,这条路,我走定了。
我没告诉刘教授,我把毕业论文的题目, secretly 定为了《顾衡降清动机考辨》。
我知道这是在玩火。
一旦被他发现,我毕不了业都是小事,很可能在这个圈子里都混不下去。
但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那句“衡之罪,非降,乃信也”,像魔咒一样在我脑子里盘旋。
我白天假装研究别的课题,晚上就偷偷摸摸地查顾衡的资料。
我成了一个幽灵。
一个游荡在图书馆、档案馆、旧书市场的幽灵。
我开始从正史之外的地方下手。
地方志、族谱、私人笔记、诗文集……
任何可能留下蛛丝马迹的角落,我都不放过。
这个过程,枯燥得像在沙漠里找一根针。
我女朋友小琳,开始跟我吵架。
“陈驰,你到底在干嘛?”她把一碗泡面重重地摔在我桌上,“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我抬起头,眼睛里全是红血丝。
“我在忙。”
“忙?忙什么?你那篇破论文,有那么重要吗?比我还重要吗?”
我没法跟她解释。
我怎么解释?
说我为了一个四百年前的汉奸,快要走火入魔了?
她会觉得我疯了。
“小琳,你再等等我,就快了,就快有结果了。”
她冷笑一声。
“结果?什么结果?陈驰,我跟你说,我们下个月就要交房租了,你那点奖学金够吗?你毕业了打算干什么?就守着这些破纸过一辈子?”
我沉默了。
这些问题,我一个都不了。
那段时间,我的世界里只有两件事:找钱,和找顾衡。
我去做家教,去发传单,去给婚庆公司扛摄像机。
赚来的钱,一部分交房租,剩下的,全都买了旧书,或者当成路费。
我根据顾衡的籍贯,去了河北的一个小县城。
县志里关于他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跟正史一模一样。
顾家,也早就败落了。
我找到顾家的祖坟,荒草萋萋,只剩下一块断裂的石碑。
我在那儿坐了一下午,直到太阳落山。
一无所获。
回北京的火车上,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第一次感到绝望。
也许,我真的错了。
也许,刘教授说得对,我就是在胡思乱想,哗众取宠。
也许,顾衡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烂人。
我的坚持,我的牺牲,我的 पागल,就是个笑话。
回到学校,小琳给我留了一张纸条。
“我走了,我们分手吧。我不想我的男朋友,活得像个古代的怨魂。”
我捏着纸条,瘫坐在椅子上。
房间里空荡荡的。
桌上那堆关于顾衡的资料,像是在无声地嘲笑我。
我把它们一股脑地扫到地上。
我哭了。
为了一个不相干的死人,我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孤家寡人。
我他妈就是个。
我决定放弃了。
第二天,我找到刘教授,跟他说我想换个论文题目。
他看了我一眼,眼神很复杂。
“想通了?”
我点点头。
“想通了就好。”他叹了口气,“年轻人,有锐气是好事,但不能钻牛角尖。历史是既成事实,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我低着头,一言不发。
“回去吧,”他摆摆手,“把心思放在正道上。”
我转身离开。
就在我快要走出门口的时候,他突然又叫住了我。
“陈驰。”
我回头。
他犹豫了一下,说:“去潘家园转转吧,就当散散心。”
我愣住了。
潘家园?旧货市场?
他让我去那儿干什么?
我没多想,以为他只是随口一句安慰。
但那个周末,我还是鬼使神神差地去了。
潘家园还是老样子,人挤人,真假难辨的古董玩意儿堆得到处都是。
我漫无目的地瞎逛,像个孤魂野鬼。
然后,我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摊上,看到了一个东西。
一个墨盒。
一个非常普通的青石墨盒,上面刻着几竿竹子。
吸引我的,不是墨盒本身。
是墨盒底下的一个刻印。
一个“顾”字。
是顾衡的私印。
我在无数史料的影印件上见过这个印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我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
我蹲下来,拿起那个墨盒。
很重,入手冰凉。
摊主是个精瘦的老头,瞥了我一眼。
“小伙子,有眼光啊。这可是前朝的东西。”
我当然知道他是胡扯。
这种东西,十有八九是仿的。
但我还是问了一句:“多少钱?”
“看你是个学生,三百。”
我还价:“五十。”
老头眼睛一瞪:“五十?你打发叫花子呢?这可是……”
我没等他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块钱拍在他面前。
“就一百,爱卖不卖。”
我当时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坚决。
或许是那段失败的追寻,让我心里憋着一股邪火。
老头 probabilmente 看我态度坚决,嘟囔了几句,把钱收了。
我拿着那个墨盒,像捧着个烫手山芋。
我甚至觉得有点可笑。
我到底在干什么?花一百块买个假古董,就为了上面一个“顾”字?
我疯了吗?
我回到宿舍,把墨盒往桌上一扔,没再管它。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老老实实地写我的新论文。
题目是《论明末党争对时局的影响》。
安全,无聊,但能毕业。
我强迫自己不再去想顾衡的事。
我把所有关于他的资料都锁进了箱底。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直到那天晚上。
北京下了场大雨,宿舍楼的电路短路了,停电了。
我摸黑点了根蜡烛。
烛光摇曳,把我的影子投在墙上,张牙舞爪。
我闲着没事,又把那个墨盒拿了出来。
在烛光下,我发现墨盒的内壁,似乎有些不太平整。
我用手指摸了摸。
感觉像是有刻痕。
我心里一动,找来一把小刀,小心翼翼地刮掉内壁上厚厚的墨垢。
刮着刮着,我发现不对劲。
内壁的材质,和外壳不一样。
外壳是青石,而内壁,似乎是一层涂了黑漆的木头。
是一个夹层!
我的手开始发抖。
我用刀尖撬开那层木板。
“咔哒”一声轻响。
木板下面,是空的。
里面塞着一卷东西。
一卷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
我的呼吸都停滞了。
我颤抖着手,把那卷油纸拿出来,一点一点地展开。
里面,是几张泛黄的信纸。
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
是毛笔字。
字迹风骨峭峻,是我在顾衡的奏疏上见过的笔迹。
是顾衡的亲笔信!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只剩下心脏狂跳的声音。
信,是写给一个叫“袁石”的人。
我搜索我所有的记忆,历史上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名人。
信的内容,是用一种暗语写的。
乍一看,像是普通的家书,谈论天气,谈论茶米油盐。
但我研究了那么久的顾衡,我知道他的一些习惯。
我发现,信里提到的某些特定词语,比如“新茶”、“北风”、“旧袍”,出现的频率很不正常。
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种密码。
我把信纸铺在桌上,像疯了一样,开始尝试破解。
我把我所有关于密码学的知识都用上了。
字频分析,替代密码,藏头诗……
整整一夜。
天快亮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规律。
那是一种基于《易经》卦象的加密方式。
每一个看似平常的词,都对应着一个卦象,再由卦象指向一个特定的字。
极其复杂,也极其巧妙。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破译。
当第一个句子被我完整地翻译出来时,我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虏势猖獗,京城旦夕不保,上意不定,唯有行险一搏。”
我继续往下破译。
内容越来越惊心动魄。
这根本不是什么家书!
这是一份完整的计划书!
顾衡,在崇祯皇帝的默许下,制定了一个极其大胆的计划:诈降!
他主动向李自成和后来的清军投降,是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充当最高级别的间谍!
他计划利用自己对北京城防的了解,和在旧臣中的影响力,里应外G合,等待时机,一举光复。
信里详细列出了可以联络的忠臣名单,传递情报的秘密渠道,甚至还有一份他绘制的清军大营布防图!
而那个收信人“袁石”,根本不是人名!
“袁”指的是袁崇焕。
“石”指的是“砥柱”。
“袁石”,是他们这个秘密计划的代号,意思是,要成为像袁崇焕那样的国之栋梁!
我看到了最后一封信。
日期是顾衡被清廷处死的前一天。
信里只有一句话。
“事泄,速走,勿念。所憾者,非吾身之死,乃信错奸佞,国祚难复也。”
他失败了。
他不是败给了敌人。
他是败给了自己人。
有人告密。
那个被告密出卖的瞬间,他所有的忍辱负重,所有的家国理想,都成了泡影。
他从一个卧薪尝胆的英雄,变成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汉奸。
而他,至死都不能辩解一句。
因为一旦辩解,就会暴露整个计划,暴露那些还在潜伏的同志。
他只能选择沉默。
选择背负着千古骂名,走向刑场。
我放下信纸,双手抖得不成样子。
窗外,天已经亮了。
一场暴雨过后,空气清新得刺鼻。
我看着桌上那些被破译出来的文字,感觉自己像做了一场大梦。
一个跨越了四百年的大梦。
我终于明白了那句“衡之罪,非降,乃信也”的含义。
他不是轻信敌人。
他是轻信了朝中的同僚。
我找到了真相。
一个被尘封了四百年的,残酷的真相。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冲到刘教授家。
我把那些信纸和我的破译稿,拍在他面前。
“刘老师,您看!”
他当时正在练字,被我吓了一跳。
他扶了扶老花镜,拿起那些信紙,一张一张地看。
他的手,也开始抖了。
他看得非常慢,非常仔细。
整个书房里,只剩下纸张翻动的声音。
看完最后一张,他沉默了,久久地沉默。
他就那么坐着,像一尊雕塑。
良久,他抬起头,看着我。
眼神里,有震惊,有痛苦,有懊悔,还有一丝……解脱。
“你……是怎么找到的?”他声音沙哑。
我把潘家园买墨盒的经历说了一遍。
他听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天意啊……真是天意。”
他站起来,走到书架前,从最高一层,搬下来一个上了锁的木箱。
他打开箱子。
里面,全都是关于顾衡的研究笔记。
比我的还要多,还要厚。
“我三十年前,就开始怀疑了。”他缓缓地说,“我发现了一些矛盾,一些官方史书上无法解释的矛盾。比如,顾衡降清后,他的家人并没有得到善待,反而被严密监控。再比如,几个被认为是顾衡同党的官员,后来都成了抗清的中坚力量。”
“我花了十年时间去查,跟你一样,一无所获。”
“我甚至……我甚至找到了顾衡在河北的那个远房后人,就是那个卖给你墨盒的家族。但我去的时候,那个知道秘密的老人刚刚去世。他们只告诉我,祖上留下一个墨盒,但早就遗失了。”
他苦笑了一下。
“我以为,这条线索就这么断了。我以为,这个秘密,就要永远被埋葬了。”
他看着我,眼神灼灼。
“陈驰,你比我勇敢。”
“我当年,查到一半,就退缩了。这个题目太大了,太危险了。要推翻《明史》的定论,要挑战整个史学界的权威,我没有这个胆量。”
“所以,我选择了放弃。我甚至……阻止你继续查下去。”
他脸上露出愧疚的神色。
“我怕你跟我一样,走火入魔,最后一事无成。我是在保护你,但其实,我是在保护我自己的懦弱。”
我鼻子一酸。
原来,他什么都知道。
他不是在打压我,他是在用他的方式,保护一个和他当年一样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
“老师……”
“别叫我老师。”他摆摆手,“在这个问题上,你才是我的老师。”
他拿起我的破译稿。
“现在,我们有了证据。铁证如山!”
“陈驰,你想怎么做?”
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我要为顾衡翻案。我要把真相,公之于众。”
刘教授的眼睛亮了。
那是一种我从未在他眼中见过的光芒。
像是熄灭已久的火焰,重新燃烧了起来。
“好!”他说,“我陪你一起!”
那一天,我们师徒俩,在书房里待了一整天。
我们整理证据,梳理逻辑,构建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从顾衡的信件,到各种史料中的矛盾点,再到清廷档案里的蛛丝马迹。
我们要做到的,是无懈可擊。
那段时间,刘教授仿佛年轻了二十岁。
他动用了他所有的人脉和资源,帮我查漏补缺。
我们经常为一个细节,争论到面红耳赤。
又会在找到一个新证据时,像孩子一样击掌相庆。
我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身后,站着我的老师。
半年后,我的论文,《顾衡别传考》,完成了。
定稿的那天晚上,我和刘教授,喝了一瓶二锅头。
他喝得满脸通红。
“陈驰啊,”他拍着我的肩膀,“你知道吗,做学问,最难的不是皓首穷经,不是忍受清贫。”
“最难的,是守住那一点点求真的勇气。”
“我这辈子,写了几十本书,评上了教授,当上了博导。但说实话,我没有一篇东西,比得上你这篇论文。”
“因为你这篇东西里,有骨头。”
我眼眶湿了。
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
论文发表的过程,比我想象的还要艰难。
我们投给了国内最权威的历史学期刊。
一个月后,稿子被退了回来。
没有评审意见,只有三个字:“不宜发表。”
我们都明白这三个字的分量。
这意味着,官方学术界,拒绝承认我们的发现。
刘教授气得把退稿信撕得粉碎。
“他们这是学阀作风!这是在扼杀真相!”
我却 strangely 平静。
“老师,我早就想到了。”
“那怎么办?就这么算了?”
“当然不。”我摇摇头,“他们不发,我们自己发。”
我把论文发到了网上。
在一个小众的历史论坛上。
我没指望能引起多大的波澜,我只是想,至少让一些人看到。
帖子发出去,石沉大海。
一天,两天,一个星期。
除了几个零星的回复,说“楼主脑洞真大”,再无声息。
我有点灰心。
刘教授也沉默了。
我们就像两个对着风车冲锋的唐吉訶德,显得那么滑稽可笑。
转机,发生在一个月后。
一个著名的历史博主,偶然看到了我的帖子。
他是个考据狂,一开始也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但他顺着我的证据链,一条一条地去核对。
核对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他发现,我说的,全是真的。
他写了一篇长文,详细介绍了我的论文和考证过程。
这篇文章,火了。
一夜之间,全网转发。
“四百年最大冤案”、“史上最强卧底”、“被教科书黑惨的民族英雄”……
各种耸人听闻的标题,铺天盖지。
顾衡,这个尘封的名字, suddenly成了舆论的焦点。
我的名字,陈驰,也第一次,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事情,彻底闹大了。
随之而来的,是学术界的反扑。
无数专家学者站出来,指责我“哗众取宠”、“伪造史料”、“亵渎历史”。
他们说我的论文是“网络文学的狂欢”,是“对严肃史学的侮辱”。
一时间,我成了学术界的公敌。
我的电话被打爆了。
有记者要采访我的,有电视台要我去做节目的,更多的是骂我的。
我不敢出门,不敢上网。
我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感觉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恶意。
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
我是不是真的错了?
我是不是真的伪造了什么?
我把那些信件,那些破译稿,翻来覆覆地看。
没有错。
每一个字,每一个证据,都对得上。
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刘教授来看我。
他给我带来一句话。
“陈驰,记住,当你的观点威胁到很多人的饭碗时,对错,就已经不重要了。”
我一下子明白了。
我推翻的,不仅仅是顾衡的定论。
我推翻的,是建立在这个定论之上的一整套学术体系。
是无数专家学者赖以成名的著作、论文、观点。
我等于是在说:你们这几十年,都研究错了。
我砸了他们的饭碗。
他们当然要跟我拼命。
“老师,那我该怎么办?”我茫然地问。
“开辩论会。”刘教授斩钉截铁地说,“既然他们说我们错了,那就摆到台面上来,公开辩论!让所有人都看看,到底谁对谁错!”
我惊呆了。
“公开辩论?跟他们所有人?”
“对!”刘教授目光如炬,“真相,是越辩越明的。我们手里有铁证,我们怕什么!”
我看着他,心里那股熄灭的火,又一次被点燃了。
对啊。
我怕什么?
我只是说出了真相而已。
辩论会定在一个月后,由一家有影响力的媒体和国内顶尖大学联合举办。
地点,就在我们学校的大礼堂。
我的对手,是国内晚明史领域的五位顶级专家。
每一个,都是著作等身、德高望重的人物。
而我这边,只有我和刘教授。
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
以卵击石。
自取其辱。
那一个月,我和刘教授,几乎没怎么睡觉。
我们把所有的证据,重新梳理了一遍又一遍。
我们设想了对方可能提出的所有问题,准备了上百个预案。
那已经不是在做学问了。
那是在备战。
辩论会那天,大礼堂座无虚席。
媒体的长枪短炮,对准了主席台。
我坐在台上,看着底下黑压压的人群,手心全是汗。
我旁边的刘教授,倒是很镇定。
他 patted my shoulder.
“别怕,说实话就行。”
辩to begin.
对方的主辩,是史学界的另一位泰斗,王教授。
他一上来,就气势汹汹。
“陈驰先生,你的论文我看过了。恕我直言,漏洞百出,充满了主观臆断!”
“你所谓的‘顾衡亲笔信’,来源不明,真伪难辨。一个从地摊上买来的墨盒,怎么能当成史学研究的核心证据?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台下响起一片哄笑。
我深吸一口气,拿起话筒。
“王教授,信件的真伪,我们已经请国内最权威的笔迹鉴定专家和文物鉴定专家做过鉴定。鉴定结果,可以证明这就是顾衡的真迹,纸张和墨迹的年份,也完全符合晚明时期的特征。相关的鉴定报告,我们已经提交给了主办方。”
王教授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们准备得这么充分。
他立刻转移了话题。
“好,就算信是真的。你那个所谓的密码破译,也完全是你的一家之言!《易经》卦象,包罗万象,你怎么就能确定,你的破译就是顾衡的本意?这不过是你的牵强附会!”
这个问题很刁钻。
密码学本身,就很难有百分之百的定论。
我看到刘教授的脸色沉了下来。
我却笑了。
“王教授,您说得对。单纯从密码学角度,确实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的证实。但是,”我话锋一转,“史学研究,讲究的是孤证不立。”
“我的证据,不是只有这一封信。”
我站起来,走到后面的投影幕布前。
“请看大屏幕。”
我把我这几年来找到的所有旁证,一条一条地展示出来。
“这是《清实录》的记载,顾衡降清后,多次向多尔衮提出错误的军情建议,导致清军数次 small-scale 军事行动失败。这,如何解释?”
“这是顾衡的同年好友,南明将领李成栋的私人笔记。里面提到,‘与故人有约,南北夹击,以复京师’。这个‘故人’,是谁?”
“这是顾衡的儿子,顾炎武的诗。‘忍看家父蒙奇耻,只为苍生续一线’。如果顾衡真是汉奸,顾炎武为什么要这么写?”
……
我一口气,列出了二十多条证据。
每一条,都来自正史,来自可靠的文献。
它们像一根根钉子,把我那看似孤立的“信件”证据,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坐标上。
整个礼堂,鸦雀无声。
那五位专家,脸色越来越难看。
他们开始交头接耳,表情慌乱。
我最后,把投影切换回那封信的最后一句话。
“事泄,速走,勿念。所憾者,非吾身之死,乃信错奸佞,国祚难复也。”
我对着话筒,声音不大,但足以让每个人都听到。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历史,是由人写的。只要是人写的,就可能会犯错,可能会被蒙蔽,可能会被篡改。”
“我们的责任,不是盲目地信奉前人的结论。”
“我们的责任,是无限地接近真相。”
“顾衡,他是一个英雄,还是一个汉奸,我们今天在这里争论不休。”
“但四百年前,他走向刑场的时候,他没有争论。他选择了沉默。”
“他用自己的名节,保护了他的同志,保护了他那个遥不可及的复国梦想。”
“今天,我们有幸,看到了他留下的真相。”
“如果我们因为害怕,因为权威,因为所谓的‘学术规范’,而选择对真相视而不见……”
我顿了顿,目光扫过对面那五张涨红的脸。
“那我们,和当年那个出卖他的奸佞,又有什么区别?”
说完,我鞠了一躬。
坐下。
全场,死一般的寂静。
几秒钟后。
掌声,响了起来。
一开始,是稀稀拉拉的几声。
然后,越来越多。
最后,掌声像雷鸣一样,淹没了整个礼堂。
我看到,台下很多学生,都站了起来。
他们的眼睛里,闪着光。
我看到,我身边的刘教授,眼眶红了。
我知道,我们赢了。
那场辩论会,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它在网上被反复播放,讨论。
舆论,彻底倒向了我们这一边。
学术界,也开始出现松动。
一些年轻的学者,开始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发表文章支持我的观点。
半年后,国家历史研究院成立了专项小组,重新调查顾衡一案。
一年后,调查结果公布。
结论是:陈驰的考证,成立。
顾衡,不是汉奸。
他是一个被误解了四百年的爱国者。
消息传来的那天,我正在家里吃泡面。
我看着电视新闻里播报的画面,突然就哭了。
我哭得像个。
我不知道是为了顾衡,还是为了我自己。
为了我那死去的爱情,为了我那荒唐的青春,为了我那无数个在图书馆里啃着干面包的夜晚。
一切,都值了。
后来,我的论文正式出版,书名叫《顾衡别传考》。
扉页上,我只写了一句话。
“献给所有在黑暗中坚守真相的人。”
再后来,我留校任教了。
我成了我们学校最年轻的副教授。
刘教授退休了,他把他的那间书房,留给了我。
我还是喜欢研究那些犄角旮旯里的历史。
那些被正史忽略的小人物,那些被误解的片段。
我总觉得,那里藏着更真实的人性。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
我结了婚,生了孩子。
当年的那个愣头青,也渐渐变成了油腻的中年人。
顾衡的事,慢慢淡出了公众的视野,重新回归了学术的范畴。
直到今天。
我外甥把那本教科书,扔到我面前。
陈驰。
我看着那个名字,恍如隔世。
我把自己,写进了历史。
成了一个教科书上的名字。
听起来,很牛逼,对吧?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为此付出了什么。
我失去了我的初恋。
我透支了我的健康。
我得罪了半个学术圈。
我人生最美好的那几年,都耗在了一堆故纸里。
值得吗?
我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
外甥看我半天不说话,有点不耐烦了。
“舅,你到底酷不酷啊?给个话啊。”
我回过神来,看着他那张青春洋溢的脸。
我想起了十二年前,那个同样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己。
我笑了。
我揉了揉他的脑袋。
“酷。”
我说。
“但别学我。”
我拿起水壶,继续给我那盆半死不活的君子兰浇水。
水珠顺着叶脉滑落,滴进土壤里。
教科书,就静静地躺在桌上。
那一页,那个名字,仿佛在看着我。
我突然想起了顾衡。
想起了他走向刑场时的心情。
他大概不会想到,四百年后,会有一个一样的年轻人,为了他的清白,赌上了自己的一切。
历史是什么?
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书。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历史是既成事实。
他们都对,也都错了。
历史,是一个又一个,像我,像顾衡这样的人,用我们自己的固执,用我们自己的犧牲,用我们自己的不甘心,一点一点,拼接起来的。
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会被遗忘。
我很幸运。
我留下了一个名字。
一个脚注。
一个考点。
这就够了。
真的,够了。
我浇完水,把君子兰搬到窗台边,让它多晒晒太阳。
希望它这次,能活久一点。
文档上传者
热门标签
相关文档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