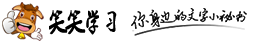欢迎来到98聘
如何写《哭的作文500字》教你5招搞定!(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11-27 08:46

写作核心提示:
这是一篇关于“哭”的500字作文,并附带写作注意事项说明。
"作文:哭,一种必要的释放"
人生如潮,有欢笑,有阳光,也必然有泪水。哭,这个看似脆弱的词汇,常常与悲伤、委屈联系在一起,但它却是一种极其必要且健康的生理与情感释放方式。
我们常常被社会文化教化,要“男儿有泪不轻弹”,要“为坚强而活”。于是,许多人从小就被要求压抑自己的眼泪,仿佛流泪是软弱的表现。然而,真正的坚强,并非没有眼泪,而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有勇气去感受,并允许自己去释放。眼泪,是内心积压情绪的出口。当喜悦、激动、感动等强烈的情感涌动时,泪水也是自然的馈赠,它伴随着呼吸,将内心的澎湃无声地表达出来,是一种纯粹的、不受修饰的情感宣泄。
然而,我们更常哭,是因为悲伤、痛苦和委屈。生活中的挫折、人际关系的裂痕、梦想的破灭……种种不如意都可能让我们潜然泪下。这时,哭泣并非示弱,而是身体在提醒我们,某些重要的情感需求未被满足,某些伤痛需要被看见和疗愈。哭泣时,泪水带走眼角的疲惫和沙砾,也仿佛冲刷着内心的阴霾。它是一种自我安抚,一种情感的疏导。让泪水自由流淌,就像给心灵做了一次深度的按摩,
有钱也是错!安徽34岁男子去世,妻子!人不在了,我也没有顾忌了
“换作你,新婚半年,老公脑壳被医生掀开,你签不签那50万的‘唤醒’单子?
”——我刷到于曼曼的帖子时,手指悬在屏幕上方,愣了五秒,脑子里全是自己老公平时打呼噜的侧脸。
她真签了,刷爆三张信用卡,再借网贷,凑齐23万6,平台筹款23万6,一分不少全砸进ICU。
可夫家转身就把7套门面房锁了,市值2000万,连钥匙都不给她摸。
最狠的是,公婆起诉书直接写“婚姻存续183天,不配分遗产”。183天,连冰箱里的喜字都没褪红,法律却告诉她:你只是个过路租客。
我扒完判决书,发现更冷的细节。
苏森2023年体检报告肌酐380,超标三倍多,慢性肾衰竭晚期,却赶在2024年11月把婚结了。
于曼曼说“他只说以前有点高,没讲会死人”,这话我信——谁相亲时会亮出体检报告当名片?
但律师甩给我一条:《民法典》1053条,重大疾病婚前不如实告知,婚姻可撤销。
换句话说,她要是早拿到那张报告,现在不是寡妇,而是“前妻”,遗产纠纷根本轮不到她上场。
命运这玩意儿,就是先把人推到悬崖,再递给她一把钝刀。
ICU门口的故事更离谱。
医生亲口承认“200ml出血,救活率不到15%”,公婆却坚持“拔管回家”,于曼曼不肯,夫家当场甩话“你要当寡妇随你,别拉我们垫背”。
她一个人蹲在楼梯间把50万手术同意书啃完,签完字才发现,配偶栏里她的名字后面,公婆早就写上“反对”。
医院不管谁反对,只要配偶签字就动刀,可刀开完了,人成了植物人,夫家把病房门一锁,连护工都不让她请。
那天她发视频,镜头对着自己哭花的脸:“我花了钱,买了他死缓,却买不到一张探视证。
”
最扎心的是账单。87万花出去,医保报完自费49万,她手里只剩平台筹来的23万6,缺口25万4。公婆一分钱不出,却在她发起“剩余善款退还”说明时留言“心虚了吧”。
我算了下,49万换183天婚姻,平均每天2677块,比五星酒店贵,比墓地便宜,最后连骨灰盒都没让她抱。
苏森走的第二天,她回婚房,发现门锁被换,喜字被撕,门口多了一张A4纸:房屋已公证,请勿入内。
那一刻她才明白,自己不是丧夫,是被“净身出户”的另一种写法。
现在案子进到蜀山法院,案由听着拗口——“配偶医疗决策权侵害”,说人话就是:我掏钱救人,你们凭什么拦着不让治?
省里专家私下说,这案子要是赢了,以后ICU门口再出现“拔管还是继续”的拉锯,配偶不再只是“签字机器”。
我看完起诉状,只有一页,却像把刀:请求确认原告享有独立医疗决策权;请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失1元。1块钱,买一句“我没错”。
她说不是为钱,只想让那183天被承认“我是他老婆,不是路人”。
我把故事讲给闺蜜听,她第一反应是“要是我就放弃治疗,反正人财两空”。
我摇头。
没蹲过ICU的人,永远不懂“希望”两个字有多重。
于曼曼后来告诉我,手术那天她其实偷偷带了两颗糖,一颗给苏森,一颗给自己,“万一他醒了,嘴里是甜的”。
糖化了,人没醒,糖纸还留在她钱包夹层,皱巴巴像张未兑现的彩票。
她说以后再也不吃糖了,可也不会后悔签字,“我救的不是他,是以后想起这段,能对自己说‘我尽力了’”。
判决书还没下,门面房已经挂出去两套。
公婆找的中介,报价每平6万8,比市价低一成,要求全款,买家得先付500万定金。
于曼曼算过,只要卖掉一半,就够偿还未清的25万4,还能剩上千万。
她请了律师,申请财产保全,法院冻结了其中三套。
中介在朋友圈发“急售,房东出国”,她截图保存,备注“出国?
出殡!
”三个字,发完自己先笑,笑着笑着又哭。
我隔着屏幕陪她骂,骂完发现,我们骂的不是公婆,是那条看不见的缝——重大疾病不强制婚前告知,婚姻登记处只查户口不查肾功能,ICU门口只看签字顺序不看谁掏的钱。
缝一开,所有人往下掉。
省卫健委的调研问卷我填了,最后一栏“建议”只写一句:把肾功能、心功能、肿瘤标志物写进结婚证附件,敢隐瞒,直接判婚姻无效。
写完心里也没底,真到那天,谁又会把体检报告递给相亲对象?
爱情来时,谁不是先掏心,再掏口袋。
于曼曼说,如果早看见那张肌酐380的报告,她还是会嫁,“但我会先给自己买份寿险,受益人写我妈”。
一句话,把爱情拉回地面:先保命,再谈爱,顺序对了,心碎时至少钱包不碎。
案子开庭那天是1月6号,合肥零下三度,她穿了件红色羽绒服,说“冲喜”。
法院门口蹲满自媒体,长枪短炮对着她“183天寡妇能不能分到2000万”。
她摘了口罩,对着镜头一字一顿:“我不争千万,只要25万4,还清债,剩下的全捐给ICU门口蹲着的女人。
”说完转身进法院,背影瘦成一把尺,量的是人心。
我在屏幕前搓了搓手,忽然想起她钱包里那颗化掉的糖——原来甜味从来不是给病人的,是给活下来的人一口继续生活的底气。
母亲出殡那天,一个瘸腿乞丐来磕头,他说出身份,我当场跪下了
我娘入土的头天,村口瘸着腿的乞丐咚地跪在灵前,磕得额头见血!
灵堂里的香烧得正旺,烟雾绕着我娘的黑白照片转。
照片上她笑得温和,眼睛弯成月牙。
我刚给娘烧完纸,手里的孝棍还没放下。
就听见院门口传来拖拽的脚步声,一瘸一拐的,踩在泥地里咕叽响。
抬头一看,是个乞丐。
破棉袄烂得露着棉絮,裤腿卷到膝盖,一条腿明显短了一截,靠着一根磨得发亮的木棍支撑。
脸上沾着灰,头发乱得像鸡窝,只有一双眼睛,亮得惊人。
他没等院里人反应,径直就往灵堂冲。
堂嫂张兰端着一碗供果,吓得往旁边躲,供果差点撒在地上。
“哎!你干啥!” 堂嫂的嗓门亮,在灵堂的肃穆里格外突兀。
乞丐没理她,扑通一声,重重跪在灵前的水泥地上。
那声响,震得我耳朵嗡嗡疼。
他双手扶地,额头往下磕,一下,两下,三下。
第三下磕完,额头就红了,慢慢渗出血珠。
我心里火一下子上来了。
这是我娘的灵堂,不是谁都能来瞎磕的。
村里白事有规矩,外人来吊唁得通个气,哪有这样直冲进来的?
“你快起来!” 我往前迈了两步,伸手想去拉他,“有话好好说,别在这胡闹!”
他却猛地甩开我的手,力气大得惊人。
“别碰我!” 他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带着哭腔,“我要给婶子磕头!她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婶子?
我愣了一下,脑子转了半天,也想不起村里有哪个亲戚跟这乞丐沾边。
堂嫂凑过来,拉了拉我的孝布,小声说:“明子,别莽撞,看他这样子不像装的。”
她手里还端着那碗供果,眼神里满是疑惑。
这时,村支书赵建国从外面进来了。
他刚去地里通知完最后一批帮忙抬棺的人,身上还沾着泥土,看见灵前跪着的乞丐,皱起了眉头。
“这位兄弟,” 赵支书走过去,声音沉稳稳的,“今天是李家婶子的白事,有啥难处你好好说,别在灵前这样。”
乞丐抬起头,额头上的血顺着脸颊往下流,混着脸上的灰,变成一道道黑印。
他盯着我娘的照片,眼睛里的泪一下子涌了出来,顺着黑印往下淌。
“赵支书,” 他哽咽着,“我叫王建军,我找李秀莲婶子,找了十几年了。”
李秀莲是我娘的名字。
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个名字,除了家里人和村里的长辈,外人很少叫。
“你认识我娘?” 我忍不住问,声音有点发紧。
王建军点点头,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又被哭声堵了回去。
堂嫂递过去一张纸巾,他接过来,胡乱擦了擦脸,露出一张算不上周正,但很老实的脸。
“婶子当年在火车站捡的我,” 他终于缓过一口气,一字一句地说,“那年我十岁,爹娘没了,跟着一伙人乞讨,被人欺负,差点冻死在火车站的角落里。”
灵堂里静了下来,只有香燃烧的滋滋声,还有王建军断断续续的哭声。
村里来帮忙的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围在旁边,脸上满是好奇。
我娘一辈子善良,村里谁有难处她都愿意搭把手,但捡过乞丐这事,我从来没听她提过。
“我记得清清楚楚,” 王建军抹了把眼泪,“那天雪下得特别大,我穿着单衣,缩在候车室的墙角,冻得直打哆嗦,连哭的力气都没有。”
“婶子抱着一个包袱,从火车上下来,看见我,就走过来了。”
“她摸了摸我的头,手特别暖,问我‘娃,你爹娘呢’,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哭。”
他说着,手不自觉地摸了摸自己的头,像是还能感受到当年的温度。
“婶子没多问,把我带到附近的小饭馆,给我点了一碗热汤面,还有两个馒头。”
“我饿坏了,狼吞虎咽地吃,她就在旁边看着,给我递水,说‘慢点吃,别噎着’。”
我想起我娘,她就是这样,见不得别人受苦。
小时候村里有流浪狗,她都会端剩饭出去喂,更别说一个冻得瑟瑟发抖的孩子。
“吃完面,婶子问我愿不愿意跟她走,” 王建军的声音低了下去,“我说愿意,我怕再被人欺负,也怕冻死。”
“她就把我带回了村里,给我找了身干净的旧衣服,是她儿子穿剩下的,” 他看了我一眼,“应该就是你小时候的衣服吧,我记得上面有个小老虎的图案。”
我心里一震。
我小时候确实有一件带老虎图案的棉袄,是我娘亲手缝的,后来不知道弄哪去了,我娘说 “送给需要的人了”,原来竟是给了他。
“婶子给我取名建军,” 他接着说,“她说‘叫建军,以后要像解放军一样,有志气,有担当’。”
“她把我安排在村西头的旧磨坊里住,每天给我送吃的,还让我跟村里的孩子一起上学。”
村西头的旧磨坊,我有印象,小时候经常去那里玩,后来荒废了,没想到娘当年把他安置在那儿。
“我那时候调皮,不爱上学,总逃课去掏鸟窝,” 王建军的脸上露出一丝愧疚,“婶子知道了,也不打我,也不骂我,就坐在磨坊门口,给我缝衣服,跟我说‘娃,只有读书才能有出路,婶子不指望你报答我,只希望你以后能堂堂正正做人’。”
“她还说,她小时候家里穷,没读过书,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识字。”
我想起我娘,她确实不识字,每次给我写信,都是让村里的小学老师帮忙写,自己再照着描几个简单的字。
“我听了婶子的话,开始好好读书,” 王建军的声音高了些,“她每个月都会给我几块钱,让我买作业本和铅笔,还总给我带好吃的,有一次她给我带了个苹果,说是别人送的,她舍不得吃,给我留着。”
“我后来才知道,那时候婶子家里也不富裕,你爹身体不好,家里就靠婶子种地、养猪过日子,她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总想着我。”
旁边的堂嫂叹了口气:“李婶就是这样的人,心善得很,当年村里谁家里有难处,她都第一个站出来。”
赵支书也点点头:“是啊,李家婶子的为人,村里没人不佩服。”
王建军继续说:“我读完小学,考上了镇上的初中,婶子送我去报到,给我买了新书包,还有一身新衣服,她说‘建军,好好读书,将来考个好大学,走出大山’。”
“初中三年,婶子每个月都要步行十几里路,到镇上给我送生活费,每次都给我带些家里种的菜,还有她腌的咸菜。”
“有一次下雨,路滑,她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还坚持把钱送到我手里,说‘别耽误你吃饭’。”
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娘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事,她总是报喜不报忧,不管受了多少苦,都自己扛着。
“我考上高中那年,婶子给我寄了五百块钱,” 王建军的声音又哽咽了,“她说那是她卖了两头猪的钱,让我好好读书,不用惦记她。”
“我那时候不懂事,以为婶子家里条件好了,就心安理得地用了那笔钱,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你爹那时候病重,需要花钱看病,婶子是把给你爹看病的钱,省出来给我交了学费。”
“我真是个白眼狼啊!” 他猛地又磕了一个头,额头的血又流了出来。
“你别这样!” 我赶紧拉住他,“我娘要是知道你这样,肯定会心疼的。”
“我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南方的一所大学,” 王建军接着说,“婶子特别高兴,特意杀了一只鸡,给我做了鸡汤,让我带着路上喝。”
“她送我到村口,看着我上车,说‘建军,到了学校要好好照顾自己,好好学习,将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她还说,以后不用我惦记她,她会照顾好自己和你爹。”
“我到了大学,开始勤工俭学,攒了点钱,想寄给婶子,可她每次都让村里的人给我带话,说她不需要,让我把钱留着自己用。”
“我知道她是心疼我,不想让我分心,所以就想着,等我毕业了,有出息了,一定好好报答她。”
“大学毕业后,我找了份不错的工作,攒了几年钱,想自己创业,” 王建军的眼神暗了下去,“我跟婶子说了我的想法,她特别支持我,还偷偷给我寄了一万块钱,说是她这些年攒的养老钱。”
“我拿着那笔钱,雄心勃勃地开始创业,可没想到,生意失败了,不仅赔光了所有的钱,还欠了一屁股债。”
“那时候我觉得天都塌了,不想活了,可一想到婶子,我又舍不得,我还没报答她的恩呢。”
“为了躲债,我四处奔波,没想到在路上出了车祸,腿断了,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他指了指自己的瘸腿,脸上满是绝望。
“我成了个废人,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更别说报答婶子了,” 他哭着说,“我没脸见她,所以这几年一直没敢回来,只是偶尔从村里出来的人嘴里,打听她的消息。”
“前几天,我听说婶子走了,” 他的哭声更大了,“我连夜从外地赶回来,就是想给她磕个头,送她最后一程,还她的恩!”
“婶子对我恩重如山,没有她,就没有我王建军,可我到最后,连她最后一面都没见到,我对不起她啊!”
他趴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肩膀一抽一抽的。
灵堂里的人都红了眼眶,堂嫂偷偷抹着眼泪,赵支书叹了口气,点燃了一支烟。
我站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从来不知道,我娘还有这样一段过往,她竟然默默资助了一个孤儿十几年,付出了那么多,却从来没跟我提起过。
我想起小时候,娘总是把好吃的留给我,自己吃咸菜馒头;想起她每个月都要去邮局,说是 “帮个熟人寄点东西”;想起她总说 “做人要善良,多帮别人一把,积德行善”。
原来,她一直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这句话。
我低头看着趴在地上的王建军,他的瘸腿扭曲着,身上的衣服又脏又破,可他的心里,却装着对我娘满满的感恩。
而我,作为我娘的亲儿子,却从来不知道她的这些付出,甚至有时候还会抱怨她太节俭,抱怨她管得太多。
我真是太不孝了!
“建军哥,” 我蹲下身,轻轻扶起他,声音带着愧疚,“你起来,我娘要是知道你这么惦记她,肯定会很高兴的。”
王建军抬起头,泪眼朦胧地看着我:“明子,我对不起婶子,我没来得及报答她。”
“你不用报答她,” 我摇了摇头,“我娘做这些,从来就没想过要报答,她只希望你能好好活着,堂堂正正做人。”
“你现在这个样子,她要是看到了,肯定会心疼的,” 我接着说,“以后,你就留在村里吧,跟我一起生活,我给你养老。”
王建军愣住了,眼睛里满是不敢相信:“明子,这…… 这怎么好意思?我是个废人,只会给你添麻烦。”
“你别这么说,” 我握住他的手,他的手粗糙得像树皮,满是老茧,“你是我娘认定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兄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堂嫂也走过来说:“建军兄弟,明子说得对,以后你就住我家隔壁的空房,我给你收拾收拾,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
赵支书也点点头:“是啊,建军,李家婶子是我们村的骄傲,你是她救助的孩子,我们村里也不会不管你,以后有啥难处,就跟我说。”
王建军看着我们,眼泪又流了下来,这次是感动的泪。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他哽咽着说,“我……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不用谢,” 我笑了笑,擦了擦眼角的泪,“这都是我娘希望看到的。”
灵堂里的香还在烧着,烟雾缭绕中,我娘的照片笑得依旧温和。
我知道,她在天上看着我们,肯定很欣慰。
接下来的几天,王建军一直留在灵堂,帮着打理我娘的后事,他瘸着腿,忙前忙后,一点都不含糊。
村里的人也都对他很好,有人给他送衣服,有人给他送吃的,还有人主动帮他联系医生,想给他看看腿。
送葬那天,王建军拄着木棍,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一步一步,走得很稳。
他说,他要亲自送我娘入土,给她磕最后一个头。
到了墓地,棺材放进墓穴,王建军扑通一声跪了下去,磕了三个响头,额头又磕出了血。
“婶子,你安息吧,” 他哭着说,“以后我会好好活着,不辜负你对我的期望,我会替你照顾好明子,照顾好这个家。”
我站在旁边,也跪了下去,给我娘磕了三个头。
“娘,你放心吧,” 我在心里说,“我会照顾好建军哥,会像你一样,做个善良的人,多帮别人一把。”
葬礼结束后,我把王建军带回了家。
我给了收拾了一间干净的房间,买了新的被褥和衣服,还带他去镇上的医院检查了腿。
医生说,他的腿是陈旧性骨折,已经愈合了,但恢复得不好,所以才会瘸,如果好好调理,再做些康复训练,情况会好一些。
我让他留在家里,什么都不用干,安心养腿,可他闲不住,每天都帮着喂猪、种地,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堂嫂也经常过来帮忙,给我们做饭、洗衣,村里的人也经常过来探望他,给他送些土特产。
王建军的话不多,但人很老实,也很勤快,慢慢地,村里的人都喜欢上了他。
有一次,我跟他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他看着我娘的照片,轻声说:“明子,婶子真是个好人,这辈子能遇到她,是我最大的福气。”
我点了点头:“是啊,我娘这辈子,都在为别人着想,从来没为自己活过。”
“以后,我会替婶子好好活着,” 王建军说,“我会努力赚钱,把腿治好,然后做些有意义的事,帮助那些像我当年一样需要帮助的人。”
我看着他,心里很欣慰。
我知道,我娘的善良,已经传递给了他,也传递给了我。
日子一天天过去,王建军的腿在慢慢好转,他也开始学着做点小生意,在村里卖些日用品,生意还不错。
他赚了钱,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娘买了一束鲜花,放在她的照片前。
“婶子,我现在能自己赚钱了,” 他对着照片说,“我以后会越来越好的,你放心吧。”
我看着他,又看了看我娘的照片,突然觉得,我娘并没有离开我们,她一直都在,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我们的行动里。
她的善良,就像一粒种子,在我们心里生根发芽,开出了最美的花。
而我,也终于明白了,善良从来都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力量,一种能温暖人心,照亮前路的力量。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金钱和财富,而是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是那份不计回报的付出和感恩。
我娘用她的一生,教会了我这个道理。
而王建军的出现,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这份道理的重量。
往后的日子,我会和王建军一起,带着我娘的嘱托和期望,好好活着,做个善良的人,把这份温暖和爱,一直传递下去。
娘,你放心,我们都会好好的。
文档上传者
热门标签
相关文档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