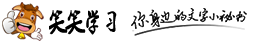欢迎来到98聘
写一篇《怀念朋友的作文》小技巧(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11-29 21:31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怀念朋友的作文,想要写得好、感人,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
1. "明确中心思想 (Clear Central Theme):" 你想通过这篇作文表达什么?是单纯地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表达对朋友离去的伤感与不舍?强调朋友在你生命中留下的深刻影响?还是怀念那份珍贵的友谊本身? 确定一个核心情感或主题,让全文围绕它展开,使文章更有深度和感染力。
2. "选择合适的切入点 (Choose an Appropriate Starting Point):" 不要试图写尽所有回忆,那会让文章显得松散、流水账。 选择一个具体的、有代表性的场景、物品、时刻或者一个让你印象深刻的细节作为开头。例如: 一件朋友送你的礼物。 一次难忘的旅行或经历。 朋友说过的一句话。 一个特定的习惯或动作。 好的开头能迅速抓住读者,并自然地引出你要表达的情感。
3. "运用生动的细节和具体事例 (Use Vivid Details and Specific Examples):" 怀念不是空泛的情感,需要用具体的细节来支撑。 回忆一些和朋友一起发生的有趣、感人、难忘的事情。这些事情应该是具体的,有画面感的。比如: 他/她当时的样子(外貌
91年,我去战友家做客,他女儿对我说:叔叔,我认识你20年了
火车是绿皮的。
车厢里混着一股方便面、汗味和廉价烟草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这是1991年,一个夏天。
我叫林峰,三十出头,从部队转业回来快五年了,在一家半死不活的国营机床厂当保卫科干事。
铁饭碗是铁饭碗,就是有点生锈。
这次请了三天假,是去一个我从没去过,却又无比熟悉的城市。
去看赵卫国的家人。
赵卫国是我战友,一个坑里爬出来的兄弟,过命的交情。
他走了,牺牲在了一次边境任务里。
那年,他女儿刚满一岁。
我一直没敢来。
不是忘了,是怕。怕看见他媳妇那双眼睛,怕看见那个没爹的孩子。
我欠他们的。
要不是为了推开我,那颗地雷下面埋着的就是我的骨头渣子。
今年,我终于攒够了胆子。
火车“咣当咣当”地响,像我这几年不安稳的心跳。
下了车,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空气里有煤烟的味道。
我按照信上的地址,七拐八拐,找到了一个老旧的家属院。
筒子楼,墙皮斑驳,楼道里堆着蜂窝煤和各种杂物。
我深吸一口气,敲响了三楼最里面那扇门。
门开了。
开门的是个女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头发简单地挽在脑后。
她比照片上憔ें悴一些,眼角有了细纹,但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
是李娟,卫国的媳妇。
“你……是林峰?”她声音有点抖。
我点点头,喉咙发紧,“嫂子,我来了。”
李娟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她侧过身,“快,快进来。”
屋子不大,两间房,但收拾得异常干净。
水泥地上铺着凉席,一张旧木桌,椅子,墙上最显眼的位置,挂着赵卫国的遗像。
穿着军装,笑得一脸灿烂。
我放下手里的网兜,里面是给孩子买的麦乳精和几斤苹果。
“嫂子,这些年,过得还好吗?”我问了句废话。
“好,都好。”李娟给我倒了杯水,搪瓷缸子,上面印着“劳动最光荣”。
“念念,快出来,叔叔来了。”她朝着里屋喊。
一个穿着小背心、扎着两个羊角辫的小女孩从门帘后面探出头来,怯生生地看着我。
这就是念念,赵念。
大眼睛,高鼻梁,像卫国。
“念念,叫叔叔。”李娟拉着她。
小女孩看着我,不说话,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
看得我心里发毛。
我蹲下来,努力挤出一个笑脸,“念念,你好啊,叔叔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
我以为她会害羞,或者会扑过来要糖。
都没有。
她就那么看着我,看了足足有半分钟,然后用一种和她年龄完全不符的,异常平静的语气,说了一句让我浑身汗毛倒竖的话。
“叔叔,我认识你20年了。”
空气瞬间凝固了。
李娟的脸“唰”地一下白了,她赶紧拉过女儿,拍了她一下,“瞎说什么呢!跟叔叔道歉!”
小女孩抿着嘴,不说话,眼睛里有种说不出的固执。
我愣在原地,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
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说认识我二十年了?
1991年,往前推二十年是1971年。
那时候,我才十岁出头,还在村里玩泥巴。
我强笑着打圆场,“没事没事,小孩子嘛,童言无忌。”
李娟一脸尴尬,连声道歉,“林峰,你别介意,这孩子,有时候就爱胡说八道。”
我摆摆手,表示不在意,但那句话像一根刺,扎进了我脑子里。
午饭是面条,卧了两个荷包蛋。
李娟的手艺很好,可我吃得心不在焉。
念念就坐在我对面,小口小口地吃着面,时不时抬眼看我一下。
那眼神,不像一个孩子看陌生人的眼神。
倒像……倒像一个老朋友。
这个念头让我打了个冷战。
“念念今年上学前班了吧?”我没话找话。
“嗯,九月份就上一年级了。”李娟给女儿夹了块西红柿。
“在学校听话吗?”
“听话,就是……就是不爱跟别的小朋友玩,总说他们太幼稚。”李娟叹了口气,语气里带着一丝忧虑。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一个六岁的孩子,嫌同龄人幼稚?
吃完饭,李娟去洗碗。
我坐在小板凳上,看着墙上卫国的照片。
念念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地走到了我身边。
“叔叔,你是不是在想我爸爸?”
我一惊,转过头看她。
“是啊。”我摸了摸她的头,“想你爸爸了。”
“爸爸说,你外号叫‘疯子’,因为你训练起来不要命。”
我的手僵在了半空中。
“疯子”这个外号,是新兵连的时候卫国给我起的。
除了我们那批最铁的兵,没人知道。
我转业后,就再也没人这么叫过我。
李娟……李娟是知道的,但她是个细心的人,不可能把这种带着点粗鲁的外号讲给孩子听。
“谁……谁告诉你的?”我的声音有点干。
“我爸爸说的。”念念仰着脸,一脸理所当然。
“你……你见过你爸爸?”
“见过啊,在梦里。”她答得很快,“他老是来我梦里,给我讲故事,讲你们在部队里的事。”
我感觉后背的冷汗把衬衫都浸湿了。
梦?
一个孩子荒诞的梦?
可这梦,也太真实了。
“他还说什么了?”我鬼使神差地追问。
“他说,你最讨厌吃芹菜,一闻到味儿就想吐。”
我彻底愣住了。
这件事,是我的一个怪癖,连我爹妈都只是大概知道我不爱吃,但绝对不知道我会到想吐的程度。
只有赵卫国,只有他亲眼见过。
那次炊事班包芹菜馅饺子,我闻着味儿就跑到厕所吐了个天翻地覆,他一边笑我没出息,一边给我递水。
李娟端着一盘切好的西瓜从厨房出来,看见我们俩的样子,奇怪地问:“你们爷俩聊什么呢,这么严肃?”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该怎么说?
说你女儿好像认识一个二十年前的我?
说她知道我所有的秘密?
说她……像卫国本人在跟我说话?
李娟会以为我疯了。
“没……没什么,”我勉强笑了笑,“念念这孩子,真聪明。”
李娟把西瓜递给我,“快尝尝,刚从井水里拔出来的,凉快。”
我拿起一块,咬了一口,冰凉的甜意顺着喉咙滑下去,却浇不灭我心里的那团邪火。
那天下午,我坐立难安。
念念也不来缠我,就自己坐在小板凳上,翻一本连环画。
很安静,安静得不像个孩子。
我借口出去抽根烟,站在筒子楼的走廊上。
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
风吹过来,带着邻居家炒菜的香味。
一切都充满了生活气息,真实得不能再真实。
可我却感觉自己像掉进了一个荒诞的梦里。
我狠狠吸了一口烟,试图用尼古丁麻痹自己混乱的神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巧合?
不可能有这么多巧合。
难道是李娟教的?
可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图什么?她看我的眼神,分明是担忧和不解,不像在演戏。
难道这孩子……真的有什么问题?
我不敢再想下去。
晚上,李娟收拾出里屋的小床给我睡,她带着念念睡在外屋。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床板很硬,能闻到被子上阳光晒过的味道。
隔着一层薄薄的木板墙,我能听到隔壁母女俩的呼吸声。
很轻,很均匀。
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昏暗的光影,脑子里乱成一锅粥。
卫国的脸,念念的脸,两张脸在我眼前不断重叠。
“叔叔,我认识你220年了。”
那句话,像个魔咒,在我耳边盘旋。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地快要睡着了。
就在这时,我听到外屋传来一阵极轻的啜泣声。
是李娟。
她压抑着,很小声,但我听得清清楚楚。
那种悲伤,像一把钝刀子,在黑夜里慢慢地割着人的心。
她是在想卫国吧。
我心里一阵酸楚。
这些年,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该有多难。
过了一会儿,哭声停了。
然后,我听到了念念的声音,奶声奶气的,却异常清晰。
“妈妈,别哭了。”
“爸爸说,他看着我们呢,你要是老哭,他会心疼的。”
我浑身的血,在那一瞬间,几乎凝固了。
第二天一早,李娟的眼睛有点肿。
她像没事人一样,张罗着早饭,稀饭,馒头,还有一碟咸菜。
吃饭的时候,气氛有点沉闷。
我几次想开口问问昨晚的事,但看着她强撑的笑脸,又把话咽了回去。
吃完饭,李娟说单位有点事,要去一趟。
“林峰,你帮我照看一下念念,行吗?我很快就回来。”
“行,嫂子你放心去吧。”
李娟走了,屋里就剩下我和念念。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和一个知道我所有秘密的“小女孩”独处,这感觉太诡异了。
念念倒是很自在,她搬个小板凳坐到我面前。
“叔叔,我们下棋吧。”
她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木头棋盘,棋子都磨得包了浆。
是象棋。
我和卫国在部队的时候,最爱在休息的时候杀两盘。
他的棋风大开大合,悍不畏死,跟他的性格一模一样。
我的棋风,则更稳健,擅长防守反击。
我俩棋力相当,每次都杀得天昏地暗。
“你……你会下?”我有些意外。
“爸爸教我的。”
又是我爸爸。
我心里叹了口气,摆开了棋盘。
“行,叔叔陪你下一盘。”
我没当回事,想着随便走几步,哄哄孩子就行了。
第一步,她当头炮。
我飞象。
很常规的开局。
但是,走了十几步之后,我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
她的路数……
太熟悉了。
弃马抢攻,双车错杀,招招都透着一股子狠劲和不计后果的疯狂。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初学者,甚至不是一个普通棋手该有的路数。
这是赵卫国的棋路!
一模一样!
我额头上渗出了汗。
我不再留手,打起十二分精神,把她当成一个真正的对手。
棋盘上,炮火连天。
我仿佛又回到了部队那个闷热的午后,对面坐着的,是那个咧着嘴冲我坏笑的赵卫国。
“将军!”
念念清脆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
我低头一看,我的“帅”已经被她的双车锁死,再无生路。
我输了。
输得干干净净,毫无悬念。
我呆呆地看着棋盘,半天说不出话来。
“你……这棋是谁教你的?”我抬起头,死死地盯着她。
“说了呀,爸爸教的。”念念眨着大眼睛,一脸无辜。
“你爸爸怎么教你的?在梦里?”
“嗯。”她点点头,“他拿着棋盘,一步一步教我,还给我讲了很多棋谱,什么《橘中秘》、《梅花谱》。”
《橘中秘》,《梅花谱》。
这是我和卫国当年从一个老首长那里淘来的宝贝,我俩翻来覆去研究了好几年。
这件事,李娟都不知道。
我感觉自己的世界观正在被一寸寸地碾碎。
我站起身,在屋子里来回踱步。
这不对劲,这太不对劲了。
一个孩子,就算再聪明,再有天赋,也不可能到这种地步。
这不是天赋,这是……附体?
我被自己这个想法吓了一跳。
我是个军人,受了这么多年的唯物主义教育,怎么会想到这种牛鬼蛇神的东西?
可眼前的现实,又该如何解释?
我看着念念那张天真无邪的脸,心里却涌起一股寒意。
她到底是谁?
或者说,她身体里住着的,到底是谁?
“叔叔,你怎么了?你的脸好白。”念念站起来,拉了拉我的衣角。
我猛地回过神,看着她澄澈的眼睛,那股寒意又被一种莫名的心疼取代了。
不管怎么样,她只是个孩子。
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没事,叔叔就是……有点累了。”我揉了揉太阳穴。
“你是不是在想南疆的事?”她突然问。
我的心脏,像被重锤狠狠砸了一下。
南疆。
那是我们执行最后一次任务的地方。
也是卫国牺牲的地方。
这个地名,我回来后,对谁都没有提起过,包括我的家人。
它像一道刻在我心里的伤疤,不敢碰,不能碰。
“爸爸说,他不怪你。”
念念的声音很轻,却像一道炸雷在我耳边响起。
“他说,那是他的选择。”
“他还说,让你别再背着了,好好活着。”
我的眼泪,在那一刻,决堤了。
我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蹲在地上,像个孩子一样,哭得泣不成声。
这些年,我强装正常,上班,下班,相亲,生活。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背着一座山。
是卫国的死。
我总觉得,如果当时我反应再快一点,如果我没有犹豫那半秒,死的就不会是他。
这份愧疚,像毒蛇一样,日日夜夜啃噬着我的心。
我不敢去想,不敢去回忆。
我把它埋在心底最深处,用厚厚的壳包裹起来,以为这样就可以假装它不存在。
可是今天,被一个六岁的孩子,轻而易举地戳破了。
“爸爸说,他很想你。”
念念伸出小手,轻轻地拍着我的背。
一下,又一下。
就像当年,卫国拍着我的肩膀,说:“疯子,别怕,有我呢。”
我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她。
她的小脸上,没有孩子的懵懂,只有一种超乎年龄的、温暖的悲伤。
那一刻,我真的信了。
我相信,是我的兄弟,是赵卫国,借着他女儿的口,来跟我做最后的告别。
来把我从愧疚的深渊里,拉出来。
“老赵……”我哽咽着,对着空气,也对着眼前的孩子,叫出了那个名字。
“我对不起你……”
“爸爸说,兄弟之间,没有这三个字。”念念替他。
我哭得更凶了。
积压了五年的痛苦、思念、自责,在这一刻,尽数倾泻而出。
等李娟回来的时候,就看到我和念念两个人,眼睛都红红的。
她吓了一跳,“这是怎么了?林峰,是不是念念惹你生气了?”
我摇摇头,站起来,擦干眼泪。
“没有,嫂子。”
我看着她,郑重地说:“我就是……想卫国了。”
李娟的眼圈也红了,她低下头,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跟李娟谈了很久。
我把我心里的疑惑,和今天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她。
我以为她会觉得我疯了,或者会害怕。
但她没有。
她只是静静地听着,脸上是一种我看不懂的,混杂着悲伤和释然的表情。
等我说完,她沉默了很久。
“其实……我早就觉得不对劲了。”她缓缓开口。
“念念这孩子,从小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她太安静了,也太懂事了。”
“她两三岁的时候,别的小孩还在哭闹,她就能自己一个人坐着玩半天。”
“有时候,她看着卫国的照片,会自言自语,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
“后来,她长大一点,就开始说一些关于卫国的事。说的那些细节,连我都不知道。”
李娟的声音带着颤抖。
“我一开始也害怕,带着她去医院看过,医生说孩子很正常,可能就是……单亲家庭的孩子,比较敏感,爱幻想。”
“我也试着这么安慰自己。可是,她说的越来越多,越来越真。”
“她知道卫国喜欢在饭后抽烟,知道他睡觉会打轻微的呼噜,知道他有一双翻毛皮鞋,鞋底有个小洞……”
这些,都是只有夫妻之间才知道的私密细节。
“我问她怎么知道的,她就说是爸爸在梦里告诉她的。”
李娟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闪着泪光。
“林峰,你说,是不是卫国他……不放心我们娘俩,所以……所以他的魂儿,一直没走,就守在念念身边?”
这是一个母亲,在绝望中能想到的唯一解释。
一个带着点迷信,却又充满了爱的解释。
我不知道该怎么。
从理智上,我无法接受。
但从情感上,我多么希望这是真的。
我希望我的兄弟,真的还在以某种方式,守护着他的家人。
“嫂子,不管怎么样,念念是你的女儿,也是卫国的女儿。”我说,“她是个好孩子。”
李...
李娟点点头,眼泪掉了下来。
“我知道。有时候看着她,我就觉得卫国还在。他只是换了个方式,陪着我。”
那一晚,我彻底失眠了。
我躺在小床上,脑子里反复回想着这几天的点点滴滴。
念念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
还有李娟说的那些话。
一个想法,在我脑海里,越来越清晰。
也许,真相并不是什么鬼神附体。
也许,答案就在李娟身上。
第二天,我没有急着走。
我对李娟说,我想再多待两天,陪陪念念。
李娟当然同意。
这两天,我没有再刻意去试探念念。
我就是陪着她,给她讲故事,带她去院子里玩。
我发现,她虽然心智比同龄人成熟,但终究还是个孩子。
她会因为一颗糖果而开心,会因为摔了一跤而哭鼻子。
她很依赖李娟,总是像个小尾巴一样跟在妈妈身后。
而我,则在暗中观察李娟。
我发现,李娟有一个习惯。
她每天晚上,在念念睡着后,都会拿出卫国的照片,对着照片,絮絮叨叨地说很久。
说的都是白天发生的事。
“卫国,今天林峰来了,你最好的兄弟。他瘦了,也憔悴了,看着让人心疼。”
“卫国,今天念念又赢了你兄弟一盘棋,你高不高兴?这丫头,下棋的狠劲儿,跟你一模一样。”
“卫国,你放心,我会好好把念念带大,让她成为你的骄傲。”
她就那么对着一张不会说话的照片,说着,笑着,哭着。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她以为念念已经熟睡的时候。
可孩子,真的睡熟了吗?
或者,在半梦半醒之间,这些话,像种子一样,一颗一颗,种进了她的潜意识里?
我还有一个发现。
李娟的床头,放着一个上了锁的木箱子。
有一次,她打开箱子拿东西,我无意中瞥了一眼。
里面全是卫国的遗物。
军功章,写了一半的家信,还有……还有好几本厚厚的日记。
我心里猛地一动。
一个大胆的猜测,在我心中成型。
我必须验证它。
那天下午,我趁着李娟上班,念念在午睡。
我走进了她们的房间。
我告诉自己,这样做不对,是侵犯别人的隐私。
但如果不搞清楚,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
那个木箱子,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打开。
我用一根铁丝,很轻易就撬开了那个老旧的锁头。
我的心跳得很快。
箱子里,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卫国的日记。
我拿起最上面的一本,翻开了。
熟悉的字迹,扑面而来。
那是卫国的笔迹,龙飞凤凤舞,带着一股军人的豪迈。
日记里,记录了我们从新兵连到最后一次任务,几乎所有的点点滴滴。
那些我们一起扛枪,一起喝酒,一起吹牛的日子。
那些我们说过的私房话,开过的玩笑。
我讨厌吃芹菜的事。
我的外号“疯子”。
我们在南疆的约定。
甚至……那盘象棋的残局。
所有的一切,都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记录在上面。
我一页一页地翻着,手在抖。
原来,卫国是个这么细心的人。
他把我们之间的友谊,看得那么重。
我翻到了最后一页。
那是他牺牲前一天写的。
“明天要进山了,任务很危险。有点想家,想李娟,想刚出生的念念。”
“也想疯子那小子。我跟他说好了,要是谁回不来,另一个人,就要把对方那份也活出来,还要照顾好对方的家人。”
“林峰,兄弟,如果我回不去了,别难过。替我,好好活着。”
我的眼泪,滴落在泛黄的纸页上,洇开了一片墨迹。
我终于明白了。
一切都明白了。
根本没有什么转世,没有什么附体。
真相,远比那些猜测,更令人心碎,也更令人温暖。
李娟,在丈夫牺牲后,陷入了巨大的悲痛。
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这些日记。
无数个夜晚,她一边流着泪,一边读着这些日记。
她对着尚在襁褓中的女儿,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日记里的故事。
讲述着她从未谋面的父亲,和父亲那位叫林峰的、最好的兄弟。
她把自己的思念,把日记里的每一个字,都揉碎了,讲给了念念听。
而念念,这个在母亲的悲伤和思念中长大的孩子。
她的童年,没有父亲的陪伴,只有这些关于父亲的故事。
这些故事,听得太多,太深。
以至于,在她的世界里,故事和现实的界限,变得模糊了。
她把母亲的记忆,当成了自己的记忆。
她把日记里的那个“林峰”,当成了她认识了很久很久的朋友。
所以,她会说,她认识我220年了。
那不是她认识我的时间。
那是她父亲赵卫国,认识我的时间。
那是我们那段持续了二十年的友谊。
她不是被附体了。
她只是用一个孩子的方式,承载了父亲的记忆,和母亲的爱。
我把日记放回箱子,锁好,恢复原样。
我走出房间,看着窗外。
阳光很好,院子里有孩子在嬉笑打闹。
我心里的那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但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对李娟和念念的心疼。
一个女人,要有多爱她的丈夫,才会用这种方式,让他在女儿的生命里,“活”下去?
一个孩子,要有多爱她的父母,才会用自己的整个童年,去构建一个有父亲存在的世界?
下午,念念睡醒了。
她揉着眼睛,看到我,笑了。
“叔叔,你还在啊。”
我走过去,蹲下来,把她抱在怀里。
她的身体小小的,软软的。
“念念,叔叔问你个问题。”
“嗯。”
“你是不是……很想爸爸?”
念念在我怀里,点了点头。
“想。”
“那……你想不想听更多关于爸爸的故事?那些……他没来得及告诉你的故事?”
念念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想!”
我笑了。
“好,叔叔都讲给你听。”
我抱着她,坐在小板凳上。
我给她讲,我们是怎么在新兵连里打架,又怎么不打不相识,成了最好的朋友。
我给她讲,我们怎么在拉练的时候,把一个馒头分着吃。
我给她讲,卫国是怎么在射击比赛上拿了第一,得意得尾巴都翘上了天。
我给她讲,他又是怎么在给我写信的时候,抓耳挠腮,一个字都憋不出来。
我讲了很多很多。
那些日记里有的,没有的。
念念听得入了迷,小脸上,一会儿笑,一会儿又撅起嘴。
李娟回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画面。
她站在门口,看着我们,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流着泪。
那天,我没有拆穿那个秘密。
我不想。
对于她们母女来说,这个美丽的“谎言”,是她们活下去的支撑。
我为什么要残忍地把它打碎?
如果卫国真的在天有灵,他一定也希望,能以这种方式,继续陪伴着他的妻女。
我要做的,不是揭开真相。
而是加入她们,一起守护这个秘密。
我要把卫国没讲完的故事,继续讲下去。
我要替他,看着念念长大。
我要替他,照顾好李娟。
我要把我兄弟那份,一起活出来。
临走的前一天,我对李娟说:“嫂子,让念念认我当个干爹吧。”
李娟愣住了,随即,泪如雨下。
她用力地点着头。
我没再提调动工作的事,但心里已经做了决定。
这个城市,我必须来。
回到单位,我立刻递交了调动申请。
理由是……想换个环境。
领导很不解,同事也劝我。
没人知道,我不是去换个环境。
我是去赴一个迟到了五年的约定。
我是去见我的家人。
手续办得很慢,花了大半年的时间。
这期间,我和李娟通了很多信。
信里,我们聊工作,聊生活,聊念念的学习。
李娟说,自从我上次去过之后,念念开朗了很多,也开始愿意和别的小朋友玩了。
她说,念念总问,干爹什么时候再来看她。
每当看到这些,我就觉得,我做的一切,都值了。
1992年春天,我的调令终于下来了。
我被调到了那个城市的一家分厂,还是做保卫工作。
我走的那天,我们厂的老书记拍着我的肩膀说:“林峰,你是个好兵,也是个好人。”
我笑了笑,没说话。
我不是什么好人。
我只是一个想赎罪的,普通的退伍兵。
我再次坐上了那趟绿皮火车。
同样的车厢,同样的味道。
但我的心情,已经完全不同。
上一次,是忐忑,是沉重。
这一次,是踏实,是归宿。
下了车,我没有先去单位报到,而是直接去了那个熟悉的筒子楼。
我敲开门。
开门的,是念念。
她长高了一点,头发也长了。
看到我,她愣了一下,然后,爆发出巨大的惊喜。
“干爹!”
她一下子扑进了我的怀里。
“干爹,你终于来了!”
我抱着她,感觉心里被填得满满的。
李娟从厨房里跑出来,围着围裙,手里还拿着锅铲。
看到我,她也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你这孩子,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我想给你们个惊喜。”我说。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吃了一顿团圆饭。
我告诉他们,我调过来了,以后,就不走了。
李娟没说话,只是一个劲地给我夹菜。
念念高兴得手舞足蹈。
吃完饭,念念又拖出了那副象棋。
“干爹,杀一盘!”
“好!”
我们又摆开了战场。
这一次,我没有再感到诡异和惊恐。
我的心里,只有温暖。
我知道,坐在我对面的,是念念。
但我也知道,我的兄弟,赵卫国,他也在。
他就在这间屋子里,在我们身边,看着我们。
他的爱,他的记忆,他的精神,已经通过念念,永远地活了下来。
后来,我成了这个家真正的一员。
我像一个真正的父亲一样,送念念上学,给她开家长会,在她被欺负的时候,替她出头。
我也像一个真正的丈夫一样,帮李娟分担家务,修家里的电器,在她生病的时候,照顾她。
我们之间,没有说过一个爱字。
但我们都心知肚明。
我们三个人,是在替赵卫国,组成一个完整的家。
念念再也没有说过那句“我认识你20年了”。
她不需要了。
因为,我已经成了她生命里,实实在在的一部分。
有时候,她还是会说起“爸爸在梦里说”。
每当这时,我和李娟就会相视一笑。
我们都知道,那是我们共同的,最宝贵的秘密。
有一年清明节,我带着李娟和念念,去了南疆的烈士陵园。
我们找到了赵卫国的墓碑。
照片上,他还是那么年轻,笑得那么灿烂。
我把一瓶他最爱喝的二锅头,洒在了墓前。
“兄弟,我来了。”
“我把你媳妇和闺女,都带来了。”
“我把你没走完的路,走下去了。”
“你,在那边,安心吧。”
李娟和念念,都哭了。
我没有哭。
我只是看着墓碑上的照片,笑了。
我知道,他看得到。
他也一定在笑。
从南疆回来后,在一个很平常的晚上。
我和李娟坐在客厅看电视,念念在自己房间写作业。
李娟突然对我说:“林峰,我们……结婚吧。”
我愣住了。
她看着我,眼神很认真。
“不是为了别的,就是……想正大光明地,当一家人。”
“念念也长大了,她需要一个完整的家。”
我看着她,看了很久。
然后,我点了点头。
“好。”
我们的婚礼,办得很简单。
没有请太多人,就是单位的几个同事,和院子里的老邻居。
那天,念念穿着一身新裙子,像个小公主。
她一手牵着我,一手牵着李娟,笑得比谁都开心。
司仪在台上问我:“林峰先生,你愿意娶李娟女士为妻,一生一世,不离不弃吗?”
我看着身边的李娟,她也正看着我。
她的眼睛里,有泪光,有感激,还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属于女人的温柔。
我没有立刻。
我转过头,看了一眼墙上。
那里,依然挂着赵卫国的照片。
照片里的他,穿着军装,微笑着,仿佛在祝福我们。
我深吸一口气,转回头,握紧了李娟的手。
“我愿意。”
我不是在取代谁。
我只是在完成一个承诺。
一个对兄弟的承诺,一个对自己的承诺。
从1991年,那个小女孩对我说出那句奇怪的话开始。
我的人生,就拐了一个弯。
我从一个背着沉重过去的行尸走肉,变成了一个有未来,有牵挂,有家的人。
有时候,我也会想。
念念那天说的,到底是孩子无心的呓语,是一个家庭在创伤下的集体记忆移植,还是……真的有某种无法解释的,超越生死的感应?
我已经不想去追究答案了。
因为,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赵卫国用他的死,换了我的生。
而我,用我的后半生,延续了他的家。
我们是兄弟。
这,就够了。
守一窗寂寞,念一段过往,想一个最爱的人
说真的,有些人你越是见不到,脑子里反而越清晰。
这不是什么毛病,是大脑在跟你玩真的。
去年有个心理学研究挺有意思,说长期惦记一个人,大脑里真的会留下"情感印记"。
就像你小时候摔破的膝盖,疤可能淡了,但一摸上去总觉得那块皮肤不太一样。
思念也是这个道理,神经科学家发现,深刻的情感记忆会激活大脑的奖赏回路——说白了,想他/她的时候,大脑在偷偷给你发糖吃。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人明明已经不在生活里了,想起来的瞬间还是甜苦交加。
现在人都说要及时止损,要快速翻篇。
但67%的人(对,就是今年那个社交媒体报告)承认自己会通过文字表达思念,发朋友圈仅一人可见,发消息再撤回,或者像老一辈那样写日记。
方式变了,本质没变。
疫情那三年让很多人体验了一把"隔岸相牵"的滋味,物理距离拉远了,反而第一次看清自己心里到底装着谁。
有个朋友隔离期间翻出了十年前的信件,边看边哭,说现在微信聊得再多,也找不回那种一笔一划的郑重感。
其实吧,这种"放不下"的状态,在当代反而成了稀缺品。
信息爆炸的时代,什么都快,三天认识,五天暧昧,一周没联系就自动默认gameover。
能持续想念一个人,某种程度上说明你的情感系统还没被算法同化成快消品。
那些说"时间会冲淡一切"的人,可能没体验过真正的刻骨铭心。
时间冲走的是杂质,留下的才是真金。
但这里有个误区得提醒一下。
思念不等于要打扰,更不等于自我感动式的等待。
灵魂相守的前提是,你得先守好自己的生活。
一窗寂寞可以,但不能满屋狼藉。
该工作工作,该社交社交,把那个人放在心里某个特定位置,而不是让他/她占据全部内存。
这样即使哪天真的重逢,你也是个完整的自己,而不是一个被思念掏空的壳子。
说到底,这种情感不是病态,是人性里最顽固也最温柔的部分。
它证明了你曾经真实地、深刻地活过。
那些深夜刷手机时突然停下的瞬间,那些看到某个表情包就愣住的时刻,都是生活在提醒你:有些风景,一旦入眼,真的就是一辈子。
文档上传者
热门标签
相关文档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