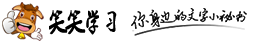欢迎来到98聘
推荐《接受批评作文》相关写作范文范例(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11-30 17:16

写作核心提示:
这是一篇关于写作文时应注意接受批评的文章:
"学会在批评中成长:写好作文的必修课"
作文,作为语文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语言文字的运用,更是思维能力和情感表达的体现。从提笔构思到最终落墨,整个过程充满了探索与创造。然而,任何创作都并非完美无瑕,当我们将自己的心血之作呈现在他人面前时,接受批评便成了不可或缺的一环。学会正确地接受批评,是每一位写作者提升作文水平、实现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那么,在作文写作中,我们应注意哪些事项来更好地面对和吸收批评呢?
"第一,保持开放的心态,正确认识批评的价值。" 批评并非是针对个人的否定,而是对作文本身提出的宝贵意见。优秀的批评能够精准地指出我们写作中的优点与不足,帮助我们发现自己可能忽略的问题。因此,首先要摒弃“挨批”的抵触情绪或“找茬”的心态。要认识到,无论是老师、同学还是其他读者提出的批评,都蕴含着改进作文、提升能力的契机。将批评视为成长的“催化剂”,而不是攻击的“子弹”,是接受批评的第一步。
"第二,虚心倾听,全面理解批评的内涵。" 当收到批评时,无论其形式如何(是具体的修改建议,还是笼统的评价),都应耐心倾听,仔细阅读。切忌只听取自己认同的部分,或急于反驳。要尝试站在批评者的角度,理解他们
爸爸请不要在饭桌上批评我:一封学生作文撕开中国式家庭教育伤疤
“你看看别人家孩子,再看看你!”
“考了98分?那2分去哪儿了?”
“一顿饭的时间,我连筷子都不敢抬。”
这不是影视剧台词,而是一篇五年级小学生作文《我最怕的一顿饭》里的原话。
文章被老师发到家长群后,全班沉默,妈妈红了眼眶,爸爸们集体失声。
这封信像一把刀,划开了无数中国家庭饭桌上的“隐形暴力”。
孩子写道:“每次吃饭,我都祈祷快点结束。数学考第二,说我粗心;英语少扣一分,说我不够拼;连我夹了一块排骨,爷爷都说‘成绩不好还敢吃肉?’”
“我不是不想好好吃,是根本咽不下去。”
短短六百字,评论区炸出上万共鸣:
“读着读着,我哭了——因为我小时候也这样。”
“原来不是我太敏感,是他们真的不懂伤害。”
我们总以为饭桌是团聚的地方,
可对很多孩子来说,那是一天中最紧张的‘审判时刻’。
成绩、排名、作业、表现……一顿饭,成了全天行为的总结大会。
更可怕的是,这种批评往往披着“为你好”的外衣。
家长觉得:我辛辛苦苦挣钱养你,说你两句怎么了?
可心理学研究早已证明:长期在压力下进食的孩子,不仅容易厌食、肠胃紊乱,更会形成‘低自我价值感’。
北京某儿童心理门诊数据显示:
近一年接诊的焦虑儿童中,67%明确提到‘害怕回家吃饭’,
原因不是饭菜难吃,而是“爸妈一边吃饭一边数落我”。
一位心理专家说:“饭桌本该是情感连接的场所,却被异化成控制与训导的战场。”
孩子越小,越会把父母的评价内化为“我是不是不够好”。
久而久之,他们学会的不是进步,而是——隐藏自己,讨好大人。
那个写作文的孩子后来告诉老师:
“其实那次考试全班第一,但我爸说‘第一名才有资格放松’。”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想考第一了。”
这句话,值得所有父母警醒。
真正的教育,不是抓住每一分钟纠正错误,
而是在轻松的时光里,让孩子愿意开口说话。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推行“饭桌三不原则”:
不谈学习
不批评孩子
不刷手机
取而代之的是:“今天有什么开心事?”“你最喜欢班里哪个同学?”“要是当一天老师,你会怎么上课?”
这些看似“没用”的对话,恰恰是亲子关系的黏合剂。
那位写作文的小男孩,自从家里实行“快乐晚餐”后,第一次主动说起同学间的矛盾,也第一次笑着说:“原来吃饭可以这么轻松。”
教育的本质,是点燃火,而不是浇冷水。
一顿饭的温度,决定了孩子心里有没有光。
下次当你想开口批评时,请先问自己:
我是想教育他,还是只想发泄我的焦虑?
别让本该温暖的饭桌,成为孩子童年最冷的记忆。
毕竟,胃装得下饭菜,心却装不下太多责备。
那个总批评我的老师,我记恨多年,同学会上才知他为我做了什么
手机在桌上嗡嗡震动的时候,我正盯着电脑屏幕上的一份报价单,看得眼睛发酸。
屏幕右下角的时间跳到了下午四点半,这个点儿,公司里的人心都开始浮了,像水壶里快烧开的水,咕嘟咕嘟地冒着泡,就等下班铃响的那一下。
我没理那手机,想着估计又是哪个卖房子的或者推销贷款的。
可它执着得很,震完一阵,歇口气,又开始新一轮的嗡嗡。
我老婆的微信弹了出来:“看手机,老同学找你。”
我这才有点不耐烦地把手机摸过来。
屏幕上是一个陌生的微信群,群名叫“育才中学98届3班同学会筹备组”。
我的手指悬在“同意”两个字上,犹豫了。
育才中学,98届3班。
这几个字像一把生了锈的钥匙,一下子捅开了我记忆里一扇不怎么愿意打开的门。门后头,站着一个人,一个我记了快二十年的人。
张怀民,我们的班主任,教语文的。
他个子不高,微胖,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戴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后面那双眼睛,好像总是在审视你,让你浑身不自在。
我对他没什么好印象,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记恨的。
这种记恨,不是因为他打过我或者骂过我,而是一种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被他用言语和眼神一点点打磨出来的挫败感。
“李伟,你这作文写的什么?流水账!你看看人家王波的,立意!思想!你的思想呢?”
“李伟,站起来!这首诗的意思,我昨天刚讲过,你又忘了?脑子拿来干嘛的?装浆糊吗?”
“你这个字,写得跟鸡爪子刨过一样,以后走到社会上,人家看你字识人,你这第一印象就完了!”
这些话,像一根根小刺,隔了这么多年,想起来,后背还隐隐约约地有点发麻。
我那时候,就是个普普通通的男孩子,有点贪玩,成绩中不溜秋,不算好,也绝对不差。可是在张怀民的嘴里,我好像浑身上下都是毛病,一无是处。
最让我耿耿于怀的,是高二那年的一次作文比赛。
我熬了好几个晚上,写了一篇自认为很不错的文章,关于我那个起早贪黑在菜市场卖菜的母亲。我写了她手上的老茧,写了她冬天里被冻得通红的耳朵,写了她算账时那股认真劲儿。
我自己写完都看了一遍又一遍,觉得特真诚。
结果交上去,张怀民把我叫到办公室,当着好几个老师的面,把我的作文本往桌上一扔。
“虚情假意!”
他敲着桌子,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上。
“写你妈辛苦,是为了博同情分吗?作文要的是真情实感,不是编故事!你这个年纪,哪来这么多愁善感的?心思要放在学习上,别搞这些花里胡哨的!”
我当时就懵了,站在那儿,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没编故事,那都是我亲眼看到的。可是在他眼里,就成了“花里胡哨”。
那次比赛,他推荐了班长王波去。王波写的是一篇读后感,引经据典,文采飞扬。
后来,王波拿了奖。
从那以后,我对语文就彻底没了兴趣,对张怀民,更是敬而远之。
毕业那天,全班同学都围着他要签名,要合影。我一个人悄悄地从后门溜了,连一句“老师再见”都没说。
二十年了,我以为这个人早就被我扔到记忆的角落里,落满了灰。
没想到,一个同学会,又把他给翻了出来。
我老婆看我半天没动静,走过来,拿过我的手机,直接点了“同意”。
“多大点事儿,还犹豫。去看看呗,二十年没见了,大家肯定都变样了。”
她倒是说得轻松。
我被她拉进了群,里面已经有二三十号人了,头像五花八门,名字也改得千奇百怪。要不是有备注,我一个都认不出来。
群里正聊得火热。
“王波!你小子现在是大老板了吧?”
“听说刘丽嫁到国外去了?真的假的?”
“大家还记得张老师吗?这次同学会,王波说把他老人家也请来!”
看到“张老师”三个字,我的心又沉了一下。
王波,当年的班长,现在好像混得确实不错,是这次同学会的组织者。他在群里发了个红包,然后说:“张老师必须请啊!没有他,哪有我们的今天?我特地去家里拜访过他了,老师身体还行,就是腿脚不太利索了。听说我们要聚会,他高兴坏了。”
下面一堆人附和。
“是啊是啊,张老师当年对我可好了。”
“我那时候家里困难,张老师还偷偷给我塞过饭票呢。”
“他就是嘴上严厉,心里比谁都热。”
我看着这些话,觉得特别刺眼。
好像我们上的不是同一个高中,教我们的不是同一个张怀民。
我老婆凑过来看了一眼,说:“你看,你老师人缘挺好嘛。你是不是当年太调皮,被老师多说了几句,就记恨到现在啊?你这心眼儿,也太小了点。”
我没说话,把手机扔到一边。
心眼儿小吗?
可能吧。
但那种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一次又一次被否定的感觉,那种你掏心掏肺写出来的东西,被人家轻飘飘一句“虚情假意”就打发掉的滋味,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是不会懂的。
那几天,群里的消息一直响个不停。
大家在商量时间,地点,费用。
我一概不参与,设置了消息免打扰。
去,还是不去?
这个问题像个小钩子,一直在我心里挂着。
不去吧,好像显得我真像我老婆说的那样,心眼儿小,放不下。都快四十岁的人了,还跟个孩子似的,记着二十年前的仇。
去吧,我实在不想看见张怀民那张脸。我怕他一开口,又是那种熟悉的,带着审视和批评的语气,会把我瞬间打回那个自卑又敏感的少年时代。
周五下午,王波直接给我打了个电话。
他声音还是跟以前一样,洪亮,带着一股天生的自信。
“李伟,周六晚上七点,老地方‘聚福楼’,你可一定要来啊!全班就差你没表态了。”
我支支吾吾地找借口:“周六……可能要加班。”
王波在那头笑了:“得了吧你,你们那单位我还不知道?周六加个什么班。再说了,张老师也来,他前两天还跟我念叨,问班里同学都怎么样了,特地问到你了。”
“问我?”我心里一惊,脱口而出。
“是啊,”王波的语气很自然,“他说,‘李伟那小子,现在怎么样了?当年脑子挺活的,就是有点拧,不知道现在那股拧劲儿还在不在。’”
我握着电话,半天没说出话来。
脑子活,有点拧。
这是张怀民对我的评价?
我印象里,他从来没夸过我半个字。
挂了电话,我坐在办公椅上,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心里五味杂陈。
或许,我真的该去一次。
不为别的,就为了去看看,二十年过去了,那个让我记恨了这么久的人,到底变成了什么样。也为了去确认一下,是不是我自己的记忆,出了偏差。
周六晚上,我还是去了。
我特地换了件新衬衫,对着镜子照了又照,想让自己看起来精神点,成功点。好像这样,就能在张怀民面前,挣回一点当年的面子。
聚福楼还是那个聚福楼,只是重新装修了,比以前气派了不少。
我走进包间的时候,里面已经坐了大半的人。
二十年的时间,像一把刻刀,在每个人脸上都留下了痕迹。当年清瘦的少年,如今挺着啤酒肚。当年扎着马尾的女孩,眼角也爬上了细纹。
大家互相打量着,笑着,大声地叫着对方的名字,好像要把这二十年的空白都用声音填满。
气氛很热烈,但我却有点融不进去。
我找到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王波看见我,立刻端着酒杯过来。
“李伟,你可算来了!罚酒三杯!”
他还是老样子,自来熟,热情得让人无法拒绝。
我跟他碰了杯,喝了口酒,眼睛却在人群里搜索。
我看到了他。
张怀民就坐在主位上,被一群同学围着。
他比我记忆中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稀稀疏疏的,背也有些驼了,脸上布满了皱纹,像干涸的河床。他穿着一件半旧的灰色夹克,洗得有点发白。
他没戴眼镜,眼睛眯缝着,很仔细地听着身边的同学说话,时不时地点点头,脸上带着笑。
那笑容,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温和,慈祥,甚至……有点茫然。
好像他也在努力地从这些中年人的脸上,寻找着当年那些青涩的影子。
我的心,莫名地被揪了一下。
这就是那个当年声如洪钟,眼神锐利的张老师?
时间,真的能改变一个人这么多吗?
陆陆续续地,人到齐了。
酒菜上来,气氛也越来越高涨。
大家开始轮流给张怀民敬酒。
每个人都说着感谢的话。
“张老师,要不是您当年逼我背古文,我现在连合同都看不明白。”
“张老师,您还记得吗?我高三那年早恋,是您把我俩叫到办公室,没批评我们,还给我们讲道理,说要互相鼓励,考上大学才是正事。我现在都记得。”
“张老师,我敬您一杯,谢谢您当年的教导!”
张怀民端着一杯茶,以茶代酒,笑呵呵地听着,眼睛里有光。
我坐在角落里,默默地吃着菜,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
他们口中的那个张老师,和我记忆里的那个,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为什么他给所有人的记忆都是温暖的,唯独留给我的,是那么冰冷的?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王波忽然站起来,举着杯子,大声说:“大家静一静,静一静!今天我们能聚得这么齐,最该感谢的,除了张老师,还有一个人!”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他。
王波的目光,却穿过人群,落在了我的身上。
“这个人,就是李伟!”
我一下子愣住了。
包间里瞬间安静下来,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我。
我感觉脸上的血一下子就涌了上来,有点发烫。
“王波,你瞎说什么呢?”我有点慌乱。
王波哈哈大笑,走过来,一把搂住我的肩膀。
“我可没瞎说。大家可能不记得了,高二那年,我们学校不是搞了个什么‘爱心捐款’活动,给山区贫困学生捐钱吗?”
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显然大部分人都没什么印象了。
“那次捐款,咱们班捐了全校第一。”王波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得意,“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还是停在我的脸上。
“因为李伟,他一个人,就捐了五百块钱!”
“五百块!”
人群里发出了一阵小小的惊叹声。
九十年代末,五百块钱,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不是个小数目。那是我妈在菜市场起早贪黑,卖一个月青菜才能挣出来的钱。
我当时脑子一热,听了学校广播里那些山区孩子的故事,就把我妈给我存着交学费的钱,偷偷拿出来捐了。
这件事,我谁也没告诉。
我没想到,王波居然还记得。
更没想到,他会在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来。
我有点手足无措,只能干笑着说:“都……都过去那么久了,提这个干嘛。”
“必须提!”王波拍了拍我的背,“当时张老师知道了,在班会上把咱们班好一顿夸,说我们班同学有爱心。但是他没说出你的名字,他说,做好事,不留名,这才是最高尚的。”
王波的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平静了二十年的心湖。
我抬起头,看向主位上的张怀民。
他也正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情绪,好像是欣慰,又好像是……别的什么。
他冲我举了举手里的茶杯,点了点头。
那一瞬间,我心里那块坚硬了二十年的冰,好像裂开了一道小小的缝。
原来,他知道。
他知道那件事是我做的,他没有批评我,还在班会上表扬了我们。
只是,他没有提我的名字。
为什么?
我端起酒杯,遥遥地向他回敬了一下,然后一饮而尽。
酒很辣,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同学会的气氛越来越热烈,大家开始聊起了现在的生活。
谁谁谁买了房,谁谁谁换了车,谁谁谁的孩子上了重点小学。
我坐在那里,话很少。
王波带来的那段小插曲,让我的思绪彻底乱了。
我开始不受控制地回忆过去,试图从那些被我贴上“批评”和“否定”标签的记忆里,找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我想起他让我重写了五遍的作文,虽然当时我觉得是刁难,但后来,我的语文成绩确实从那以后就没掉下过八十分。
我想起他总是在课堂上提问我那些我最容易忘的知识点,虽然让我很没面子,但高考的时候,那几道题,我一道都没错。
我想起他批评我的字像鸡爪子,可从那以后,我真的开始每天坚持练字,现在写得一手还算拿得出手的钢笔字,在单位里,领导还夸过我。
这些细节,以前被我心里的那股怨气给盖住了,现在,它们一点点地浮了上来。
难道……真的是我错了?
我心里乱糟糟的,又喝了好几杯酒。
酒过三巡,张怀民站了起来。
他年纪大了,站得有点晃悠,王波赶紧过去扶住他。
“同学们,我……我说两句。”他声音有点沙哑,但整个包间立刻就安静了下来。
“看到你们,我很高兴。”他环视了一圈,目光在我们每个人脸上都停留了片刻。
“二十年了,你们都长大了,都有了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家庭。我这个当老师的,没什么大本事,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你们。”
“我当年……对你们很严厉。”他顿了下,目光好像不经意地从我脸上一扫而过。
“有时候,可能话说得重了点。我在这里,跟你们说声,对不住了。”
说着,他竟然微微地鞠了一躬。
在场的所有同学,都愣住了。
然后,不知道是谁带的头,大家全都站了起来,拼命地鼓掌。
掌声雷动。
很多人眼圈都红了。
我也站了起来,跟着鼓掌,心里却翻江倒海。
他说,话说得重了点。
他是在说我吗?
他是在为当年那句“虚情假意”,向我道歉吗?
我不知道。
我只觉得,心里那道裂缝,好像又扩大了一些。
同学会快结束的时候,张怀民因为身体原因,要先走一步。
王波扶着他往外走。
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张怀民停下了脚步。
他看着我,忽然开口了。
“李伟,你这肚子,可不像当年跑一千米的样子了啊。”
又是这句话。
和刚见面时说的一模一样。
我心里咯噔一下,刚刚升起的那点暖意,瞬间又凉了半截。
你看,他还是这样。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骨子里,就是个喜欢挑刺,喜欢批评人的人。
我扯了扯嘴角,想挤出一个笑容,但估计比哭还难看。
“是啊,张老师,人到中年,身不由己。”我敷衍地。
他却没走,继续看着我,眼神很认真。
“工作再忙,也要注意身体。你妈……她不容易。”
说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在王波的搀扶下,慢慢地走了出去。
我愣在原地,像被雷劈了一样。
他……他怎么会知道我妈?
不对,他是我班主任,他当然知道。
可是,他那句“她不容易”,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他要特地跟我说这个?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送走了张怀民,王波又回到了包间。
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提议换个地方,去KTV唱歌。
我却一点心情都没有。
张怀民最后那句话,像个谜一样,在我脑子里盘旋。
我拉住正要招呼大家出门的王波。
“王波,你等一下,我问你个事儿。”
“怎么了?”王-波看我脸色不对,有点诧异。
“张老师……他,他以前是不是去过我家?”我问得有点急。
王波想了想,摇了摇头:“没印象啊。怎么了?”
“那你知不知道,他跟我妈……是不是认识?”我又问。
这个问题,我自己都觉得有点荒谬。
我妈一个在菜市场卖菜的,张怀民一个重点中学的老师,他们俩能有什么交集?
王波被我问得一头雾水。
“李伟,你是不是喝多了?张老师怎么可能认识你妈啊。他家访也都是去那些成绩特别好或者特别差的同学家,你这种中不溜秋的,他哪有时间管。”
王波的话,像一盆冷水,把我浇了个透心凉。
是啊。
我真是喝多了,胡思乱想。
他那句话,可能就是随口一说。
我自嘲地笑了笑,松开了王波。
“没事了,你们去玩吧,我今天有点不舒服,先回去了。”
没等王波再说什么,我就走出了包间。
外面的夜风很凉,吹在脸上,让我混乱的脑子清醒了一点。
我没有回家,而是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
脑子里,全是今天晚上发生的事。
同学们的笑脸,张怀民苍老的样子,王波说的话,还有……张怀民最后那句莫名其妙的叮嘱。
“你妈……她不容易。”
为什么?
为什么他要这么说?
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张怀民不是一个会说废话的人。他说的每一句话,一定有他的用意。
一个念头,像闪电一样,划过我的脑海。
我猛地停下脚步,拿出手机,翻出王波的电话,拨了过去。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背景音是震耳欲聋的音乐和鬼哭狼嚎的歌声。
“喂!李伟!怎么了?不是回去了吗?”王波大声地喊着。
“王波!”我也对着手机喊,“你现在,马上,把张老师家的地址发给我!”
“你要他家地址干嘛?”
“你别管了!快发给我!我有急事!”
王波可能被我的语气吓到了,没再多问,说了句“行,我马上找找”,就挂了电话。
几分钟后,一个地址发到了我的手机上。
是一个很老的小区,离这里不远。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那个地址。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只是有一种强烈的直觉,我觉得,我必须去见他一面,必须把心里的这个疑问弄清楚。
不然,我可能会记挂一辈子。
出租车在老旧的小区门口停下。
这里的路灯很暗,楼道里散发着一股潮湿的霉味。
我按照地址,找到了张怀民家。
那是一扇很旧的木门,上面的红漆已经斑驳脱落。
我站在门口,抬起手,却迟迟没有敲下去。
我该怎么说?
问他为什么说那句话?
他会不会觉得我莫名其妙?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门,忽然从里面打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应该是张怀民的爱人。她看到我,愣了一下。
“您……找谁?”
“我……我找张老师。”我有点紧张,声音都变了调,“我是他以前的学生,李伟。”
“李伟?”老太太念叨着这个名字,好像有点耳熟。
“哦,我想起来了,老张今天去参加同学会,还提起你了。”她笑了起来,很和善,“快进来吧,他刚喝了点酒,躺下歇着呢。”
我跟着她走进屋子。
屋子不大,两室一厅,陈设很简单,但收拾得很干净。
客厅的沙发上,张怀民正靠在那里,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
“老张,老张。”师母走过去,轻轻推了推他,“你学生来看你了。”
张怀民缓缓地睁开眼睛,看到我,他似乎一点也不意外。
他坐直了身体,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坐吧。”
师母给我们倒了杯水,就借口去厨房忙活,把空间留给了我们。
客厅里很安静,只听得见墙上老式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
我端着水杯,手心有点冒汗,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还是他先说话了。
“怎么找来了?”他声音很平静。
“我……”我深吸了一口气,决定不再拐弯抹角,“张老师,我想问您一件事。”
他点了点头,示意我说下去。
“今天在同学会上,您最后跟我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看着我,没有马上。
他的眼神,不像在学校时那么锐利了,变得有些浑浊,但依然很深,好像能看透人心。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开口。
“你妈妈,是个很了不起的女人。”
我心里一震。
他果然,是知道些什么的。
“高二那年,你妈妈来学校找过我。”
他的声音,把我带回了那个遥远的下午。
“她没让我告诉你。她说,怕你知道了,心里有负担。”
我的呼吸,一下子就停住了。
“那天她来的时候,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工装,上面还沾着泥点子。她手里提着一袋子苹果,红彤彤的,一个一个擦得很亮。她说,是她自己摊子上最好的苹果,让我尝尝。”
张怀民的语气很慢,像是在讲述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
“她一开口,就跟我道歉。她说,‘张老师,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我家李伟这孩子,都怪我,没教育好。’”
“她说,她一个人带我,每天天不亮就要去菜市场,天黑了才回家,根本没时间管我。她说,她知道我脑子不笨,就是心野,爱玩,怕我学坏了。”
“她说着说着,就哭了。”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在我这个当老师的面前,哭得像个孩子。她求我,她说,‘张老师,我求求您,您帮我管管他。您就拿他当您自己孩子一样,该骂就骂,该罚就罚。只要能让他走上正道,您怎么对他都行。’”
“她说,她这辈子没什么盼头了,唯一的指望,就是我。她希望我能考上大学,离开那个嘈杂的菜市场,过上好日子。”
张怀民说到这里,停了下来,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
我的眼泪,却已经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
我从来不知道。
我从来不知道,我那个坚强得像座山一样的妈妈,曾经为了我,那样卑微地去求过一个外人。
我只记得,她每天都乐呵呵的,好像从来没有烦心事。
我只记得,她总跟我说,“儿子,你想干啥就干啥,妈支持你。”
我从来不知道,在她开朗的笑容背后,藏着这么深的担忧和这么沉重的爱。
“所以……”我哽咽着,几乎说不出话来,“所以您后来对我那么严厉,都是因为我妈?”
张怀民点了点头。
“你妈妈把她唯一的希望,交到了我手上。我不能辜负她。”
“你那篇写你妈妈的作文,我看了。写得很好,很真诚。我这辈子,看过无数学生作文,那篇,是我印象最深的之一。”
我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那……那您为什么说我虚情假意?为什么不让我去参加比赛?”
他叹了口气。
“因为你那时候,太顺了。你有点小才华,人也聪明,周围的老师同学都喜欢你。我怕你骄傲,怕你把心思都用在写这些东西上,耽误了真正重要的功课。”
“年轻人,需要敲打。尤其是像你这样,有点小聪明的年轻人,更需要有人在你沾沾自喜的时候,给你泼一盆冷水,让你清醒清醒。”
“至于比赛,王波的那篇读后感,四平八稳,更适合那种场合。而你的文章,是你心里的东西,我不希望它被拿出去,被那些评委用条条框框来打分,来评判。那是对你和你母亲那份感情的亵渎。”
我的脑子,嗡嗡作响。
原来是这样。
原来,我记恨了二十年的那句“虚情假意”,背后藏着这样的用心。
原来,我耿耿于怀了二十年的那次“不公”,竟然是对我的一种保护。
我一直以为,他是我的敌人,是那个不断打击我自信心的人。
我却从来没有想过,他和我妈妈,竟然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
他们一个在明,一个在暗,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守护着同一个有点“拧”的少年。
我妈用她宽厚的爱,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港湾。
而他,选择扮演那个恶人,用最严厉的方式,逼着我这艘小船,驶向正确的航道。
他承受了我所有的不解,误会,甚至怨恨,却从来没有为自己辩解过一个字。
只因为,他对一个母亲的承诺。
“那次捐款,五百块钱,是你拿了学费吧?”张怀民忽然又问。
我点了点头,有点不好意思。
“我当时就猜到了。我让你妈妈来学校一趟,想把钱还给她。可她说什么都不要。她说,钱花了可以再挣,孩子的善良,比什么都重要。她还让我千万别批评你,说你做得对。”
“从那天起,我就知道,你这孩子,本质不坏。就是一棵小树苗,长得有点歪,需要有人给扶一把,捆一捆,疼是疼了点,但总能长直了。”
我再也忍不住了,趴在桌子上,像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
这二十年来,我心里积压的所有委屈,所有不甘,所有怨恨,都在这一刻,随着眼泪,倾泻而出。
我哭的,不仅仅是这二十年的误解。
我哭的,是我的母亲。那个我一直以为我很了解,却其实从来没有真正懂过的母亲。
我哭的,是眼前的这个老人。这个我记恨了半辈子,却原来是除了我母亲之外,最希望我过得好的人。
张怀民没有劝我。
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等我哭完。
师母端了一盘切好的水果出来,放到桌上,又悄悄地退了回去。
我哭了很久,直到把心里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干净,才慢慢地抬起头来。
眼睛又红又肿,狼狈不堪。
“张老师,”我站起身,走到他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对不起。”
这一声“对不起”,迟了整整二十年。
他摆了摆手,示意我坐下。
“没什么对不起的。我当老师的,职责就是这个。只要你们一个个,最后都能好好地,我就心满意足了。”
“你现在,过得怎么样?”他问,语气就像一个普通的长辈,在关心自己的晚辈。
我把我的工作,我的家庭,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他听得很认真,时不时地点点头。
“不错,不错。”他欣慰地笑了,“踏踏实实的,比什么都强。你妈妈知道了,肯定很高兴。”
提到妈妈,我的心又是一阵酸楚。
她在我大学毕业那年就去世了,没能看到我现在的生活。
如果她知道,我今天终于解开了这个心结,她也一定会很高兴吧。
那天晚上,我和张老师聊了很久。
聊我的工作,聊他的退休生活,聊当年的那些同学。
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了那种老师和学生的隔阂。
更像是两个久别重逢的朋友。
从他家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
我走在清冷的街道上,心里却前所未有的平静和温暖。
那块压在我心头二十年的巨石,终于被搬开了。
我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
回家的路上,我给我老婆打了个电话。
“老婆,我错了。”
电话那头的她,显然被我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搞蒙了。
“你说什么呢?大半夜的。”
“我说,我错了。我不该记恨张老师,是我心眼儿太小,是我误会他了。”
我把今天晚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她。
她在那头,沉默了很久。
最后,她轻轻地说:“回来吧,我给你留了灯。”
挂了电话,我抬头看天。
夜空里,有几颗稀疏的星星。
我想起了我的妈妈。
我想,她现在,一定也在天上,微笑着看着我吧。
第二天,我买了一些上好的茶叶和一些适合老人吃的点心,又一次去了张老师家。
这一次,我的心情完全不同了。
没有了紧张和忐忑,只有坦然和尊敬。
师母开的门,看到我,笑得很开心。
“快进来,老张正念叨你呢。”
我陪着张老师下了一盘棋。他的棋艺很好,杀得我片甲不留。
但他没有像当年改我作文一样,批评我下得臭。
他只是在下完棋后,慢慢地复盘,告诉我,哪一步走错了,哪一步,其实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洒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也洒在纵横交错的棋盘上。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人生,不也像这一盘棋吗?
年轻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是棋手,可以掌控一切。
殊不知,在每一个关键的路口,都有人在我们身后,默默地为我们指点,为我们筹谋。
他们或许言语严厉,或许方式笨拙,但他们的目的,都只有一个。
那就是希望我们,能走得更稳,更远。
从那以后,我每隔一两个星期,就会去看望张老师。
有时候,是陪他聊聊天,下下棋。
有时候,是帮他修修家里接触不良的开关,或者扛一袋米上楼。
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像亲人。
我也把这些事,告诉了王波他们。
王波听完,沉默了很久,最后在电话那头,长长地叹了口气。
“李伟,真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张老师他……真是不容易。”
后来,我们班组织了一个小组,轮流去看望张老师。
大家不再只是在同学会上,才想起这位曾经的恩师。
我们把他,真正地当成了自己的长辈。
又是一年春天。
我带着妻子和孩子,去给我妈妈扫墓。
在墓碑前,我把我和张老师的故事,仔仔细细地讲给了她听。
我说:“妈,您放心吧。我现在过得很好。张老师身体也很好。”
“您和张老师,都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贵人。一个给了我生命,一个给了我方向。”
“以前我不懂,现在,我全明白了。”
一阵风吹过,墓碑旁的松树,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在回应我。
我抬起头,看着湛蓝的天空。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些爱,是沉默的。
有些守护,是严厉的。
它们可能不会让你当时感到温暖,甚至会让你觉得刺痛。
但只要你走得够远,回头再看时,你就会发现,正是那些当初让你最难受的“批评”和“敲打”,才把你塑造成了今天这个,还算不错的自己。
而那些愿意对你“恶语相向”的人,才是真正把你的未来,放在心上的人。
文档上传者
热门标签
相关文档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