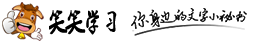欢迎来到98聘
苦的味道作文如何写我教你。(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12-06 02:17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苦的味道”的作文,可以是一次深刻的个人体验或感悟。以下是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以及一个写作思路示例:
"作文注意事项:"
1. "明确“苦”的内涵:" "字面意义:" 可以写味觉上的苦,比如吃苦瓜、喝中药等。 "引申意义:" 这是更常见的写法。可以指生活中的困难、挫折、艰辛、牺牲、劳累、失败的滋味,或者某种需要忍耐、克制、付出代价的经历。 "建议:" 尽量选择后者(引申意义),因为它更能体现深度和思考,更容易写出真情实感。
2. "选择合适的切入点:" 是一次具体的经历?比如考试失利后的苦涩、努力奋斗过程中的艰辛、为了某个目标做出的牺牲等。 是一种普遍的情感体验?比如成长的烦恼、人生的必经之路、对某些现象的反思等。 选择一个你最有感触、最有话可说的点作为中心。
3. "描写要具体生动:" "感官描写:" 即使写引申意义的苦,也可以适当运用其他感官(视觉、听觉、触觉、嗅觉)来烘托气氛。比如,失败的苦可能伴随着“阴沉的天空”、“压抑的寂静”、“紧握的拳头”等。 "心理描写:" 这是关键
那年在看守所,我睡在死刑犯旁边,他收到判决书后三天没有说话
铁门在我身后“哐当”一声锁死,那声音沉闷得像一块巨石,直接砸进了我的胸腔里。
我叫李卫民,四十二岁,一个跟木头打了半辈子交道的木匠。
进来之前,我有个小小的家具作坊,不大,但活儿精细,十里八乡都认我这块牌子。
事情出在一批给酒店定制的活儿上,对方收了货,尾款迟迟不结,我去理论,话赶话动了手。对方人多,我抄起一根木方自卫,没成想把人脑袋打开了瓢。
故意伤害,进来了。
看守所里的空气,混杂着消毒水、汗味和一种说不清的霉味,吸进肺里,凉飕飕的。
我被带进307监室,十几平米的地方,靠墙两排大通铺,已经躺了二十多个人,像秋风扫过的落叶,姿态各异地堆着。
管教指了指最里面靠墙的一个空位,“睡那儿。”
我点点头,抱着发下来的被褥,小心翼翼地从人缝里挤过去。
我的铺位紧挨着一个男人,他侧身躺着,背对着外面,只留给我一个宽厚而沉默的背影。他身上那件蓝色的囚服洗得有些发白,但叠放的衣物却整整齐齐,像用尺子量过一样。
“新来的?”旁边一个瘦猴样的男人小声问我。
我“嗯”了一声。
“犯的啥事?”
“经济纠纷,打架了。”我含糊地。
瘦猴撇撇嘴,朝我旁边的铺位努了努嘴,声音压得更低了:“离他远点,马哥,‘背一命’的。”
“背一命”是这里的黑话,意思是他身上背着一条人命。
我的心猛地一沉,下意识地往旁边挪了挪,身体都僵硬了。
夜里,监室里鼾声、梦话声此起彼伏,我却毫无睡意。
身旁的“马哥”一动不动,呼吸均匀而绵长,仿佛睡得无比安稳。可我总觉得,那片寂静里,藏着一头随时会醒来的猛兽。
第二天,我才知道了他叫老马,大名马向东。
监室里的人对他都有一种敬而远之的尊重,没人敢去招惹他。他吃饭、洗漱、放风,都安安静静的,话很少,眼神总是飘向窗外那片被切割得四四方方的天空。
他不像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倒像个心事重重的老农,脸上刻满了风霜,眼神里有种已经认命的平静。
这样的日子过了大概半个月,我的律师来看过我一次,情况不太乐观,对方咬死了不松口,可能要判实刑。
我老婆也来过,隔着厚厚的玻璃,她哭得眼睛通红,一个劲儿地说:“卫民,家里你别担心,作坊我看着,女儿我照顾着,你……你在里面好好的。”
我看着她憔悴的脸,心疼得像被刀子剜。
我一个大男人,本该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却成了全家最大的拖累。
那天下午,管教喊了老马的名字。
“马向东,判决下来了。”
整个监室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老马身上。
他慢慢地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衣服,跟着管教走了出去。
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捏着一张纸,那张纸又薄又轻,在他手里却仿佛有千斤重。
他没有看任何人,径直走回自己的铺位,把那张纸整整齐齐地叠好,塞进了枕头底下。
然后,他躺下,用被子蒙住了头。
从那天起,老马就没再说一句话。
吃饭的时候,别人把饭盆递给他,他接过来,默默地吃完。
放风的时候,他走到墙角,蹲下,一蹲就是半个小时。
有人想跟他搭话,他只是抬眼看一眼,那眼神空洞得吓人,像两口深不见底的枯井。
第一天,他没说话。
第二天,他还是没说话。
到了第三天,整个监室的气氛都变得压抑起来。大家心里都清楚,那张纸上写的是什么。
死刑,立即执行。
这三个字,像三座大山,不仅压在老马心上,也压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上。
我睡在他旁边,感受得最真切。
夜里,我能听到他极力压抑的呼吸声,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在黑暗中独自舔舐伤口,偶尔,被子下会传来极其轻微的抽动。
我不敢动,也不敢出声,只能装作睡着了,心里却翻江倒海。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是后悔?是恐惧?还是不甘?
一个即将走向生命尽头的人,在他最后的沉默里,究竟藏着怎样一个世界?
我自己的那点事,跟他的比起来,忽然变得那么微不足道。
我还在想着出去以后怎么把作坊撑起来,怎么弥补老婆孩子。
而他,已经没有以后了。
第1章 一碗面条
第四天早上,监室里所有人都被一阵压抑的哭声惊醒了。
那哭声不是嚎啕大哭,而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像拉扯一根生了锈的铁丝,又涩又哑。
是老马。
他依然用被子蒙着头,整个身体都在剧烈地颤抖。
监室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坐了起来,默默地看着那个起伏的被团。
没人去劝,也没人敢去劝。
有些悲伤,是任何语言都无法触及的。
哭了大概十几分钟,声音渐渐小了下去,最后只剩下粗重的喘息。
早饭是玉米糊糊和馒头。
我把自己的那份递给他,他没接。
他掀开被子,坐了起来,眼睛肿得像两个核桃,布满了血丝。
他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清:“兄弟,谢了,吃不下。”
这是他三天来说的第一句话。
我把饭盆放在他铺上,“多少吃点,人是铁,饭是钢。”
话说出口,我自己都觉得苍白无力。
他没再理我,只是呆呆地坐着,目光没有焦点。
中午,管教破天荒地给老马送来一份“加餐”。
一份白菜肉末浇头的面条,还有一个荷包蛋。
这是“上路饭”之前的优待。
热气腾腾的面条,香味在监室里弥漫开来,勾起了所有人的馋虫。
老马看着那碗面,看了很久。
然后,他抬起头,对管教说:“管教,我能……跟他换换吗?”
他指了指我。
所有人都愣住了。
管教也有些意外,但还是点了点头,“随你。”
老马把那碗面推到我面前,“兄弟,你吃吧。”
我看着他,又看看那碗面,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马哥,这……”
“我闺女,”他低着头,声音很轻,“最爱吃我做的打卤面,每次都卧个荷包蛋。”
他的眼圈又红了。
“她说,爸做的面,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面。”
我端着那碗面,感觉它有千斤重。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
这碗面,他吃不下去。对他来说,这不是一碗面,而是他再也回不去的过往,是他心底最柔软也最痛苦的念想。
“你吃吧,”他又说了一遍,“看你吃饭,香。像我闺女。”
我的眼眶一热,差点掉下泪来。
我埋下头,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我吃得很用力,很认真,仿佛在完成一个神圣的仪式。
面条很香,但我吃不出味道,嘴里心里,都是苦的。
监室里很安静,只有我吸溜面条的声音。
所有人都看着我,也看着老马。
老马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奇怪的满足和悲伤。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吃的不是面,而是一个父亲对女儿全部的爱和思念。
第21章 木头的纹理
吃完那碗面,我和老马之间的那层冰,仿佛悄无声息地化开了。
他开始断断续续地跟我说话。
话不多,通常是他问,我答。
“兄弟,你真是个木匠?”
“是,马哥。干了二十多年了。”
“木匠好啊,”他长长地叹了口气,“跟木头打交道,木头不会骗人。”
他的话,像一根针,扎在我心上。
我就是被“人”骗了,才进来的。那个合作方,当初称兄道弟,一口一个“李大师”,说我的手艺是艺术品。结果呢,货到手就翻脸不认人。
“马哥,您以前是做什么的?”我小心翼翼地问。
“我?”他自嘲地笑了笑,“开大车的,全国各地跑。”
原来是个长途司机。
我想象着他开着一辆重型卡车,在高速公路上日夜兼程的样子。那也是个辛苦活,挣的都是血汗钱。
“开大车,也能长见识。”我说。
“见识?”他摇摇头,“见的都是黑心的老板,还有各地不一样的收费站。唯一的念想,就是早点跑完这趟,回家抱抱闺女。”
他又提到了他闺女。
每次提到“闺女”这两个字,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就会浮现出一丝极其温柔的光。
那种光,让他的轮廓都变得柔和起来。
“我闺女叫笑笑,一笑起来,眼睛弯得跟月牙儿似的。”
他靠在墙上,眼神飘向那扇小小的铁窗,仿佛能穿透高墙,看到那个叫笑笑的女孩。
“她学习好,从小到大都是班里前三名。画画也好,墙上贴满了她的奖状。”
“她说,爸,你别开大车了,太辛苦了,等我将来考上大学,挣大钱养你。”
老马说着说着,就笑了,那笑容里有骄傲,有幸福,但很快,又被无尽的悲哀淹没。
“都怪我……都怪我没本事,没保护好她……”
他的声音哽咽了,后面的话,被他生生咽了回去。
我没敢再问下去。
我知道,那后面,一定是一个血淋淋的故事。
晚上,熄灯号吹响,监室里陷入黑暗。
我躺在铺上,听着身边老马沉重的呼吸声。
“兄弟,”他忽然开口,“睡不着?”
“嗯,有点。”
“想家了?”
“想。想我老婆,想我闺女。”
“你闺女多大了?”
“十五,上初三了。”
“跟我家笑笑……出事那年一样大。”
黑暗中,我能感觉到他的身体僵硬了一下。
沉默了很久,他才再次开口,声音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又冷又硬。
“兄弟,你说,这世上……真有报应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
我说:“我爸以前常说,人在做,天在看。”
“天在看?”老马冷笑一声,“天要是真在看,怎么会让好人没好报,让坏人活千年?”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怨恨和不甘。
“我闺女,那么好的一个孩子,她做错了什么?她才十五岁啊!人生才刚刚开始!”
我知道,他要开始讲他的故事了。
我翻了个身,面对着他,在黑暗中轻声说:“马哥,你要是想说,我就听着。”
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那口气里,带着一股铁锈的味道。
“那天,我从外地拉货回来,比预计早了一天,想给老婆孩子一个惊喜。”
“到家都半夜了,我没吵醒她们,自己开了门。”
“结果,我看到……”
他的声音开始发抖。
“我看到我们家笑笑,浑身是血地躺在地上……”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无法呼吸。
“她身上……全是伤……那帮……三个人……”
老马说不下去了,黑暗中传来他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的声音。
“我老婆被他们绑在椅子上,嘴也堵着,只能呜呜地哭。”
“我当时脑子‘嗡’的一下,什么都不知道了。我从厨房抄起那把剁骨头的刀……”
“等我清醒过来,那三个,都倒在地上了。”
“一个……没气了。”
第22章 木头的纹理
监室里死一般的寂静,连呼吸声都听不见了。
我的后背冒出一层冷汗,整个人都僵住了。
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是“背一命”。
“后来呢?”我艰难地问。
“后来,我报了警。我老婆疯了,彻底疯了,现在还在精神病院里,谁也不认识。”
老马的声音平静得可怕,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笑笑在医院抢救了七天,还是没救回来。”
“临走前,她拉着我的手,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爸,我疼……’”
黑暗中,我仿佛看到了那个叫笑笑的女孩,看到了她临终前那双充满痛苦和不舍的眼睛。
一个父亲,亲耳听到女儿说出这样的话,该是怎样的心如刀割。
“那两个活下来的,一个判了无期,一个判了十五年。”
“而我,因为防卫过当,致人死亡,一审,死刑。”
老马的声音里没有一丝波澜,仿佛在陈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事实。
“马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干巴巴地安慰,“你那是为了保护家人……”
“没用的。”他打断我,“法律就是法律。我杀了人,就得偿命。我认。”
“我不后悔。”他一字一顿地说,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我的心里。
“我只是……只是不甘心。”
“凭什么我闺女要遭那样的罪?凭什么我老婆要疯?凭什么我们好好的一家人,就这么散了?”
“我就是想不通这个理。”
他反复地问着“凭什么”,像一个迷路的孩子,在无尽的黑暗中寻找一个答案。
可这个世界,哪有那么多“凭什么”。
很多时候,厄运的降临,就是这么不讲道理。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
他把他和女儿笑笑的过往,像放电影一样,一点一点地讲给我听。
讲她第一次喊“爸爸”,讲她第一次走路摔倒了自己爬起来,讲她把不及格的卷子藏在身后,讲她偷偷攒下零花钱给他买生日礼物。
那些琐碎的,温暖的,闪着光的记忆,是他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而现在,这些财富,都变成了最锋利的刀子,一刀一刀地凌迟着他的心。
“兄弟,”快天亮的时候,他忽然问我,“你会做小木马吗?”
“会啊。”我点头,“我闺女小时候,我就给她做过一个,她喜欢得不得了,天天骑着。”
“那……你会做小人儿吗?就是那种,能活动的,关节都能动的小木人儿。”
“会,那个叫‘鲁班锁’的一种,也叫‘关节人’,榫卯结构,有点复杂,但能做。”我来了精神,谈到我的手艺,我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我跟你说马哥,这木头啊,是有灵性的。你得顺着它的纹理来,你敬它一尺,它还你一丈。做出来的东西,才结实,才有魂。”
我跟他讲起了不同木材的特性,讲起了榫卯的精妙,讲起了刨花散发出的清香。
黑暗中,老马一直安静地听着。
“好,真好……”他喃喃地说,“有手艺的人,心里是踏实的。”
“等我出去了,”我拍着胸脯说,“马哥,我给你闺女做一个最好看的关节小人儿,穿着公主裙的那种。”
话说出口,我就后悔了。
我提到了他的伤心事。
监室里又是一阵沉默。
过了许久,他才低声说:“好……那我就……先替笑笑谢谢你了。”
“不过,”他顿了顿,“不用做公主裙了。”
“就给她做一身……她平时穿的校服吧。”
第31章 一线天光
自从那天晚上之后,老马像是变了一个人。
他不再是那个沉默寡言、与世隔绝的“马哥”了。
他会主动跟人说话,虽然话依然不多。
放风的时候,他不再一个人蹲在墙角,而是会跟着我们一起,在小小的院子里一圈一圈地走。
阳光从高墙的缝隙里挤进来,在地上投下一片狭长的光斑。
我们都管那叫“一线天”。
所有人都喜欢踩着那片光走路,仿佛那样就能沾染上一点自由的气息。
老马也喜欢。
他会眯着眼睛,仰头看着那片天空,脸上露出一种近乎贪婪的神情。
“真好啊。”他不止一次地感叹。
我知道,他说的不是阳光,而是阳光所代表的,外面那个他再也回不去的世界。
他开始关心我的案子。
“兄弟,你那事儿,有谱了吗?”
我摇摇头,苦笑:“律师说,能争取个缓刑,就是最好的结果了。对方不肯和解,一口咬定我故意伤人。”
“钱的事?”
“嗯,尾款三十万,他想赖掉。我辛辛苦苦带着徒弟们干了三个月,一分钱拿不到,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我才急了。”
“你那手艺,值这个价。”老马很肯定地说。
“值,但人家不给,有什么办法。”我叹了口气。
“卫民,”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记住,什么时候,都别丢了手艺人的本分。”
“我知道,马哥。”
“我说的本分,不光是活儿要干得漂亮。”他看着我,眼神很严肃,“还有良心。”
“木头不会说话,但你做的东西会。你用的是好料还是次料,是卯榫还是钉子,用的人心里都有一杆秤。”
“你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口碑,就是这么一点一点攒起来的,也是这么一点一点败掉的。”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这些道理,我父亲也跟我说过。
我爸也是个老木匠,他常说,咱们手艺人,手上沾的是木屑,心里装的是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老马的话,让我想起了我爸。
他们都是那种最朴素的中国人,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相信善恶有报,相信做人要对得起良心。
可现实,却往往给他们最沉重的打击。
“马哥,你放心,”我看着他,“我李卫民,这辈子都不会做昧良心的活儿。”
他笑了,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信你。”
那几天,我们聊了很多。
聊他的车,聊我的木头,聊天南海北的风土人情,聊各自的家庭。
我们刻意地回避着那个沉重的话题,但我们心里都清楚,时间不多了。
最高院的死刑复核,随时都可能下来。
那就像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落下。
监室里的人,对老马的态度也变了。
从最初的畏惧,变成了同情,甚至有了一丝敬意。
大家会主动把饭菜里仅有的一点肉末拨给他,会把干净的衣服让给他先穿。
这是一个将死之人,能得到的,最后的体面。
第32章 一线天光
有一次,放风的时候,监室里那个外号“瘦猴”的年轻人,因为抢占篮球场,跟别的监室的人起了冲突。
对方人多势众,眼看就要动手。
老马走了过去。
他什么都没说,就那么静静地站在瘦猴身边,看着对方那几个人。
他的眼神很平静,但那平静里,有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力量。
对方那几个人对视了一眼,骂骂咧咧地走了。
瘦猴一脸感激地看着老马,“谢谢马哥。”
老马只是淡淡地说:“都是一个屋的,别让人欺负了。”
从那以后,瘦猴对老马简直是言听计从。
晚上,我跟老马说:“马哥,你真有威慑力。”
老马自嘲地笑了笑:“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他们当然怕。”
“不过,”他话锋一转,“卫民,你跟他们不一样。”
“你是个有手艺的人,有家有老婆孩子,有念想。你跟我们这些人,不是一条道上的。”
“你得出去。”他看着我,一字一顿地说。
“出去了,好好过日子。别再犯浑,别再动手。没什么坎是过不去的。”
“为了老婆孩子,也得忍。”
我听着他的话,心里五味杂陈。
一个即将赴死的人,在劝一个还有希望的人,要好好活着。
这世上,还有比这更荒诞,也更沉重的事情吗?
“马哥,”我低声说,“等我出去了,我去看看嫂子,还有……笑笑。”
老马的身体震了一下。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
“不用了。”他声音沙哑地说。
“你嫂子,就让她安安静静地待着吧,别去打扰她。忘了这一切,对她来说,是最好的结局。”
“至于笑笑……”
他顿了顿,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你就……把我跟你说的那些故事,记在心里就行了。”
“就当,这世上,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叫笑笑的姑娘,她爱笑,爱画画,也爱她那个不争气的爹。”
“别让她……被人忘了。”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顺着脸颊滑落,滴在冰冷的枕头上。
我重重地点头,“嗯,我记着,一辈子都记着。”
第41章 最后的清晨
那一天,终究还是来了。
是一个很普通的清晨,天刚蒙蒙亮。
监室的铁门被“哗啦”一声打开,走廊里的灯光刺得人睁不开眼。
管教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张名单。
他的表情很严肃,甚至有些凝重。
“马向东。”
他念出了这个名字。
监室里所有醒着的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老马从铺上坐了起来。
他异常的平静,仿佛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刻。
他没有看管教,而是转过头,看着我。
“兄弟,”他笑了笑,“天亮了。”
我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又干又涩。
老马开始不紧不慢地穿衣服。
他把自己那身洗得发白的囚服穿得整整齐齐,每一个扣子都扣得一丝不苟。
然后,他开始叠被子。
他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像一块豆腐块,放在床头。
这是部队里养成的习惯,他跟我说过。
做完这一切,他站起身,环视了一圈这个他待了近一年的地方。
监室里的人都坐了起来,默默地看着他。
没有一个人说话。
瘦猴的眼睛红了,死死地咬着嘴唇。
老马走到监室中间,对着所有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各位兄弟,我马向东,先走一步了。”
“这些日子,承蒙大家照顾。”
“往后,都好好的。”
他的声音很平稳,听不出一点波澜。
然后,他转身,朝门口走去。
他走得很稳,一步一步,像是在丈量着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程。
在经过我身边的时候,他停了下来。
他伸出手,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卫民,记住我跟你说的话。”
“好好活。”
我终于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我用力地点头,哽咽着说:“马哥,你……你放心。”
“还有……”他凑到我耳边,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别忘了,那个穿着校服的小木人儿。”
我泣不成声,只能拼命点头。
他笑了,那是我见过的,他最轻松的一个笑容。
仿佛卸下了一生所有的重担。
他转过身,大步地走出了监室的门。
铁门在他身后,缓缓关上。
这一次,那“哐当”声,没有砸在我胸口,而是像一把重锤,砸碎了黎明前所有的寂静。
第42章 最后的清晨
老马走后,监室里很长一段时间都笼罩在一种压抑的沉默里。
大家都不说话,各自做着自己的事,但所有人都心不在焉。
早饭送来了,还是玉米糊糊和馒头。
我看着老马空出来的那个铺位,还有那床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一点胃口都没有。
瘦猴端着饭盆,蹲在墙角,一边吃,一边无声地掉眼泪。
上午,管教把我叫了出去。
我以为是我的案子有什么进展,心里还有些忐忑。
管教把我带到一间没人的办公室,递给我一支烟。
“抽吧。”
我有些受宠若惊,接了过来。
管教自己也点上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的烟雾,模糊了他那张平时总是板着的脸。
“马向东,走了。”他说。
我点点头,“我知道。”
“他给你留了点东西。”
管教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信封很旧,上面没有写字。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银行卡,还有一张小纸条。
纸条上,是老马那歪歪扭扭的字迹:
“卫民兄弟,这是我这些年开车攒下的一点钱,密码是笑笑的生日,950816。”
“不多,五万块。你出去后,拿着应急。作坊要重新开张,用钱的地方多。”
“别推辞,这是当哥的,最后能为你做的一点事了。”
“还有,如果……如果方便的话,每年清明,帮我去笑笑的坟上,烧个纸,告诉她,她爹没给她丢人。”
“地址在……”
下面是一个墓地的地址。
我的手开始发抖,那张薄薄的纸条,重得我几乎拿不住。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滴一滴地砸在纸条上,洇开了一片水渍。
“他……他是好人。”管教在一旁叹了口气,“可惜了。”
“他家里,就真的一个人都没有了吗?”我抬起头,红着眼睛问。
管教摇摇头,“他老婆还在医院,神志不清。父母早就没了。他是家里的独子。”
“他走之前,吃了早饭。一碗面条,一个荷包蛋。跟那天给你吃的一样。”
“他吃得很慢,吃完,跟我们说了声‘谢谢’。”
“他说,这辈子,没求过人。最后,想求我们一件事。”
“他说,他有个兄弟叫李卫民,是个好木匠,为人实在,就是脾气冲了点。希望我们能多照顾照顾。”
“他还说,你那案子,他是证人。他亲耳听见你跟那个老板理论,是你先被打了,才还的手。”
管教看着我,眼神复杂。
“他已经把这份证词,按了手印,交上去了。”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没想到,老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为我着想。
他甚至,为我做了伪证。
我根本没跟他说过我被打的细节,他只是凭着对我的信任,就为我赌上了他最后的名誉。
我拿着那张银行卡和纸条,蹲在地上,嚎啕大哭。
像个孩子一样,哭得撕心裂肺。
我哭的,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的逝去。
我哭的,是一个好人,在命运的不公面前,那最后的坚守和善良。
第5章 尘埃落定
老马的证词,起了关键作用。
加上我律师找到的一些其他证据,证明了对方确实存在严重的合同欺诈行为。
我的案子,最终被定性为“因民间纠纷引起的防卫过当”,加上对方伤情鉴定只是轻伤,而且我已经取得了对方的谅解——当然,是用钱换来的谅解。
我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宣判那天,我站在法庭上,听到“缓刑”两个字的时候,腿一软,差点没站住。
这意味着,我不用再回那个地方了。
我自由了。
走出法院大门的那一刻,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
我老婆和女儿在外面等着我。
女儿扑进我怀里,放声大哭。
我老婆也抱着我们父女俩,眼泪止不住地流。
我抚摸着女儿的头发,看着妻子憔悴的脸,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回家。
回家的路上,我一句话都没说,只是贪婪地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街景。
那些熟悉的街道,熟悉的人群,熟悉的生活气息,在失去过之后,才显得如此珍贵。
回到家,推开门,一股熟悉的,混杂着饭菜香和生活气息的味道扑面而来。
我那小小的家具作坊,就在家后面。
我老婆在我进去的这段时间,把它打理得井井有条。
虽然没有接新活,但工具都擦得锃亮,木料也码放得整整齐齐。
我走到一块刨了一半的红木板前,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上面细腻的纹理。
那熟悉的触感,让我瞬间热泪盈眶。
我回来了。
我李卫民,又可以拿起我的刨子,我的凿子,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木匠了。
晚上,老婆做了一大桌子菜。
女儿一个劲儿地给我夹菜,小嘴说个不停,讲学校里的趣事,讲她考试又进步了。
老婆坐在旁边,只是微笑着看着我,眼神里全是失而复得的庆幸。
吃完饭,我把老马留给我的那张银行卡,交给了老婆。
我把老马的故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
老婆听完,沉默了很久,眼睛红了。
“这钱,我们不能动。”她说,“这是……一条命换来的情义。”
我点点头,“我知道。”
“卫民,”她握住我的手,“咱们把作坊重新开起来。活儿可以少接点,钱可以少挣点,但一定要做得地道,不能昧良心。”
“不能辜负……马哥对你的这份情。”
我用力地回握住她的手,“我懂。”
第6章 一座新坟
缓刑期间,我不能离开本市。
但清明节那天,我还是跟社区申请,去了老马给我的那个地址。
那是一个离市区很远的公墓,建在半山腰上。
我提着香烛纸钱,还有一瓶好酒,按照地址,找到了笑笑的墓。
墓碑很新,上面嵌着一张女孩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的女孩,梳着马尾辫,穿着校服,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月牙儿。
跟老马描述的一模一样。
墓碑上,刻着她的名字:马笑笑。
旁边,还有一个空出来的位置。
我心里一酸,知道那是老马给自己留的。
我在墓前,把酒倒了三杯。
一杯,敬这个叫笑笑的,命运多舛的姑娘。
一杯,敬那个为女报仇,至死不悔的父亲。
一杯,敬他们父女俩,在那另一个世界,能够重逢。
我点燃纸钱,看着火光跳跃,烟雾袅袅升起。
“笑笑,”我对着墓碑轻声说,“你爸托我来看看你。”
“他说,他没给你丢人。”
“他还说,他很想你。”
“你爸……是个英雄。”
风吹过松林,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在回应我。
我在墓前坐了很久,把我跟老马在监室里的点点滴滴,都讲给了这个素未谋面的女孩听。
讲那碗面条,讲那“一线天”,讲木头的纹理。
最后,我说:“笑笑,你爸还让我给你做个礼物。一个穿着校服的小木人儿。”
“你放心,叔叔是最好的木匠。等做好了,我给你送来。”
“你爸在天上看着呢,我不会让他失望的。”
下山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
我回头望去,那座新坟,在漫山遍野的墓碑中,显得那么孤单。
但我知道,他们父女俩,不孤单。
只要还有人记得他们,记得他们的故事,他们就永远活在某个地方。
回到家,我把自己关进了作坊。
我找出了一块最好的金丝楠木。
那是我压箱底的宝贝,木质细腻,纹理华美,在光线下会泛起金色的光泽。
我没有画图纸,小木人儿的样子,早已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我拿起刻刀,深吸一口气。
刀锋落在木头上,发出“簌簌”的轻响。
木屑飞舞,带着楠木特有的清香。
我的心,前所未有的平静。
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黑暗的监室,听着老马讲述他女儿的故事。
他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刻刀,把笑笑的样子,一笔一划地刻在了我的心里。
我做得非常慢,非常仔细。
每一个关节,每一个榫卯,都力求完美。
我不仅是在完成一个承诺,更是在进行一场修行。
这场修行,关乎手艺,关乎良心,关乎一个普通人对另一个普通人的,最沉重也最真挚的情义。
第7章 传承
那个穿着校服的小木人儿,我做了一个多月。
它只有巴掌大小,但四肢和头部都可以活动。
我用最细的画笔,给它画上了五官,那双眼睛,我反复画了十几次,才终于画出了笑笑照片里那种,弯弯的,像月牙儿一样的感觉。
校服的蓝色,我也调了很久,才调出那种最朴素,最常见的学生蓝。
做好的那天,我把它放在手心,感觉到的,不是木头的重量,而是一个生命的重量。
我没有立刻把它送到墓地去。
我把它放在了我作坊最显眼的位置。
每个来我这里定家具的人,我都会让他们看看这个小木人ë。
我会跟他们讲,这是一个父亲,留给女儿最后的念想。
我会跟他们讲,我李卫民做木匠,凭的是手艺,更是凭良心。
我的作坊,重新开张了。
生意没有以前那么火爆,因为我不再接那些催得急、利润薄的批量活儿。
我只接定制,每一件,都当成艺术品来做。
我用的都是最好的料,最传统的榫卯工艺。
我的价格比别人贵,但我的活儿,也比别人好。
渐渐地,我的名声又传开了。
人们都知道,城南有个李木匠,手艺好,人实在,做的家具,能传代。
老马留下的那五万块钱,我一分没动。
我用自己挣的钱,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基金。
我联系了律师,把这笔钱,捐给了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公益组织。
捐赠人,我写的是:马向东,马笑笑。
我希望,他们的名字,能以这样一种方式,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
也希望,这个世界上,能少一些像他们一样的悲剧。
两年缓刑期满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那个小木人儿,再次去了那个公墓。
我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在了笑笑的墓碑前。
“笑笑,叔叔来晚了。”
“你看,这是你爸让我给你做的。喜欢吗?”
阳光下,那个穿着校服的小木人儿,安静地坐在墓碑前,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
仿佛,她真的收到了这份,迟到了太久的礼物。
又过了几年,我的女儿考上了大学,学的是法律。
她说,她想成为一名好律师,去帮助那些像马伯伯一样,需要帮助的好人。
我的作坊,也收了几个徒弟。
都是些肯吃苦,爱琢磨的年轻人。
我教他们的第一课,不是如何使用工具,而是如何分辨木材的纹理。
我会告诉他们:“做木匠,跟做人一个道理。要顺着纹理,摸着良心。手里的活儿,不能骗人。心里的规矩,更不能丢。”
这些话,是我爸教我的,也是老马教我的。
现在,我再把它们,传下去。
每当夜深人静,我独自在作坊里,闻着满屋的木香,听着刨花落在地上的声音。
我总会想起那年在看守所的日子。
想起那个睡在我旁边,沉默了三天,最后却把“生”的希望留给我的男人。
他叫马向东,一个普通的卡车司机,一个伟大的父亲。
他用自己的生命,给我这个木匠,上了最深刻的一课。
他让我明白,人这一辈子,金钱名利,都是过眼云烟。
真正能留下的,是你的手艺,是你的口碑,是你骨子里的那份,对得起天地的良心。
还有,那份沉甸甸的,人与人之间的情义。
我拿起一块新的木料,在灯下仔细端详着它的纹理。
每一道纹理,都像一个故事。
而我的故事,从遇见老马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重新改写了。
人最感觉的苦是什么
你说这人间的苦,到底是个啥滋味?是医院缴费窗口前攥着空钱包的窘迫?是深夜接到儿子电话却不敢说家里出事的强颜欢笑?还是看着老伴病床上插满管子,自己却连个像样的护工都请不起的无力感?
张明的故事让我想起老话说的"贫贱夫妻百事哀"。但这哪是百事哀啊,分明是事事都扎心。他每天凌晨三点就起来,先给老伴擦身换药,再去地里摘菜,赶在早市前卖掉。中午回来熬粥,下午又去附近工地打零工。村里人都说他像台永动机,可谁知道他每晚躺下时,骨头缝里都在唱"二泉映月"。
最戳心的是有次老伴突然清醒,颤巍巍从枕头底下摸出个布包,里面是她攒了半年的零钱——总共三百二十七块五毛。"别告诉娃..."她气若游丝,"他娶媳妇还差彩礼钱..."张明当场就蹲在地上哭了,那哭声把院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都震落了好几片。
这世道啊,总有人把"坚强"说得轻飘飘。可真正的苦,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悲剧,而是像张明这样,把心碎成渣还得一粒粒捡起来过日子。就像那首老歌唱的:"生活啊,像一根线,有解不开的小疙瘩。"我们每个人,不都是在这根线上打结的人吗?
所以人间最苦的感觉是什么?大概就是明明自己已经苦得像块黄连,却还要笑着对最爱的人说:"我没事,你放心。"这种苦,比黄连还苦,比中药还难咽,可偏偏,这就是生活本来的味道。
文档上传者
热门标签
相关文档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