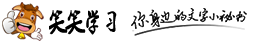欢迎来到98聘
一篇文章轻松搞定《别样人生作文》的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12-08 10:26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别样人生”的作文,需要关注以下几个关键事项,才能写出深度和特色:
"1. 理解“别样人生”的内涵与范围:"
"深入思考:" 首先要思考“别样人生”具体指什么?它不仅仅是与众不同,更强调一种与主流、常规或普遍认知不同的人生轨迹、选择、价值观或经历。 "界定范围:" 确定你想要写的“别样”是什么?是职业选择(如艺术家、志愿者、自由职业者)、生活方式(如极简主义、数字游民)、人生追求(如专注公益、探索极限)、面对的困境与挑战(如残疾、逆境重生)、独特的成长环境(如单亲家庭、国际交流)等等。范围要明确,避免泛泛而谈。
"2. 选择独特的切入点与视角:"
"避免陈词滥调:" 不要仅仅停留在“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独特的”这种表面认知上。要挖掘更深层次的“别样”之处,比如这种“别样”是如何形成的?它带来了什么特殊的体验、感悟或挑战? "个人经历与观察结合:" 如果可能,结合自己的观察、阅读或真实的个人经历来写,会更具真情实感和说服力。即使写他人的故事,也要有独特的观察角度。 "聚焦核心:" 选择最能体现“别样
别样人生
似乎写不出什么新意来了。我想是该把精力转移,去完成我那些初步构思,但远未成型的小说。
现在有三部小说构思,也都写了开篇。一些创作片段也曾发在。
完整完成的第一篇小说是《山外青山》,篇幅比较短,或许应算是一个加长的散文。它披着一个科幻的外衣,虚构了七条宇宙航线,煞有其事起了七个名字,但没有太多的故事情节,想表达的是在星际航行中却怀揣着古典的忧伤。或许源于少年时读过的班马的一篇散文《星球细语》,还记得开头一句:在太空中,宇航员的脸陷入了难解的惆怅。
但说起来,写部小说的念头萦绕已久。2014年,11年前,罗列了一部小说大纲,题材是穿越+武侠。毕竟少年时沉醉武侠世界,中年又恰逢穿越风潮。主角暂名霍许,或许可以是这样吧。小说设想三部,背景是大唐中宗时期,禅宗一花开五叶的盛景之下。当然穿越者最可贵的是什么?是超前的见识?是渊博的知识?或许有一些吧。但我认为,最能触动人心的是那份现代人的心性与情感。文字方面,有意模仿了金庸文风,类似《倚天屠龙记》中俞岱岩出场时的白描手法。
我这样的写的:大唐大中六年,潭州官道上,一名弱冠少年正大步疾行。遥见沩山逶迤,不禁拭去额头细密的汗珠,吁出一口气。此次下山竟已二月有余,下山前,在山腰的密印禅院里,师傅嘱托了两件事情,一是请仰山慧寂禅师在大雪封山前亲来,有要事商榷。二是绕路去宣州采办纸笔,在辩经会前带回大沩山。不想在途中,受阻于兵变,耽搁了时辰,总算日夜兼程赶回潭州地界。
然而,金庸的文字看似平实,内里却是深厚功力与广博学识的沉淀,加之构建故事的非凡天赋与耐心,我终究力有未逮,只留下些许片段。
时光荏苒,2025年4月,我驻足。遥想当年在“我看看中文网”、搜狐博客的岁月,已恍如隔世。小店重开,总想用心经营。终于,完成了写篇科幻的心愿,《山外青山》就此诞生。我很新欢这种诗意冷感的科技描写。
山外青山写完后,两位道友提供了新的思路。道友A大手一挥:“要修仙!”道友B金口一开:“要现代!”。于是冒出《我在精神病院学修仙》这个题目。时值6月,我在《感谢道友赐我“仙现”混搭风》中宣告,将不自量力地开启新小说,计划用三个月勾勒大纲,并陆续发了六七篇创作随笔。但真正落笔,方知难度。
小说主角,我命名为吴可。无可无不可之意。讲述一个刚魂魄穿越到这个世界的人,醒来即面临一场蓄谋已久、即将收尾的阴谋,被原身女友的追求者、闺蜜联手设计,以“精神问题”为由送入“云水精神康复疗养院”,遭遇冷漠医生、强制治疗的故事。框架易搭,细节难填,精神病院的日常、功法进阶体系等等,犹如大楼初成,内部的水电通风消防等系统才最是繁琐。
7月底,写下《打了三针科兴,我也想有个系统》;8月初,又在《放下“端着”,写个“不正经”的爽文!》中说,有了新的构思,暂定名《我的系统不正经》或《二流人生绑定系统》。我决心写一部“庸俗”的小说,打破所有框架束缚,让逻辑与三观暂时退位。
或许正因为放下了“必须好好写”的包袱,这篇系统文的推进反而顺畅许多。只要我能厚着脸皮,毫无顾忌地恶搞,完成度便大幅提升。它必须是一部有趣的小说,其核心信条是:不能先把自己逗乐的章节,都要推翻重来。摈弃束缚三观的枷锁!释放内心深处的恶趣味吧,反正这里没人识得我。
写了大约二十章,没有完成。10月底,《退休名单》一文催生了“方想”这个名字。自觉名字不错,不要浪费,便为其写了《无限循环》与《未至之境》,于是第三部小说构思应运而生。《未至之境》或许更贴合我当下的心境,我渴望一种克制精准、带有诗意冷感的文字,小说侧重于思辨,甚至有意规避强烈情节,因为我尚未发现自己有擅长设计复杂故事的天赋。
似乎创作总始于一些灵光的碎片:一个萦绕不散的场景,一段暗自回响的对话。常常这样,为了一碟醋,包一顿饺子。为一个设想中的情节或几句有意思的对白,便敷衍出众多人物,架构起复杂关系,进而硬要凑成一部小说的规模。
时间是越过越快的,不经意间,少年的诗篇就那样留在了少年时期。中年的散文顺理成章的接替上来。而今开始琢磨小说,难道不是因为即将跨入老年的门槛。毕竟明年,我就有资格领取单位重阳节的礼物了。小说,是规模更庞大、结构更复杂的另一种生活,也是重现脑海中那些或许一闪而过的别样人生。
在我们日积月累,耗资巨大而一无所获的生活里,如果有一天回望,其实人生留下的也就这么点儿东西。它没给我带来任何名望,金钱和权利。它只是伴随着心情的起伏,思想波动自然诞生。它占据了玩乐的时间,也需要不断地学习,思考。但不同于学习的是,它从未让你感到过痛苦。它更像一种温柔的牵引,能抚慰你的情绪,安抚你的内心。这就是爱好。
那么,让这三部小说彼此间产生些微妙的关联吧。时间跨度就设定为一百年。这三篇都是偶然触发,但有个有趣的规律:后发者往往先至。《我在精神病院学修仙》是逆境中的奇遇,《二流人生绑定系统》是庸常中的开心,《未至之境》则是说无限循环中微小的偏差。我可能会先继续创作第三部,因为前两部隔得有点久,有些忘了当时的心境与设定。
写过一篇《我们都在排队等待被这个世界删除》,像古老王朝的经卷,悄然消失。可是终究还有表达的欲望。依然生活在执念之间。
在被删除之前,让我们开启别样人生吧。
《陆小曼:别样的人生》
1956年春,陆小曼就在上海文史馆干活,每天都在琢磨画国画。那年头,她画的《江边绿荫》《清溪待渡》还上了全国国画展。这个事儿,让大家一下子注意到她不光有才气,还真有两下子。除此之外,她还动起了翻译的心思,把一些外国文学搬成中文,连泰戈尔的短篇小说都敢揽过来试试。其实她早就热爱这些东西,现在终于有机会沉下心做点自己的事,也算给自己找了个安身立命的法子。
讲真,那会儿陆小曼早就不怎么出门了。以前的舞会、牌局、社交场合都通通不去,家里胭脂水粉也都搁着落灰。她基本一天到晚关在家里跟老师琢磨画画,越画越专心。老师贺天健给她定了不少规矩,说要么认真学,要么干脆别浪费时间。一个月学费五十大洋,可真不是小数目。如果偶尔混日子偷懒,她就会瞄一眼卧室里的徐志摩照片,心里就像被扎了一下,立马就收心敛神再画起来。日子虽清淡,画画却成了她顶重要的事儿。
正是画画这个手艺,让陆小曼觉得自己还能靠双手吃饭,不至于太没底气。早在1941年她就在上海弄了个展览,画了上百件作品,山水、花鸟什么风格都有,清爽里透着些许灵气。之后这类画展她也参加了好几回。慢慢的,大家说起她,不再光惦记着“徐志摩的前妻”,而是夸她成了“画家陆小曼”。也许对于她,这就是某种新开始。她没那么在意别人的评价,不过那点认可,还是让她多少舒服了些。
但时间再往前推点,徐志摩走之后,陆小曼的生活其实是一天不如一天。她身体本来就弱,还要靠翁瑞午帮她按摩、配药维持。翁瑞午原本是个推拿师,后来两个人竟相伴三十年,这其中有些说不清的依赖。翁瑞午那时有正式的太太,这种关系搁外人眼里当然觉得奇怪。但陆小曼贪恋这份照料,大概也是无可奈何。最早,为了让她止痛,翁瑞午让她试了鸦片,没想到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到底是她生性软弱还是太执拗?谁说得准呢。如果不是徐志摩离去那么突然,她也许不会一直搅进这些不堪的麻烦里。
说到1931年深秋徐志摩那一天,其实挺让人心堵。为了能省点路费,他硬是搭了免费飞机进京去赶林徽因的讲座。可是天不遂人愿,飞机失事,他就这样撒手人寰。对于陆小曼,那是彻底毁灭性的打击。她觉得,这一切都跟自己的花销有关,甚至认定自己拖累了他。那篇《哭摩》的文字,读出来就知道她心里的自责和难以释怀。这两个人结婚那会儿,早就成了众人谈资,等到最后却收场成了这样的结局。
再往回说,陆小曼和徐志摩那场婚姻,也确实够轰动。婚礼当天请来了梁启超当证婚人,结果人家当场批评这俩,志摩太浮夸成不了大器,小曼要收敛脾气知错能改。两个人啥也没说,就是相互一笑。整个婚姻,外头人说三道四,两边家里都反对,可他们就是一心认定了彼此。可惜爱情终归抵不过柴米油盐。陆小曼花钱没数,吃穿用度都得讲究连鸦片都看质量。志摩为了应付日常,只能到处讲课、奔波挣钱,来来回回,能挺那么久已经不容易。很多人说他是被现实和情感压垮,其实也真没冤枉他。
其实刚开始结缘,陆小曼和徐志摩还得“感谢”王赓。那时候陆小曼刚结婚,人还算规矩。王赓出差的时候把师弟徐志摩托付给小曼照顾。这俩人,一个温柔文雅有点浪漫情结,一个是上海大家闺秀爱自由好玩。结伴久了,感情也就慢慢起来了。俩人很快就擦出火花,北平坊间小报天天写“出轨”“夺爱”之类的新闻,大街小巷都在议论。离婚那一年,她还因为堕胎出了问题,不仅此生没法生孩子,还落下了病根。这种身体和心理的伤害其实比看得见的还要重,也给后来依赖鸦片埋下了隐患。
王赓其实条件很好,留美回来的高才生,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仕途一片坦途。婚礼那天,一片盛大,连报纸都说是“第一良缘”。不过说到底,小曼要的是浪漫轻松,人家王赓只有军人那一板一眼。家里气氛越来越冷,最后关系就僵在那儿了。像他俩这样的,凑一块其实挺不合适。
更早的事,大家其实都知道小曼出身不凡。家里是上海有头有脸的官宦人家,父亲陆定官场里混得开,母亲吴曼华也是名门之女,擅画会写,一身才气。小时候,她跟着父母去北京,进了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好得不行。英语、法语都玩得转,文学、音乐、绘画全都懂三分,妥妥的学霸。后来外交部临时要翻译,顾维钧点名让她参加“巴黎和会”,直接成了社交圈里的红人。
她年轻时那会儿风光得很:舞会、戏院、打牌啥事都喜欢,大家都争着和她结交。还有个“南唐北陆”说法,唐瑛和她,一个南方一个北方,是民国里最出色的名媛。各大报纸都夸她“艳压群芳”,其实她心里门儿清,回家日记上也会写寂寞。外头人只关心她漂不漂亮,没人关心她到底喜欢什么,想要什么。她看起来享受荣光,可实际上,她最想的,是有人,能理解她的灵魂。可这世道里,懂得她的人总是姗姗来迟。
说白了,陆小曼这辈子经历过盛放的光彩,也受过没人能懂的孤独。她有些日子活成了别人期盼的样子,有些时候却只能跟自己死磕。她喜欢的东西,从来都不是轻轻松松就能捧到手。这世上的事,真是没法讲什么绝对的对错。就像有的人活到老,都还在追寻,究竟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是幸运,还是遗憾,说不明白。
到了后来,她性格也越来越沉静。不出门就是常态了,画画成了每天的功课。有爱好能支撑,挺过那些灰暗时光。周围人说她是“画家陆小曼”,她听着,心里其实也五味杂陈。往往别人注重的是她和徐志摩的故事,赞叹的是她的美貌,只有画画让她觉得活得真实,手下的画是真正归自己的。过去那些大起大落的日子,就像翻过的一页,留下痕迹不再回头。
邻居偶尔会见到她在窗口静坐,手边摊着画纸,有时候还会点支烟,静静地望着外头的天色。久了,谁也不问她的过去,大家都觉得她安静得很。有时候有人送些吃的用的东西过来,家里也并不富足。她也没什么怨言,摇头笑笑。偶尔提起徐志摩,也只是淡淡地说几句,并不多再诉苦。
家里那张徐志摩的照片,是她不愿割舍哀愁的记忆,于她而言,像座无法跨过的桥。心底唯一的慰藉,莫过于画笔下流淌的色彩。她会在画上撒点泪水,却也就那么过去了。日子虽不富贵,但也自有一份平静。
她后来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医药费花去不少。翁瑞午偶尔带些药过来帮她缓解疼痛。朋友来看她,有的惋惜,有的叹气,还有人私下里说她可惜了。有些远房亲戚提及她和徐志摩,偶尔还感慨一番,但日子久了也无人再提。她自己习惯了孤独,也不再向谁诉说太多。
她其实有时会跟过去的自己“对话”。日记里画满草草几笔的肖像画,下边写着“如能重来,好好生活”。但这话没人看得见,只有她自己知道。那些年,在大名鼎鼎的人物堆里走过来,看透了繁华,也学会了独处。人到老年,日子单调,但是心里清楚,画画是自己唯一的归宿。谁都劝不动她改掉抽鸦片的毛病,她只是笑笑,摆手不再解释。
陆小曼偶尔还勉强去见些同龄朋友,聊聊世事,也聊聊家常。大家闲来提起旧时,彼此都说还挺想念热闹的岁月,但生活总要往前走。她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今后的日子哪怕再普通,自己也要安安稳稳过下去。
有时候,她午后会在窗前发呆,看院子树影斑驳。邻居偶尔喊她出去晒晒太阳,她也只是轻轻地挥挥手,说自己待着挺好。院子里有只流浪猫,人来猫往,大家习惯了。她有时会喂喂猫,看着猫吃饭,把手里的画笔轻轻搁在案头,仿佛找到些许乐趣。
其实旁人看她冷漠,内心其实柔软。她时常把小小的善意藏在琐碎里,不求回报。有邻居生病,她会让人带点汤过去;有小孩子考试,她偶尔会教教几句英文。她并不求成为谁的榜样,只是想把日子一天天熬下去,肚子里还埋着一大片温情。
晚年的陆小曼,画展渐渐办得少了。身体不大能扛,画作也没那么多了。但每当家里来了朋友,她还是会亮出几幅心爱之作,跟人讲讲当年在外头展出的趣事。听的人有时笑着,有时静静地听她聊。没有人再问那些旧事,大家不再关心她和徐志摩之间到底怎么了,只是做个平常的朋友,过些平静的日子。
有些时候,她会在花瓶里插几支自己画出来的菊花,待着静静看。外头雨下得大,她絮叨着天气变凉。屋里空气不流通,她也不多说什么。每天清晨醒来,就铺开画纸,不赶时髦,也不上心别人的议论,安安静静画自己的山水。
她这一生,华丽过、孤单过,跌跌撞撞也是难免。画画给了自己片刻的安稳,外界的风言风语不再能影响她的心情。老照片藏在抽屉底,不再翻看。日子清淡,身心也不再挣扎,剩下的,只是随缘而安。
有时候想起年轻时的疯狂,她自己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人生好像一场大梦,醒了就淡淡地承认,梦里热闹,梦外清静,都是历练。人总要学会跟自己和解,有些理想没能实现,也没什么可惜的。
陆小曼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偶尔会有朋友探望,她也只是说自己还挺好的,不愿多谈病痛。画室角落放着旧画,也不再整理。她说,过去的光亮都变成了今天的影子,人只要还能画画,就不算太薄凉。这话听着简单,其实藏着数不清的无奈和坦然。
临近晚年,陆小曼也慢慢变得淡然。她不再主动联系任何老友,连外头有人提起她,也只是尴尬地笑笑。那些曾经赞美她风采的人,现在只剩下偶尔回忆,或者在旧报纸上一瞥。陆小曼自己则忙着画画,哪怕手没那么稳,也要把一笔一画画出来,像和时间作对。
偶尔,在夜晚,她会在灯下翻翻旧书。在泰戈尔诗集旁边,是几张信纸。她并不多说过去,只在心里盘算着明天要画什么。家里的猫安静地趴在地板上,她就这样静静地守着自己的空间。
日子流走,身边的人也渐渐换了一批又一批。不变的是她的小屋、一盏灯、几张画纸。外头无论吵闹还是安静,她都波澜不惊。旧友的来信偶尔会送到门口,她看一眼,淡淡收下又不着急回信。画笔还在她手里,生活也还在继续。
就这样陆小曼走完了自己的路。没太多轰轰烈烈,也没太多悲情。她就用画笔和平凡日子,安安静静地把自己活成了别人口中的故事,自己的故事,却只有自己懂。
文档上传者
热门标签
相关文档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