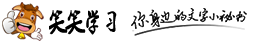欢迎来到98聘
一篇文章轻松搞定《时间的声音作文》的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12-08 11:56

写作核心提示:
这是一篇关于“时间的声音”的作文,并附带写作注意事项。
---
"作文:时间的声音"
时间,这位无声的画师,这位无形的雕刻家,它用看不见的手,塑造着世界,也改变着我们。我们常常谈论时间的流逝,感叹它的无情与匆匆,却很少去倾听,它是否真的有声音?在我看来,时间的声音,并非来自某个特定的源头,而是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以细微而深刻的方式,回响在我们的生命里。
时间的声音,首先体现在自然的更迭之中。听,春天到来时,冰雪消融的碎裂声,是时间悄然揭开大地面纱的低语;嫩芽破土而出的细微声响,是生命在时间里萌发的喜悦之音;夏日炎炎,蝉鸣聒噪,那是不知疲倦的生命在时间长河中奋力歌唱的旋律;秋风乍起,落叶簌簌,是时间挥别季节的叹息,带着成熟的丰盈与淡淡的忧伤;严冬降临,万籁俱寂,雪花飘落的无声无息,仿佛是时间沉淀下来的宁静与肃穆。这些自然的声音,是时间流淌过万物的脚步声,是它刻录下的季节之歌。
时间的声音,也蕴含在生活的日常里。清晨,闹钟的滴答声或父母的催促声,是时间提醒我们新的一天已经开始;白日里,键盘敲击的嗒
把航空机翼的理论“安”进人的心脏里
【科学家日历】
点滴故事中,领略科学家精神的熠熠光辉。我们特别开设【科学家日历】专栏,讲述科学家的故事,打造展示科学家群像风采的“人物志”、讲述科技事业发展历程的“时光笺”、弘扬科学家精神内涵的“文化集”。
康振黄(1920年6月1日—2018年12月5日)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空气动力学家,工程流体力学家,生物力学家,力学教育家。
康振黄长期从事空气动力学、流体力学、生物力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提出了双叶翼型人工机械心瓣设计理论。为推动我国生物力学和人工心脏产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2025年12月5日是他逝世7周年,我们一起纪念。
康振黄少年逢抗战,他弃北大、选航空,立志救国。赴美完成学业后,他毅然归国。他拿扫帚当“机翼模型”,靠流体力学救回精密天平;他拓荒生物力学,把航空薄翼“折”成人工心瓣,终成中国生物力学开拓者之一。康振黄用一生践行着“务实报国”的信念。
车间里的“机翼”
1969年的成都科学仪器厂车间里,正在打扫卫生的康振黄蹲在一台停摆的精密天平旁发呆。这台天平是当时科研检测的核心设备,其关键部件“阻尼器”的性能直接决定测量精度——阻尼器需通过特定材质的结构控制流体流动速度,从而抵消天平摆动的惯性,让指针稳定在准确数值上。而当时正值物资供应紧张的时期,阻尼器的核心结构依赖高纯度铝材制造,偏偏铝材因产能受限、运输受阻而陷入短缺,整台天平也只能暂时闲置。
这位曾专攻航空流体力学的教授,虽暂别实验室,却没丢掉专业本能。康振黄盯着天平的阻尼结构陷入沉思:阻尼器本质是“流体在特定腔体中的运动控制”,这和航空机翼在气流中通过形态调整受力、控制飞行姿态的流体力学原理,其实是相通的。手边没有专业模型,他便捡起扫地的扫帚柄,把细长的柄身当作简化的“机翼模型”,反复调整扫帚柄与地面的夹角,模拟不同气流角度下机翼的受力情况,同时指尖在灰尘里快速演算流体力学公式。
通过扫帚柄的形态模拟,康振黄精准推导出水力阻尼的关键参数:比如流体通过阻尼孔的流速、压力损失与材质密度、结构形态的对应关系。他发现,当时供应相对稳定的铜材,虽然密度与铝材不同,但通过调整阻尼孔的孔径和铜质部件的厚度,其阻尼系数能完美匹配天平的需求,完全可以替代缺供的铝材。一番针对性改造后,这台停摆多日的精密天平重新达到测量标准。谁也没料到,这蹲在车间里用扫帚柄推演原理的“扫地教授”,会在十年后,把航空机翼的理论“安”进人的心脏里。
把航空翼折进心脏的瓣叶
1979年,59岁的康振黄推开了华西医科大学的诊室门。当医生指着患者胸口的人工心瓣摇头时,他攥紧了手里的病历:当时的人工心瓣多是单叶或僵硬结构,开合完全依赖血流冲击——血液向前泵出时瓣叶完全打开,血流回落时才被动关闭,这种“全开全闭”的模式会留下明显的时间差和缝隙,导致血液大量回流,患者术后稍一活动就胸闷气短,当时国内还无一人从力学角度破解这一难题。
“航空里的薄翼能通过流线型姿态减阻,还能提前调整角度应对气流变化,心瓣不也是流体里的‘翼’?”像当年主动接下天平难题时一样,康振黄攥住了这个跨界的机会。
这是条没人走过的路:医学家不懂流体力学,力学家摸不透心脏生理。康振黄把实验室搬进了诊室,一边跟着医生听诊,一边在解剖图上标流体轨迹。他发现,心脏泵血的血流速度、压力变化和航空气流的动态特性高度相似,于是将航空领域的“薄翼理论”拆解重组:
把双叶瓣叶设计成流线型,就像机翼一样贴合血流方向,更关键的是,借鉴机翼“提前调整姿态应对气流”的逻辑,让瓣叶不再被动等待血流回落才关闭,而是在血流峰值过后、开始回流前就“提前部分关闭”。这种设计能精准缩小瓣叶间的缝隙,从源头阻断回流通道。
实验室的玻璃罐里,模拟血液的液体打着旋冲击着模型瓣叶。前50次试验,瓣叶要么卡壳要么回流超标,年轻助手揉着熬红的眼叹气,康振黄却举着磨损的模型说:“航空颤振试验失败了上百次,心瓣也得‘飞’过这关。”他把瓣叶弧度磨得比机翼梢尖还精细,在公式里抠到毫米级的流体夹角,终于在第73次试验时,玻璃罐里的“血液”顺着瓣叶流畅开合,回流率也降到了国际标准范围之内。
康振黄(左)在实验室观察人工心瓣复位模拟装置
来源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缝进瓣叶里的科学家底色
1985年的手术室灯亮起时,康振黄攥着心瓣装置的手在抖。当“双叶翼型人工心瓣”成功植入患者胸腔,监护仪上的血流曲线渐趋平稳,在场的医生才惊觉:这位同时承担着重要学术管理工作的老人,是白天处理学术事务、深夜泡在实验室里,才把“航空翼尖”折成了救心的“瓣叶”。
后来有人问他,59岁跨界值吗?他指着书架上《心瓣流体动力学》的手稿——那是国际上首部心瓣力学专著,扉页写着“翼向空天,瓣向人心”。即便后来承担起更繁重的学术管理职责,他仍揣着心瓣模型去研究生实验室,把常用的公文包改成了“力学公式本”,随时记录科研灵感与推导过程。
当患者握着他的手说“能跑了”时,康振黄想起当年车间里的天平:无论是扫着地解技术难题,还是在花甲之年拓荒生物力学,他的“科学家底色”从没变过——是把专业刻进骨子里的务实,是把国家需求扛在肩上的较真,是哪怕翼尖转向,也要朝着有用的方向飞。
这枚从机翼理论里长出来的心瓣,成了中国生物力学的第一颗种子,而康振黄蹲在车间、诊室、实验室里的身影,早已把跨界拓荒、务实报国的科学家精神,缝进了每一片流动的瓣叶里。
康振黄(讲课者)给学生讲解流体力学
来源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
科学家说:
康振黄说:“我们就去找那个世界前沿的,人家没有解决或正在解决的,我们就搞这个,不能去跟着人家的后面走。”
康振黄说:“带好研究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中国的事业得靠这些年轻人来继承。因此,凡我知道的知识都及时传授给他们,不知道的,就引导他们学习,让他们迅速成长。”
审核专家:周广刚,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理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康振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采集工程.
工程流体力学家康振黄:让生命之花灿烂.正脉科工CAE.2022-9-28.
心瓣探微:康振黄传.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
迎接教育事业黄金时代的到来.四川教育,1985,(03):6.
关于科技形势和加强科技管理的几个问题——访四川省副省长康振黄教授.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4,(03):16-19.
供 稿: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特约编辑:王学健 解雨婷
责 编:谢 芸
审 核:张敬一
值班编委:孟令耘
来源: 中国科协之声
老 家
漫长的农耕岁月,人们以家族为单位共同守护着一方水土,一个家园。家,除了居住地标识外,这里的每一块砖瓦,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光阴流转,记录着成长痕迹,给人以深刻的情感与文化寄托。对家的深深依恋,孵育了国人热土难离、安土重迁的心理情结。但凡有一线生机,则不会轻易离开故土,一旦外出谋生,立马就有颠沛流离、背井离乡之类的概念来定义心中的无奈与生存的艰辛。虽然现代社会早把这类传统习俗冲得七零八落,年轻人倾心于“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执意将远方与“诗”联系在一起,把出门闯荡、四海为家视为生活的常态与时尚,然而,家乡观念作为某种生理与心理的特殊纽带并没就此割裂,无论是普通话交谈中偶尔流露的地方口音,还是饮食口味里顽强存在的舌尖记忆,依然能把天南地北聚拢在一起的人们清晰地按地域区分开来。
因此,回老家,仍旧是游子们言语和行为中频繁出现的表达。
自己从19岁离开家乡,在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回家的次数少说过百,且集中于过年过节回乡人群最密集的时段,拥塞的路途、嘈杂的客流、奔波的劳苦以及千篇一律的重复行程,经常让回家的归途变成疲惫之旅,但每年一如既往,从来没有滋生过一丝一毫的厌倦情绪。老家何以具此魅力?思来想去,一时还真的难以说清。
高铁普及后,回家变得轻松便捷,但当年排队买票、上车无座、车厢内拥挤不堪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今年回乡时,路过当初风光无二、如今却显得荒凉破败的老火车站,浓浓的酸楚感瞬间从胸中涌出。曾经无数次在这里上车下车,回家的距离,被这里的“绿色长龙”一寸寸丈量,绿皮车将一幅漫长的故乡画卷缓缓收起,又徐徐展开。而心里的感受,也在车轮与铁轨接缝处撞出的“哐当”声中,被拉扯得五味杂陈。归来的喜悦与不舍离去的复杂情绪,或许还飘浮在某个车厢的角落,生命漂泊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绵延无际的铁轨上。那时节,车次很少,供需关系格外紧张,尤其在春节前,能抢到一张回家的车票简直就是莫大福分。最难忘的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刚拿到回乡探亲的车票,却因参加单位一位特别受尊敬的老大姐的告别仪式,无奈临时退票。完事后,四处托人,购票无望,只好买张站台票上车。那是一趟深夜发出的列车,车厢里水泄不通,挤满了持站票的乘客,自己被夹在两节车厢连接处的过道里,人挨人站立的距离连转下身都十分困难。车厢内混杂着煤灰、汗馊、泡面和橘子皮的浓烈怪味,最初令人倍感恶心,许久方才慢慢适应。虽系寒冬,车厢里却闷热如夏,身上不时冒出细汗。如此这般,一动不动地站了整整一夜,不仅未得一刻睡眠,而且连水也没喝上。黎明时分准备下车时,弯腰拿起脚边的提包,突然发现皮包已被火车连接处活动的底盘磨出了一个大洞,衣服和物品纷纷滑落。慌乱中只好把衣物塞进提包漏洞,倒过来抱着行李挤出车厢,那尴尬狼狈之状,至今记忆犹新。
那年月,哪回探亲都是一次疲于奔命的艰辛旅程。即使有幸购得一张坐票,过道里照样挤满了无座的旅客,三人一排的座位总会挤进一个无法长时间站立的老年人,严重的时候连厕所里也站满无处可去的乘客,上个厕所总不免大费一番周折。车厢的气味一如既往地污浊,加上抽烟者不管不顾地狂吸,时间一长,头痛欲裂感随之而来。思乡却又恐惧乘车回家,有这等心理者恐怕不在少数。
尽管回家的路途充满艰辛,但游子回归的决心从来未被撼动过。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当然是亲情的牵挂和团圆的渴望,是游子对家乡的思念与留恋。回家似乎早已内化为一种近乎自动的生理时钟。当春节、中秋等特定节日临近时,身体和心灵会自动进入“准备回家”的状态,仿佛成了一种不需要任何理由、本该如此的规定性动作。回家变为一种遵从生命节律的惯性,变为一首本能、习惯与文化共同谱写的协奏曲,变为再一次关于“我是谁”的庄严确认。
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回老家除了一份亲情的召唤之外,更重要的还源于心灵深处与自我过往对话的需求。回到亲人身边,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既是现场的探望,也是往昔的追忆,更是寻找情感寄托的心灵治愈之旅。
尽管每次归来,老家都不再是曾经的模样,尽管老家是个固定的地理锚点,但每次归途都像在接近一个不断后退的镜像。新修的柏油路已经覆盖了当年草籽的梦境;手机地图虽能定位老屋的坐标,却测不出井水曾有的甘甜;那些曾经熟悉的人,有的已经离世,年轻人也变得陌生;曾经的欢声笑语,如今只能在记忆中回响。这样的变化,无法不让人深感生命的脆弱和无常。只有回家才能明白,携带故乡行走的游子,如同蜗牛背负着城堡,每一道螺旋斑纹都是早已压缩过的星空。尽管我们不能阻止时间的流逝,无法挽回失去的一切,但在追忆中,我们可以找到那曾经的美好,使之变为游子奋发前行的动力。
老家或许就是这种时空交错、虚实相生的复杂存在,是游子用记忆纺成的岁月绸缎。它或许就是春雨后泥土苏醒的腥气,是冬日灶膛里红薯烤焦的甜香,是母亲晾晒的棉被上阳光与皂角交织的味道;或许就是午后巷口豆腐佬悠长的吆喝声,是夏夜池塘青蛙们不知疲倦的合唱,是祖母油灯下永远讲不完的故事里轻柔的停顿与叹息;或许就是身体早已熟记的地图,是脚掌熟悉的每一块青石板的凸凹,是指尖记得的老墙门楣上那一道残留的划痕。它们虽静默无语,却将一切编织进你的骨血里,成为你生命的底色与初音。
时光如一条潺潺的溪流悄然滑过,而老家,就像那溪流深处的一块带有包浆的石头,始终在记忆的河床上静静沉卧,散发着湿润而熟悉的光泽。无论光阴如何流转,那个见证过自己成长印记的老家,始终是游子心灵的港湾;童稚时代最初的纯真与热情,永远是心灵深处最柔软的情感源泉。只要回到老家,人们就可以卸下所有的面具,找回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感受那份最纯粹的温馨和安宁。夜晚,当你躺在童年睡过的老床上,四周一片寂静,听着窗外隐约传来的蛙声和虫鸣,儿时的摇篮曲仿佛重新在耳边响起,所有熟悉的环境与气息都能诱人回到那个被爱包围的童年,生命中一切的烦恼和疲惫都会在这一刻烟消云散。回老家,哪里只是躯体的回归,其实更是心灵的洗礼,使人在纯真的回忆和深切的眷恋中感受到生命的温暖和力量。
老家的本质,或许正是这种时空交错的双重叠影:我们永远在离开它的过程里完成对它的抵达,在渐次遗忘的间隙里突然与它迎面相逢。老家在时间的炼金术中不断被改建。童年的眼里,那是个膨胀的宇宙,家后土山上的蟋蟀洞可能通往地心,河滩上的鹅卵石或是休眠的星球;长时间离家之后,故乡开始坍缩,坍缩成电话里的某种方言,坍缩成履历表上的个人籍贯,最后坍缩成体检报告里与出生地相关的遗传密码。渐渐地,老家已不再是你回去就能够找到的地方,变成你远行时行李箱夹层里残留的乡土,成为你大脑中始终装着的发酵过的记忆,甚至是一个不断被书写与深爱的流动的背影。
老家不仅是地图上的某个经纬坐标,更是我们不断重写的记忆手稿。尽管每次回望都会修改它外在的轮廓,但它始终钉在那里,若胎记般长在生命的初处。
云 德
文档上传者
热门标签
相关文档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