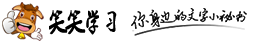欢迎来到98聘
熟悉的身影作文如何写我教你。(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12-18 10:56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熟悉的身影”的作文,可以抓住以下几个关键点来注意:
"1. 明确“熟悉的身影”的含义和对象:"
"具体化:" “熟悉的身影”通常不是指一个模糊的概念,而是指某个具体的人、某种反复出现的人或某种场景中的人。你需要首先明确你想要描写的是谁的或哪类人的身影。比如:是每天清晨清扫街道的环卫工人?是放学路上总能看到的老师?是每次遇到困难时默默帮助你的朋友?还是某个特定节日里忙碌的身影(如节日庆典的志愿者、年夜饭时厨房里忙碌的家人)? "确定核心:" 思考这个“熟悉的身影”为什么对你来说“熟悉”?是因为经常见到?还是因为这个人/这个身影对你有特殊的意义?
"2. 深入挖掘“熟悉”背后的情感和意义:"
"不仅仅是看见:" 作文的关键在于写出“熟悉”带来的感受和思考,而不仅仅是描述这个人或身影长什么样。你要写出你看到这个身影时内心的情感变化:是温暖、感动、敬佩、思念,还是带有一丝淡淡的忧伤? "建立联系:" 这个身影与你之间有什么联系?它是否见证了你的成长?是否给你带来了某种力量或影响?是否代表了一种习惯、一种承诺、一种精神? "提炼主旨:" 思考这个“熟悉的身影”想要
童年回忆!当校园里出现熟悉的“跳房子”……
视频加载中...
近日,四川德阳。当学校里出现“跳房子”,接下来的一幕幕令人感慨……熟悉的格子、跳跃的身影,让无数人瞬间回到童年。网友:跳房子是怎么做到全国统一的?
母亲总偷藏剩饭,我跟踪她到孤儿院,顿时红了眼眶。
一碗剩饭
第一章 灶台上的秘密
我叫张伟,今年四十二,在城里一家不大不小的单位里做个部门副手,日子不好不坏,就像温吞水,喝着不烫嘴,也没什么滋味。
可最近这大半年,我这碗温吞水,被我妈搅得起了波澜。
起因,是剩饭。
更准确地说,是那些被我妈像宝贝一样,偷偷摸摸藏起来的剩饭。
这事儿一开始是我媳妇小莉发现的。
小莉是个爱干净的女人,我们家那一百二十平的房子,被她拾掇得一尘不染,连踢脚线都擦得反光。
我妈是三年前我爸走了以后,被我硬从乡下老家接过来的。
一开始,小莉对我妈,那是没得说的。
嘘寒问暖,换季的衣服、脚上的鞋,都置办得妥妥帖帖。
可时间长了,两代人的生活习惯,就像两块长得不一样的石头,怎么摆都硌得慌。
最大的矛盾,就出在这吃饭上。
我们家条件还行,小莉又是讲究营养搭配的人,每天晚上的饭桌,四菜一汤是标配,总有鱼有肉。
我妈刚来的时候,看着一桌子菜,总是缩着手,嘴里念叨:“吃不了,吃不了,太浪费了。”
小莉就笑着说:“妈,没事,吃不完明天热热还能吃。”
可后来,小莉发现不对劲了。
冰箱里的剩菜,总是莫名其妙地失踪。
不是那种放了两三天,被我们公认该扔掉的。
而是头天晚上的红烧肉,第二天中午小莉想给我儿子小宇做个盖饭,一开冰箱,没了。
盘子倒是洗得干干净净,扣在碗柜里。
小莉问我:“老张,昨晚那半盘红烧肉你早上吃了?”
我正喝着豆浆,含糊着说:“没啊,早上谁吃那么腻的。”
“那能去哪儿了?”小莉嘀咕着,也没往心里去。
可这样的事,一连发生了好几次。
有时候是一碗炖鸡,有时候是几条烧得好好的鲫鱼。
小莉开始怀疑是不是冰箱坏了,东西放不住,被我妈提前扔了。
我妈听了,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没有没有,多好的东西,扔了遭天谴。”
这事儿就成了一桩悬案。
直到有一次,小莉半夜起来给小宇盖被子,路过厨房,听见里面有窸窸窣窣的声音。
她悄悄凑过去一看,我妈正猫着腰,借着冰箱里透出来的微光,把一盘剩的饺子,小心翼翼地往一个塑料袋里装。
那神情,专注又紧张,像是在藏什么绝世珍宝。
小莉没出声,第二天早上才跟我说。
我当时就火了。
“这老太太,怎么回事!东西放坏了吃了要生病的,她不知道吗?”
那天晚饭,我特意多做了点菜,吃完饭,我守在客厅看电视,眼睛却一直瞟着厨房。
果不其然,等我们都回了房,我妈又摸进了厨房。
我跟过去,一把推开门,把她吓了一跳。
她手里正拿着一个装着几块排骨的保鲜袋,看我进来,慌得跟个孩子似的,赶紧往身后藏。
“妈,你干什么呢?”我压着火气问。
“没……没干啥,我看看还有没有碗没洗。”她眼神躲闪,不敢看我。
“你手里拿的什么?”我指着她身后。
我妈没办法,只好把那个油腻腻的袋子拿出来,低着头,小声说:“我看这排骨还多,扔了可惜……”
“可惜你就藏起来?藏起来干什么?等它发霉长毛了再看?”我声音一下就高了。
“不是的,不是的……”她急得直摆手,脸都憋红了,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你听我说,妈,”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缓和下来,“现在日子好了,不缺这口吃的。东西吃不完,放冰箱,第二天热热还能吃。你这样拿个塑料袋装着,天一热就馊了,吃了要拉肚子的,到时候去医院花钱更多,不是更浪费?”
我妈低着头,搓着围裙角,一声不吭。
那样子,让我心里又堵又软。
我知道她苦了一辈子,节俭惯了。
可我就是想不通,节俭也不是这么个节俭法啊。
那晚之后,我妈消停了几天。
可没过多久,故态复萌。
而且,她变得更“聪明”了。
她不再把剩菜藏在厨房的犄角旮旯,而是用好几个塑料袋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好,藏在她的房间里。
要不是小莉有次给她收拾房间,闻到一股若有若无的馊味,我们还被蒙在鼓里。
小莉把那个藏在床底下的袋子拎出来的时候,脸都绿了。
里面的菜已经有了酸味。
那天,小莉第一次跟我红了脸。
“张伟,你得管管你妈了!这不是节俭,这是毛病!家里搞得乌烟瘴气的,万一小宇不懂事,翻出来吃了怎么办?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了?”
我没法反驳,心里憋着一团无名火。
我冲进我妈的房间,她正坐在床边发呆。
“妈!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把那个馊掉的袋子扔在她面前,“你要是心疼东西,你就光明正大地放冰箱里!你要是不想让我们吃,你就自己吃掉!你这样偷偷摸摸藏起来,算怎么回事?你非得把家里搞得跟个垃圾堆一样才甘心吗?”
话说出口,我就后悔了。
我看见我妈的肩膀猛地一颤,她慢慢抬起头,眼睛里浑浊一片。
她没哭,也没辩解,只是看着我,嘴唇哆嗦着,半天,才说出一句话。
“小伟,妈……妈对不起你。”
那一刻,我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
我宁愿她跟我吵一架,也不想看她这个样子。
她一辈子要强,什么时候这么低声下气过。
我转过身,摔门出去,一拳砸在墙上。
小莉走过来,拉了拉我的胳膊,叹了口气:“你也别太凶了,她毕竟年纪大了。”
“我就是想不通!”我烦躁地抓着头发,“你说她图什么?她自己也舍不得吃,就这么藏着,等着坏掉。这不就是纯心跟我们过不去吗?”
小莉沉默了。
是啊,图什么呢?
这个问题,像一根刺,扎在我们一家人的心上。
从那以后,家里的气氛变得很奇怪。
我妈话更少了,吃饭的时候总是扒拉两口就说饱了,然后默默地回自己房间,把门关上。
她不再明目张胆地藏剩菜,但我们都知道,她还在继续。
只是藏得更隐蔽了。
有时候是一小包用报纸裹着的馒头,藏在阳台的旧花盆后面。
有时候是一小瓶我们喝剩的牛奶,塞在她衣柜最深处的旧衣服里。
我们发现一次,就悄悄处理一次,谁也不再提起。
我们就像在进行一场心照不`宣的拉锯战,她藏,我们找。
日子久了,我甚至有了一种荒谬的错觉,觉得我妈不是在藏剩饭,而是在藏一个巨大的、不能言说的秘密。
而这个秘密,沉甸甸的,压得我们所有人都喘不过气来。
我开始失眠,夜里常常睁着眼睛,听着我妈房间里传来的轻微响动。
我脑子里反复回响着她那句“妈对不起你”。
不,不对。
事情肯定没有那么简单。
我认识我妈一辈子,她是个倔强、要强,甚至有点固执的老太太,但她绝不是个无理取闹、专门给儿女添堵的人。
她做的每一件事,背后一定有她的道理。
只是这个道理,我们不懂。
我决定,要弄明白。
第二章 那个搪瓷碗
为了弄清我妈的秘密,我开始留意她的一举一动。
我发现,她每周三和周六的上午,都会雷打不动地出门。
她走的时候,总是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
那包不大,但每次出门前,她都会在房间里捣鼓很久,把包塞得鼓鼓囊囊的。
我问她去哪儿,她总是含糊其辞。
“去公园走走。”
“去跟老姐妹们说说话。”
可我知道她在撒谎。
因为有两次,我提前下班回家,看见她从外面回来,额头上都是汗,脚步虚浮,像是走了很远的路。
但她那个帆布包,却瘪了下去。
里面的东西,不见了。
我心里那个疙瘩,越结越大。
一个周六的早上,我借口单位加班,起了个大早。
我妈也跟往常一样,吃过早饭就开始在房间里忙活。
我躲在自己房间,从门缝里偷偷观察她。
只见她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小箱子,打开,从里面拿出几个塑料袋。
那些,正是她这几天“攒”下的“宝贝”。
有半只我们没吃完的烧鸡,几根香肠,还有几个白面馒头。
她把这些东西小心翼翼地装进帆布包,又从衣柜里拿出一个旧军用水壶,灌满了水。
做完这一切,她才蹑手蹑脚地走出家门。
我等了五分钟,然后悄悄跟了上去。
我妈年纪大了,腿脚不便,走得很慢。
她没有去附近的公园,而是径直走向了公交车站。
她上了一辆903路公交车。
那路车的终点站,在城市的另一头,一个我从未去过的、相当偏僻的郊区。
我开着车,不远不近地跟在公交车后面。
心里五味杂陈。
我不知道自己会发现什么,甚至有点害怕。
我怕发现的是一些我无法接受的真相,比如我妈是不是被什么人骗了,加入了什么奇怪的组织。
公交车摇摇晃晃,开了一个多小时。
窗外的景象,从高楼大厦,慢慢变成了低矮的平房和光秃秃的田野。
最后,公交车在一个叫“幸福里”的站台停下。
我妈下了车。
我把车停在远处,看着她瘦小的背影,在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
那条路的尽头,是一排灰扑扑的房子,墙皮斑驳,门口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木牌子。
离得太远,我看不清牌子上写的什么。
我看见我妈走到那排房子前,熟门熟路地推开一扇铁门,走了进去。
我把车熄了火,坐在车里,点了一根烟。
烟雾缭绕中,我的思绪回到了很多年前。
我想起了我的童年,想起了那个同样灰扑扑的、属于我们家的搪瓷碗。
那是我记事以来,我们家唯一的“奢侈品”。
碗口是蓝色的,碗身上印着一朵大红花,花瓣的边缘,有好几处磕掉的瓷,露出里面黑色的铁皮,像几块丑陋的伤疤。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那个碗,永远是满的。
不是满着饭,而是满着稀得能照出人影的玉米糊糊。
我们家兄妹三个,我最大,下面还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小兰。
小兰是老幺,生下来就体弱多病,像根豆芽菜,风一吹就要倒。
那时候,日子紧巴得像根拉直的绳子,稍微一用力,就断了。
我爸在村里的砖窑厂上班,挣的工分勉强够一家人糊口。
我妈就带着我们,在屋后开了块小小的菜地,种点青菜萝卜。
饶是如此,我们还是常年挨饿。
饿,是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
那种感觉,就像胃里有无数只小虫子在啃噬,火烧火燎的,让人坐立不安。
每天最盼望的,就是我妈端出那个搪瓷碗,给我们一人盛一勺玉米糊糊。
那碗糊糊,就是我们全部的能量来源。
可家里人多,粮食少,每个人都吃不饱。
我妈总是先把碗里的糊糊给我们兄妹三个分了,然后自己就着锅底刮下来的一点锅巴,喝口水,就算一顿。
我爸心疼她,总是把自己的那份匀给她一半。
她又把匀来的那份,偷偷倒回小兰的碗里。
小兰太小了,不懂事,端着比别人都满的碗,吃得咂巴作响。
我和弟弟就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拼命地咽口水。
有时候实在馋得不行,我就会趁我妈不注意,偷偷从妹妹碗里,用手指剜一小块糊糊,飞快地塞进嘴里。
那带着妹妹口水、甜丝丝的味道,我记了一辈子。
为了这事,我没少挨我妈的揍。
她会用纳鞋底的锥子,狠狠地扎我的手心,一边扎一边骂:“你是哥哥!你怎么能抢妹妹吃的!你妹妹身体不好,你要让着她!”
我疼得哇哇大哭,却不敢说自己饿。
因为我知道,我妈比我更饿。
我见过她半夜饿得睡不着,一个人坐在灶台前,就着月光,喝一肚子凉水。
那时候,我恨过我妈的偏心。
我觉得她不爱我,她只爱妹妹。
这种怨念,像一粒种子,在我心里扎了根。
直到那年冬天。
那年的雪下得特别大,封了山,我爸的砖窑厂也停了工。
家里的粮食,很快就见底了。
最后只剩下小半袋玉米面。
我妈把它做成糊糊,用那个搪瓷碗装着,郑重地放在桌子中央。
她对我们说:“这是我们家最后的粮食了。从今天起,这碗糊糊,只给小兰一个人吃。我们大人,喝水。等雪化了,爸去上工了,就有吃的了。”
我和弟弟虽然不情愿,但看着妹妹蜡黄的小脸,也都没敢出声。
那几天,是我们家最难熬的日子。
我和弟弟饿得前胸贴后背,整天躺在炕上,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
我爸默默地抽着旱烟,眉头拧成一个疙疙瘩瘩的铁疙瘩。
我妈则整天抱着小兰,把她裹在自己那件破棉袄里,一口一口地喂她喝糊糊。
小兰却好像知道家里的光景,每次都只喝一小口,就把头摇开。
我妈就哄她:“小兰乖,多吃点,吃了才有力气。”
小兰不说话,只是用她那双黑葡萄一样的大眼睛,看看我妈,又看看炕上躺着的我和弟弟。
第五天的时候,小兰开始发烧。
浑身滚烫,小脸烧得通红,说胡话。
我妈急疯了,抱着她就要往村里的卫生所跑。
可雪太大了,一脚踩下去,能没过膝盖,根本出不了门。
我爸想去找村里的赤脚医生,也被大雪堵了回来。
我妈就抱着小夜,坐在炕上,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她不停地用温水给小兰擦身子,嘴里一遍遍地念叨:“小兰,你快点好起来,等雪化了,妈给你做好吃的,给你炖鸡吃,给你吃肉……”
可小兰的烧,一直没退。
她越来越虚弱,连喝糊糊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妈就把糊糊含在自己嘴里,嚼碎了,再一点一点地渡到小兰嘴里。
可小t兰只是象征性地吞咽一下,大部分都从嘴角流了出来。
那天夜里,我被一阵压抑的哭声惊醒。
我睁开眼,看见我妈抱着小兰,坐在灶台前。
那个印着大红花的搪瓷碗,就放在旁边的灶台上,里面还剩着小半碗糊糊。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洒在我妈身上,她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
她没有嚎啕大哭,只是无声地流着泪,身体剧烈地颤抖着。
怀里的小兰,一动不动。
我当时年纪小,还不完全明白死亡意味着什么。
我只知道,我再也见不到那个会把自己的糊糊分给我吃的妹妹了。
我只知道,我妈的心,跟着小兰一起,死了。
小兰走后,那个搪瓷碗,就被我妈收了起来。
很多年,我都没再见过它。
家里的日子,后来慢慢好起来了。
我和弟弟都长大了,考上了大学,离开了那个贫穷的小山村。
再后来,我结了婚,生了小宇,在城里安了家。
我把父母也接了过来。
我以为,过去的苦难,都过去了。
我以为,我妈已经忘了那些伤痛。
可现在我才明白,有些伤疤,刻在骨头上,一辈子都好不了。
一根烟抽完,我的眼角有些湿润。
我推开车门,朝着那排灰扑扑的房子走去。
门口那块木牌子,在风中轻轻摇晃着,上面的字迹已经斑驳,但我还是看清了。
“阳光孤儿院”。
我的心,猛地一沉。
第三章 阳光下的影子
我没有立刻进去。
我绕到孤儿院的侧面,那里有一堵半人高的围墙,墙上爬满了干枯的藤蔓。
我找了个豁口,悄悄探出头往里看。
院子不大,水泥地坪上画着几个跳房子的格子,旁边是一个锈迹斑斑的滑梯和两个秋千。
几个穿着旧衣服的孩子在院子里追逐打闹,笑声清脆,像春天刚解冻的小溪。
一个中年妇女,大概是孤儿院的院长或者工作人员,正站在一旁,笑着看他们玩。
而我的母亲,赵淑珍女士,正坐在滑梯下的一个小马扎上。
她背对着我,背影佝偻,比在家里时更显瘦小。
她从那个熟悉的帆布包里,一样一样地往外掏东西。
那半只烧鸡,那几根香肠,还有那几个白面馒头。
她把这些东西放在一张小桌子上,然后又掏出一个小小的、不锈钢的饭盒。
我认得那个饭盒,是小宇小时候用过的,上面还贴着一张奥特曼的贴纸。
她打开饭盒,一股热气冒了出来。
我猜想,里面是她早上特意煮的什么。
她忙活完这一切,就坐在那里,静静地等着。
不一会儿,从屋里跑出来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大概五六岁的样子。
小女孩跑到我妈面前,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张奶奶。”
我妈的脸上,立刻绽开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无比温柔的笑容。
那笑容,就像冬日里最暖的阳光,瞬间融化了她脸上所有的皱纹和沧桑。
“萍萍来啦,”我妈的声音,是我从未听过的轻快,“快来,看看奶奶今天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
她拉着那个叫萍萍的小女孩坐下,把那半只烧鸡撕成一小块一小块,把香肠切成一片一片,整整齐齐地码在盘子里。
然后,她打开那个奥特曼饭盒,用勺子舀出一勺,吹了吹,小心翼翼地喂到萍萍嘴边。
“慢点吃,别烫着。”
萍萍很乖,张开小嘴,把饭吃了进去,然后满足地眯起了眼睛。
“好吃吗?”我妈问。
萍萍用力地点点头:“好吃,奶奶做的最好吃。”
我妈笑了,眼角的皱纹里,都盛满了笑意。
她就那样,一口一口地喂着萍萍,眼神专注而慈爱。
那眼神,我太熟悉了。
三十多年前,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她就是用同样的眼神,看着怀里奄奄一息的小兰。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攥住了。
疼得我几乎无法呼吸。
我终于明白了。
我什么都明白了。
她不是在藏剩饭,她是在为这个叫萍萍的孩子,攒下我们全家最好的口粮。
她不是有病,她只是想把当年欠小兰的,那份未能说出口的爱,那份未能完成的承诺,补偿给另一个同样弱小的生命。
她当年对小兰说:“等雪化了,妈给你炖鸡吃,给你吃肉……”
雪化了,日子好了。
可是小兰,却永远地留在了那个冬天。
这成了她一辈子的心结,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而这个叫萍萍的女孩,就是她为自己找到的一剂良药。
我看着萍萍的侧脸,那瘦弱的肩膀,那怯生生的眼神,像,真像当年的小兰。
难怪,难怪我妈会对她这么好。
她不是在喂养一个孤儿,她是在喂养三十多年前,那个在饥饿和寒冷中逝去的、自己的女儿。
院子里的孩子们,闻到了肉香,都围了过来,眼巴巴地看着桌上的食物。
我妈把烧鸡和香肠分给他们,每个孩子都分到了一小块。
孩子们欢呼着,狼吞虎咽地吃着。
我妈看着他们,脸上的笑容更深了。
只有那个奥特曼饭盒里的东西,她没有分。
那是专门留给萍萍的。
我看到萍萍把饭盒里最后一口饭吃完,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勺子。
我妈就用手,轻轻地摸了摸她的头,柔声说:“萍萍乖,下个星期三,奶奶还给你带好吃的来。”
萍萍重重地点了点头。
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了。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滚而下。
我蹲下身,把脸埋在臂弯里,肩膀剧烈地抽动着。
我哭的,不仅仅是我那可怜的、早夭的妹妹。
我哭的,也不仅仅是我那苦了一辈子、把所有伤痛都埋在心里的母亲。
我哭的,是我自己。
我的愚蠢,我的自私,我的麻木。
我以为我给了她富足的生活,就尽到了一个儿子的孝心。
我抱怨她的“坏习惯”,指责她的“不可理喻”,却从未想过去探究她内心深处,那道血淋淋的伤口。
我只看到了灶台上那些变味的剩饭,却没看到她藏在剩饭背后,那颗破碎的、渴望弥补和救赎的心。
我这个儿子,当得太不称职了。
我就那样在墙角下,蹲了很久很久。
直到院子里的孩子们都回了屋,直到我妈收拾好东西,蹒跚着走出铁门。
我才擦干眼泪,站起身。
我没有上前去叫她。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不起?
这三个字,太轻太轻了,根本无法承载我此刻心中万分之一的悔恨和愧疚。
我只是默默地发动了车子,像来时一样,远远地跟在她乘坐的那辆903路公交车后面。
车窗外,阳光明媚。
可我却觉得,我的母亲,就像一个走在阳光下的影子。
她把所有的温暖和光明,都给了别人。
留给自己的,只有一道孤单、落寞的背影。
而我,作为她唯一的儿子,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亲手为她的影子,又添上了一抹浓重的黑暗。
回到家,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小莉敲门进来,看到一屋子的烟雾,皱了皱眉。
“怎么了?不是去加班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还抽这么多烟。”
我掐灭烟头,看着她,沙哑着嗓子说:“小莉,我错了。”
小莉愣住了,不明所以地看着我。
我把今天看到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
从我妈偷偷出门,到我跟踪她去孤儿院,再到她喂那个叫萍萍的小女孩吃饭。
我说得很慢,很艰难,说到最后,声音又哽咽了。
小莉静静地听着,眼圈也慢慢红了。
等我说完,她走过来,从背后抱住我,把头靠在我的背上。
“老张,别难过了,”她的声音也带着哭腔,“这不怪你,我们都不知道……”
“不,怪我。”我摇着头,“我明明知道她以前受过多少苦,我明明知道小兰是她一辈子的痛,可我从来没想过,这道痛,会以这样的方式,延续到现在。”
我们俩就那样抱着,沉默了很久。
书房里,只剩下彼此的呼吸声,和窗外传来的、遥远的市声。
良久,小莉才开口,她说:“老张,那我们以后……该怎么办?”
是啊,该怎么办?
直接戳穿她,告诉她我们都知道了?
不,不行。
以我妈的性子,她会觉得给我们添了天大的麻烦,会觉得没脸再待在这个家里。
她那点可怜的、用来自我救赎的寄托,会被我们无情地打碎。
那会比杀了她还难受。
继续假装不知道,任由她继续偷偷摸摸地藏剩饭?
也不行。
我不能再让她吃那些可能变质的东西,更不能再让她为了省下一点肉,自己整天只吃青菜豆腐。
我想了很久,直到窗外的天色,一点点暗下来。
我对我媳妇说:“小莉,我有办法了。”
第四章 一场“偶遇”
我的办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演一场戏。
一场精心设计的,“偶遇”。
接下来的几天,我开始做准备。
我先是托关系,打听了一下那家“阳光孤儿院”的情况。
那是一家民办的孤儿院,规模很小,资金紧张,主要靠社会上一些好心人的捐助维持。
院长姓李,就是我那天在院子里看到的那个中年妇女。
她是个很了不起的女人,早年丧偶,没有子女,退休后就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办了这家孤儿院,收养了十几个无家可归的孩子。
我还了解到,那个叫萍萍的小女孩,是三年前被遗弃在孤儿院门口的,有先天性的心脏病,所以一直没有人愿意领养。
我妈,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始“光顾”这家孤儿院的。
知道了这些,我心里更有数了。
周三那天,我特意请了一天假。
早上,我妈又像往常一样,背着她那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出门了。
我等她走了以后,对小莉说:“行动开始。”
小莉点点头,给了我一个“加油”的眼神。
我开着车,先去了一趟超市。
我买了一后备箱的东西。
新鲜的排骨、牛肉、大袋的苹果和香蕉、成箱的牛奶、还有各种各样小孩子爱吃的零食。
然后,我开车直奔“幸福里”。
我没有直接去孤儿院,而是把车停在了那条土路的路口,等着。
大概十点半左右,我远远地看见我妈的身影,出现在路的另一头。
她走得很慢,背着那个帆布包,在冬日的阳光下,像一个移动的、小小的黑点。
我深吸一口气,发动车子,迎了上去。
我在离她还有二十米的地方停下,摇下车窗,装作一副刚看到她的、无比惊讶的样子。
“妈!你怎么在这儿?”
我妈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搞蒙了。
她愣在原地,看着我,张了张嘴,半天没说出话来。
“你……小伟,你不是上班去了吗?”
“我今天出来办点事,正好路过。你呢?你来这儿干嘛?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一边说,一边下了车,朝她走去。
我妈的眼神开始慌乱起来,她下意识地把那个帆布包往身后挪了挪。
“我……我来找个老姐妹,她就住这附近。”
“老姐妹?哪个老姐妹?我怎么没听你说过?”我故作好奇地追问。
“就是……就是以前一个村的,你不知道。”她说话已经有些语无伦次。
我走到她面前,看着她那张写满了紧张和不安的脸,心里一阵酸楚。
我没有再逼问她,而是指了指路的那头,说:“行啊,那你去吧。我正好也去前面办点事,顺便把你那个老姐妹也接上,中午咱们一起在外面吃个饭。”
“别别别!”我妈急了,“不用不用,我们说说话就回去了,不吃饭。”
“那怎么行,大老远来一趟。走,我送你过去。”我说着,就去搀她的胳膊。
我妈死活不肯走,僵持在那里。
我知道,火候差不多了。
我叹了口气,放开她,装作不经意地往孤儿院的方向看了一眼。
“咦?那是什么地方?‘阳光孤儿院’?这里还有个孤儿院啊。”
我妈的身体,明显地僵硬了一下。
“走,过去看看。”我拉着她,不容分说地就往孤去。
我妈被我拽着,踉踉跄跄地跟着,嘴里还在徒劳地辩解:“有啥好看的,一个破院子……”
我没理她,径直走到了孤儿院的铁门前。
这时候,李院长正好从里面走出来,看到我们,愣了一下。
我立刻堆起笑脸,迎了上去。
“您好,请问您是这里的院长吗?”
李院长点点头:“是啊,你们是?”
“哦,我们是路过的,看到这里有个孤儿院,就想过来看看。我姓张,这是我母亲。”我把我妈往前推了推。
我妈低着头,脸涨得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李院长的目光落在我妈身上,立刻就笑了:“哎呀,是张奶奶来了!快请进,快请进!”
她热情地拉着我妈的手,又对我说:“张先生,你可有个好母亲啊。张奶奶是我们这里的常客了,风雨无阻,每周都来看孩子们,给他们带好多好吃的。孩子们都可喜欢她了。”
我故作惊讶地“啊”了一声,转头看着我妈:“妈,原来你说的老姐妹,就是这些孩子们啊?”
我妈的头埋得更低了,攥着帆布包的带子,手指都发白了。
我心里叹息,知道不能再逼她了。
我对李院长说:“院长,我们能进去看看孩子们吗?我车上带了点东西,想给孩子们。”
“那太好了!太感谢了!”李院长激动得连连道谢。
我打开后备箱,把那些大包小包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搬下来。
李院长和几个大一点的孩子都过来帮忙。
我妈站在一旁,看着那些新鲜的肉、水果和牛奶,眼神复杂,像是不知所措。
进了院子,我看到了那个叫萍萍的小女孩。
她正一个人坐在滑梯下面,看到我妈,眼睛一亮,跑了过来。
“张奶奶!”
她跑到我妈跟前,却又看到了我这个陌生人,怯生生地停住了脚步。
我妈下意识地把她拉到自己身后,护着她。
那个动作,像一只老母鸡,护着自己最宝贵的小鸡仔。
我蹲下身,尽量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和蔼可亲。
“你就是萍萍吧?你好,我是张奶奶的儿子,你可以叫我张叔叔。”
萍萍躲在我妈身后,探出个小脑袋,好奇地打量着我。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早就准备好的、崭新的奥特曼玩具,递给她。
“送给你的。”
萍萍看了看玩具,又看了看我妈。
我妈犹豫了一下,对我投来一个询问的眼神。
我冲她点点头,笑了笑。
她这才对萍萍说:“萍萍,叔叔给你的,快谢谢叔叔。”
萍萍小心翼翼地接过玩具,小声说:“谢谢张叔叔。”
那天中午,我们没有走。
李院长非要留我们吃饭。
厨房里,我妈坚持要亲自动手。
她把我买来的新鲜排骨,炖了一大锅。
又把牛肉切了,炒了两个菜。
她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那么熟练,那么自然,仿佛她天生就该属于这里。
吃饭的时候,几十个孩子围着几张破旧的桌子,坐得满满当当。
我妈把最大的一块排骨,夹到了萍萍的碗里。
萍萍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妈,然后用她的小勺子,把那块排骨,笨拙地分成了两半,把其中一半,放到了我妈的碗里。
“奶奶,你也吃。”她奶声奶气地说。
我妈愣住了。
她看着碗里那半块沾着米粒的排骨,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她低下头,用极低的声音,说了一句:“哎,好孩子。”
然后,她夹起那块排骨,慢慢地,放进了嘴里。
我看到,有两行浑浊的泪,从她布满皱纹的脸上,滑落下来,滴进了饭碗里。
我别过头,再也看不下去。
那顿饭,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百感交集的一顿饭。
第五章 不再躲藏的爱
从孤儿院回来,我妈一路上都没说话。
她只是抱着那个已经空了的帆布包,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物,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也没有开口。
我知道,有些事情,不需要说破。
沉默,是最好的尊重。
回到家,小莉已经做好了晚饭。
看到我们一起回来,她也装作很惊讶的样子:“哎呀,爸今天怎么跟儿子一起回来了?加班结束了?”
我妈看了我一眼,没说话,默默地回了自己房间。
晚饭的时候,气氛有些沉闷。
我妈还是跟以前一样,低头扒拉着碗里的饭。
小莉给她夹了一筷子鱼,说:“妈,多吃点,今天这鱼新鲜。”
我妈顿了顿,抬头看了看小莉,又看了看我,然后,默默地把那块鱼,吃了下去。
就在那一刻,我知道,我们家那场持续了大半年的、心照不`宣的拉锯战,结束了。
第二天,我妈没有再偷偷藏剩饭。
吃不完的菜,她会主动拿上保鲜膜,盖好,放进冰箱。
周末,小莉去超市,特意多买了很多菜。
她对我妈说:“妈,冰箱里东西太多了,下周我和老张都要出差,小宇要去奶奶家住几天,这些东西放着就坏了,要不……您看怎么处理一下?”
我妈愣愣地看着小莉,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
小莉把一个大购物袋塞到她手里,笑着说:“妈,您看着办吧,扔了怪可惜的。”
我妈拎着那个沉甸甸的袋子,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然后,她点点头,说了声:“好。”
下一个周三,我妈又出门了。
这一次,她没有再背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
而是拎着小莉给她的那个,印着超市LOGO的大购物袋。
她的脚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轻快和坦然。
从那以后,我们家形成了一种新的默契。
每周,小莉都会“有意”地买多一些食物。
而我妈,则会“理直气壮”地,把这些“吃不完”的东西,带去孤儿院。
她不再偷偷摸摸,我们也不再假装不知。
那个曾经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压抑的秘密,变成了一件全家人共同参与的、温暖的善举。
我妈的话,也渐渐多了起来。
她会跟我们聊起孤儿院的孩子们。
她说,那个叫小东的男孩最调皮,上次把李院长的眼镜藏了起来。
她说,那个叫小雅的女孩最爱美,总喜欢把野花插在头上。
说起这些的时候,她的眼睛里,有光。
而说得最多的,还是萍萍。
“萍萍那孩子,真懂事,就是身体太弱了,天一冷就咳嗽。”
“萍萍喜欢画画,上次还画了我,画得可像了。”
“萍萍说,她长大了,想当个医生,给所有生病的小朋友看病。”
每当这时,我和小莉都会静静地听着,时不时地附和几句。
我们谁也没有提过小兰。
但我们都知道,我妈口中的萍萍,其实就是另一个时空里,健康长大了的小兰。
她通过萍萍,看到了女儿本该拥有的,那个五彩斑斓的人生。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年底。
我拿到了单位发的年终奖,我跟小莉商量,想拿出一部分钱,给萍萍做手术。
我咨询了医生,萍萍的先天性心脏病,虽然麻烦,但并不是绝症,只要手术成功,她就能像个正常的孩子一样生活。
小莉没有丝毫犹豫就同意了。
她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把这个决定,告诉了我妈。
那天,我们一家三口,第一次和我妈,进行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谈话。
我把我早就查好的医院、医生资料拿给她看。
我对她说:“妈,我们想,把萍萍的病治好。钱我们来出,就当是……就当是替小兰,做点事。”
我说出“小兰”那两个字的时候,心都揪紧了。
我妈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她看着我,看着那些资料,眼泪,又一次无声地流了下来。
这一次,她没有压抑。
她捂着脸,放声大哭。
哭得像个孩子。
那是积压了三十多年的,思念、悔恨、痛苦和释然。
我和小莉坐在她身边,轻轻地拍着她的背。
我们知道,从这一刻起,那个禁锢了她半生的枷锁,终于被打开了。
那个寒冷的冬天,终于过去了。
萍萍的手术,安排在了第二年春天。
手术很成功。
我们在医院陪了她一个多月。
那一个月,是我妈这几年来,最开心的日子。
她每天给萍萍炖各种有营养的汤,给她讲故事,教她认字。
萍萍出院那天,阳光灿烂。
李院长带着孤儿院所有的孩子都来了。
萍萍穿着我们给她买的新裙子,脸上是健康的红晕,她扑进我妈的怀里,大声地叫着:“奶奶!”
我妈抱着她,笑了。
那笑容,是我从未见过的,发自内心的,灿烂的笑。
后来,我们全家都成了“阳光孤儿院”的常客。
我每个月会从工资里拿出一部分钱,定期捐助孤儿院。
小莉一有空,就去教孩子们画画、唱歌。
我的儿子小宇,也把他的玩具和零花钱,都分享给了那些弟弟妹妹。
而我妈,依旧是那里的“张奶奶”。
她不再带剩饭去了。
而是每周都列好单子,让我去买最新鲜的食材,然后她在孤儿院的厨房里,给孩子们做一顿丰盛的大餐。
去年,萍萍被一对善良的夫妇领养了。
他们是我的同事,知道萍萍的故事后,非常感动。
离开那天,萍萍哭得很伤心。
她抱着我妈,说:“奶奶,我以后还能来看你吗?”
我妈摸着她的头,笑着说:“傻孩子,当然能。你以后,就有自己的爸爸妈妈了,要听话。”
送走萍萍,回家的路上,我妈显得有些失落。
我安慰她:“妈,这是好事,萍萍有家了。”
我妈点点头,看着窗外,轻声说:“是啊,有家了,真好。”
我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
她想起了小兰,那个永远没能拥有一个完整童年的女儿。
但她的眼神里,没有了以往的悲伤,更多的是一种欣慰和安宁。
萍萍的圆满,终究是抚平了她心中最大的遗憾。
前几天,是我妈七十岁的生日。
我们没有在外面订酒店,就在家里,一家人,简简单单地吃了个饭。
萍萍和她的新爸妈也来了,给她带来了生日礼物。
小宇用他攒了一年的零花钱,给我妈买了一个金手镯。
我妈戴在手上,嘴上说着“浪费钱”,眼睛却笑成了一条缝。
饭后,我们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我妈靠在沙发上,拉着萍萍的手,看着电视里热闹的节目,脸上一直挂着笑。
小宇靠在她另一边,给她讲着学校里的趣事。
小莉在厨房里切着水果。
我看着眼前这幅景象,心里暖洋洋的。
我想起多年前,那个在墙角下,看着母亲背影痛哭流涕的自己。
我想起那碗曾经让我无比困惑和烦躁的剩饭。
原来,那碗剩饭里,藏着的不是馊掉的菜,而是一个母亲,对逝去女儿最深沉的思念,和对另一个生命的、最无私的爱。
这份爱,曾经因为误解而显得那么沉重和晦涩。
而现在,它终于在阳光下,绽放出了最温暖的光芒,照亮了我们整个家。
我看着母亲的笑,那笑容,比我见过的所有阳光,都暖和。
文档上传者
热门标签
相关文档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