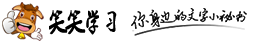欢迎来到98聘
推荐《等你回家作文》相关写作范文范例(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12-20 23:41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等你回家”的作文,可以非常动人。以下是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可以帮助你写出一篇情感真挚、结构清晰的文章:
"一、 确定核心情感和主题:"
1. "明确“等待”的对象和原因:" 是等待远行的亲人(父母、孩子、爱人)?是等待一个重要的归来?还是等待一种状态的恢复(比如战争结束)?清晰地定义你等待的是谁,为什么等待。 2. "聚焦核心情感:" “等你回家”的核心情感是什么?是思念、牵挂、期盼、爱、不舍、孤独,还是对未来的憧憬?抓住最触动你的那一点,作为文章的情感主线。 3. "确立文章主题:" 你想通过这篇文章表达什么?是歌颂亲情/爱情的伟大,是描绘等待中的生活细节,是表达对未来的期盼,还是反思旅人的不易?一个清晰的主题能让文章更有深度。
"二、 构思文章结构和内容:"
1. "选择合适的叙事视角:" 通常采用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这样更能直接抒发内心的情感,让读者产生共鸣。也可以尝试第三人称,但要注意代入感。 2. "设计引人入胜的开头:" 可以直接点题,描写一个等待的场景。 可以从回忆入手,讲述等待的原因。 可以设置一个悬念或细节,引发
我把三十五岁的大龄剩女撵出了家门,等端正了态度再回来。
那天我把她的行李箱一脚踢到门口,滚轮哗啦啦地撞到墙,灯影斜着,像给这事打了一道生硬的字幕。
我说,三十五了,还这么拧,端正了态度再回来。
她那一瞬间没有哭,也没有吼,她只是低头把鞋子换好,把钥匙从那个带小熊挂件的钥匙圈上拆下来,放在鞋柜上,手指头抖了一下。
她看我一眼,眼底的东西像是把冬天打碎了,说了一句,“剩下的不是我,是你那一套旧观念。”
我嘴巴一硬,想说再响一点的狠话,可那口气就卡在喉结后面,像夹到了骨头。
周美华从厨房里出来,手上还带着洗碗的泡沫,盯着我,想说什么,最终把眼神垂下去,去捡那只翻倒的酱油瓶。
她拎着箱子走了,夜风一阵一阵,楼道里有个孩子在上楼跑,鞋底拍得很响,像给她的背影打节拍。
我把门关上,门缝里挤出来一条偏执的冷气,我站在门背后,手掌贴着木头,听见她拖箱子的声音越来越轻,直到电梯叮的一下。
我那句“端正态度再回来”在屋子里来回撞,撞到了旧沙发的塌陷处,撞到了我们那只不响的挂钟,最后落在了我的鞋边。
她叫李苒,三十五,纠结的、好看得不招人喜欢的那种,脸上总有一条小小的反骨,笑起来自带防备。
我们就是那种破旧的家庭,旧城边上两室一厅,厨房小到要一边煮面一边侧身,煤气灶的火总是蜷着,像不愿意好好工作的人。
她这次回来,是被裁了,或者说被“优化”,她不肯用他们公司那套词,她说,除了我妈,谁都没有资格给她贴标签。
我那天在饭桌上找她的毛病,话像筷子,敲敲盘子就冒出来。
我说,你看你姑家的丫头,二十八生了娃,你呢。
我说,我开车接了个客人,人家说女儿在深圳当老师,有房有车,你呢。
她把碗里的青菜夹到我碗里,说,吃菜。
她说得很慢,像每一个字都要自己给自己打气。
周美华踢了我一下,没踢重,像蚊子叮,我没当回事。
她给我妈买的血糖仪还没开封,她在说明书上画了红圈,写了“早晚”。
她被撵出去之后,屋子里就只剩下这台血糖仪和她写给我妈的字。
第二天我起得早,四点半起身去车库,冬天车玻璃内外都是白雾,我的手指在玻璃上画了一个圈,像给自己开了个小窗。
我把车发动,暖风慢慢起来,我捏了捏手,指节干干的,有两处裂了口,像嘴角。
五点半我拉到第一个客人,是个穿得很干净的青年,一路上捧着个保温杯,喝着淡得像白水的茶。
他说他要去火车站,去外地出差,我点点头。
他问我家里几个孩子,我说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那儿子还在外地读书。
他说,那挺好。
我说,女儿三十五了,还没婚事,回来也不消停,脾气也怪。
他说,你这话不地道。
我愣了一下,笑笑,没接。
青年拿起手机又放下,车窗外工地的红旗在风里直直地立着,一点也不动。
回家的时候太阳刚升起来,楼下那个卖包子的大叔把蒸笼盖揭开,热气冲起来,像把早晨堵成了一个白色的球。
周美华把面摊摆出来,小炉子烧水哒哒哒响,锅边的汤泡泡像在笑,我在旁边整理筷子,看见她手上的碗有一道小缺口。
她不说话,我更不说,我就把筷子分开,红的给顾客,黑的留自己用,这种小规矩不知从哪年来的,弄着弄着就跟着日子生根了。
十点多我把车停去保养,坐在走廊塑料椅上等,电话叮一下,是我妹发的消息。
她说,昨晚你是真撵她走啊。
她说,哥,你这嘴,有时候跟锄头一样,挖到自己脚背上。
我想回她,回了删,又打另一个又删,最后发了一个“嗯”。
换完油回来,屋里静得像被什么吃掉了,我打了个喷嚏,回荡着,像在空屋里开了个会。
她没有发任何消息,周美华把那台血糖仪拆了,试了一下自己的手,滴了一滴血,她皱眉,把数据写在一个小本上。
小本子是她一直记的,买菜花了多少,谁来吃过饭,谁欠了五块一直没还,像在给我们这个家做一本不完美的账。
下午我去楼下的麻将馆坐了一会儿,抽烟的人多,烟雾绕着灯光打圈,几张牌啪一声拍桌上,像拆封了某种被时间压住的皮。
老许在那,我跟他打招呼,他看见我,笑得像有个秘密。
他说,听说了啊,女儿让你撵走了。
我说,你哪来这么快的消息。
他说,楼上的王姐撞见了,晚上在群里说了两句。
我心里一惊,问他哪个群,他说,他们那个“幸福小区群”,我突然想把手机砸了,再把群里的人一个一个拎出来,问他们到底幸福了谁。
老许说,唉,你这老思想,改改吧。
我说,我没老思想,我就是不喜欢她那种眼神,什么都带着一把刀,像我欠了她。
老许挠挠头,说,欠不欠你自己心里清楚吧。
回到家我敲了敲门,周美华在里面斜靠着沙发,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小。
她说,你给她打电话吧。
我说,我的电话也没那么容易打。
她淡淡看我一眼,鼻子呼吸很稳定,像平衡木上练出来的。
晚上我又出车,拉了一个去医院看病的老大爷,他在后座咳嗽两声,纸巾拿出来捂着,拍我肩说,师傅,辛苦啊。
我说,不辛苦。
老大爷说,他孙女三十七了也没嫁,他媳妇每天在家里念叨,念叨到自己都快失眠了。
我在后视镜里看他一眼,他的眼皮有一条老年斑,像一道松弛的墨迹。
他说,后来他媳妇倒下了,心脏不行,孙女跑前跑后,把老老太太抱上抱下,谁家女儿干活能做到这份上。
我嗯了一声,还想再听点,他已经开始说医院通讯室的排队队伍有多长。
车里微气温有点上来,玻璃上开始出水珠,我纸巾擦了一圈又一圈,手背上有点疼。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该说点什么,嘴巴开开合合,最后又闭上了。
那晚我停在路边吃了一碗羊杂,汤油亮亮地飘着,肉挺好嚼,我吃了一半就不想吃了,心里像放了一个石头,汤的油都绕着它转。
回到家已经十一点,周美华睡了,她把那台血糖仪放在我们床头边,像刻意提示我这个家的稳定还在。
我关了灯躺下,窗外有人吹口哨,一阵一阵,我突然想起她小时候第一次带回家作文,题目叫《我的城市》,四年级写这个,我觉得废话,她却写得像我们那条路上的白狗,描得细。
她那篇作文我还留着,封皮都黄了,她笔迹清清楚楚,字像人站得直直的,挺。
我当年看了只说了句“嗯”,没有具体夸,也没具体骂,就这样一直都没有具体。
隔了几天,她还是没消息,我却开始收到一些奇怪的东西。
一个快递,里面是一台新的电饭锅,写到件人叫“——”。
另一个快递,是几包酵母和面粉,还有一个小卡片,上面划拉了一句,“可以试试自己做面包,给妈。”
周美华拿着卡片看了很久,没说,她把面粉密封好,贴了标签,像给这个卡片找了个具体的家。
我假装不知道是谁寄的,那个破烂心眼以为自己很聪明,心里其实五味子一样乱。
我在车上把这事想了又想,越想越像把自己绕进了个圈,一圈再一圈,圈的中心空空的,就一个人站那儿。
我终于去她以前的公司门口看了一眼。
那是一个新做出来的产业园,外墙是玻璃和金属,银光亮亮,门口种了三棵樱花,在冬季站那儿像三个等候的人。
我没进去,我坐在外面台阶上抽了根烟,看了看大厅里来去的年轻人,裤子都是一种尖锐的浅色,鞋子都是新买的白。
我突然明白她说的那句,“我白天站在那里,晚上躺下来,还在站在那里。”
她以前的同事从门里出来,一个男孩,戴眼镜,眼镜片上一圈油光,像在厨房里切了葱没洗手就碰了镜片。
我叫住他,问他认识李苒吗,他看我几眼,警觉,之后说,认识。
他说,你是她爸吧。
我说,是。
他说,她去年就走了,那时候他们部门换负责人,新上来的那位特别喜欢搞那套“年轻化的团队”,李苒被他打了几次绩效,找她谈话的那种谈话,像做学前教育,问你“未来期待”,弄得烦。
我咬着烟屁股,让烟味猛烈一点,压住什么不适,那男孩揉了揉鼻子,说了一句,“她真不是不好,我知道你们一代人不太懂。”
他说完这句跑了,像被谁追,那种羞怯的跑让我觉得他其实也过得不咋样。
我在台阶坐了半小时,心里往下掉,掉到一个冷里,冷在脚心里发起,传到胃。
回去的路上,我去菜市场买了两条鱼,老板问我做红烧还是清蒸,我说做清蒸吧,不油。
鱼抱在塑料袋里,尾巴拍着袋子啪啪的响,我突然觉得这个声音和她拖箱子的声音一样。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说了一句,“给她打个电话吧。”
周美华很平静地看我,我说的是“她”,没有说名字,她知道我这个嘴,就是这么绕。
她说,好。
她拿起来电话,翻了翻,停住,最后拨了一个号码,很快就接通了。
她说,苒啊,你在做什么。
电话那头应该在走路,风声很直,像沿着一个窄窄的街。
她说,妈,我在看房。
我和周美华都“啊”了一下,那个“啊”是想让对方觉得自己随和,实际上外壳下面是一背硬。
周美华说,怎么看房啊,又要租啊。
她笑了一下,笑声很淡,像水里一滴油,漂着。
她说,租啊,不然住树上吗。
我突然想说那句“你可以回来住”,但我的嗓子像被木块堵住了,我在桌面上敲了敲,冒出来一个微弱的声音,“回来吧。”
她沉默了两秒,说,等我这边忙完吧。
挂了电话,我去阳台站了一会儿,夜里那几盏广告牌的光在空中压了一层亮,我的心跳跟着它们节奏,乱。
接下来一周她没再联系,我把车开得越来越远,一路开到河边,开到那个新的桥下,桥身上贴着安全提示,字像紧紧握住的拳头。
桥下有人钓鱼,拿着一罐方便面的空罐装蚯蚓,我看了他们五分钟,没看出鱼上来,我的心却像被钩住,往那地方挪。
我不想承认,我把她撵出家门这个事,挺像我自己往外踢了自己一脚。
我那句“端正态度再回来”,像一个被我挂在门口的牌子,牌子上落灰了,风吹得它打我的脸。
某一天早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医院打来的,说我妈的常规检查有几个数据不稳,让家属过来。
我妈住得并不远,和我们隔着一个街区,她从不愿意变成别人家里那种被放在某个地方的存在,她得自己有一个地方。
我把车停在医院门口,拎着她的小包进去了,她在走廊坐着,手里握着那本小笔记,本子角已经卷起来了。
她说,她没事,就是医生说血压有一点波动,叫人看看。
我说,我来啊。
她笑了一下,笑里有一个不轻不重的自得,像去菜市场砍到了便宜。
她说,苒前天陪我去过,她给我买了一个小巧的保温杯,水不漏,她拿在手里出门像捧着一个保险。
我愣住了,各种东西在我的脑子里挠,在我的胸腔里踢。
我妈不看我,她把笔记翻到一页,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她说,这是苒的房东,她让房东把地址给我,说她租到一个靠地铁的。
我把那个电话又抄了一遍,抄得慢,像在抄自己的名字。
我给那个房东打了电话,房东声音是一个中年女人,说话有一点理,像做行政的,语速不快。
她说,李苒租的是一个老房子的次卧,一千八,房东家里有个儿子在读书,房子里各种杂物多,厨房有个老油烟机,总是嗡。
她说,李苒人很规矩,周末会给房东婆婆买菜,偶尔还帮他们做点文书。
我说谢谢,她说不用,她说她看惯了租客里各种的人,像看水里的鱼,总有一条让人心里一动。
我挂了电话,站在医院门口,冷风一下子把我的外套掀起一角,我伸手按住,手背有点发红。
我突然想给她打电话。
我点开她,这么小小的一个名字,躲在我的通讯录里像一个不敢被碰的东西,我按下拨出,声音很快有了回响。
她说,爸。
她叫我,我就不想再把话说得像锤子。
我说,我在医院,医生说我妈血压有点高。
她说,我知道,我前天去过,医生还让你少抽烟。
我说,嗯。
我想说其他,她在那头走路,脚步带着一个细碎的节奏,像小时候她在家里练跳绳的声音。
我说,找到了房子啊。
她说,找到了。
我说,租金贵不贵。
她说,还行。
我说,我会转你钱。
她说,不用。
她说,爸,我不缺钱。
我嘴里“啊”了一声,其实心里一点也“啊”不出来。
她说,爸,你其实不愿意听我的话,你只是想让我像个牌子立在那里,给你看着舒服。
她说得慢,但每一个字轧进我的骨头里,咔嚓响一声。
我说,不是。
她说,是。
她说,我三十五了,我不是一个站在门口等你指挥的小孩了,我也不是一个用来给你在麻将馆吹牛的人。
我说,我没有吹牛。
她笑了一下,她那个笑里有苦,有那种怕人看出来的羞,像把亮光一把拢住,不给别人。
她说,你可以爱我,但别用你爱你自己的方式爱我。
我说,我只是想好好过。
她说,我也是。
她挂了,我站在医院门口,手机屏幕反着我的脸,像给我照了一个毫不留情的样子。
我那天没再去拉活,我回家,坐在我们家小桌前,把那本账本翻了一页一页,找以前她给我们买东西的记录,找到一条条,我像在对着她的名字去认一种从来没有认真想过的绳结。
三年前她给我们交了那一次补充医疗保险,写在账本左下角,一行字干净利落,我觉得自己在一个糙的世界里突然看见了一个细。
晚上有人敲门,我开,门口站的是邻居秦姐,她手里拿着一个刚蒸出来的南瓜饼,她的鼻子有一个小黑点,我礼貌地没看太久。
她说,你女儿在楼下等你。
我一下拉开了门,跑下去、跑下去,手在楼梯扶手上挠,像怕摔,到了楼下,她站在那个夜色不重的地方。
她穿了一件灰色的羽绒服,帽子没带,头发接触了风,微微飘,像一条渔船上的旗子。
她说,妈在吗。
我说,在。
她说,我把那个锅拿来了,我买错了型号,给你们换了一个。
她递给我一袋子东西,里面是锅,锅被泡泡纸包得很紧,像一个胖子被裹在被子里。
她说,还有一些药,我知道你不爱吃,但是医生说你得吃。
她伸手递给我两盒药,上面写着一种名字我认识,另一个我不认识,我突然觉得自己这个年纪也需要识字。
我把东西接过来,手碰到了她的手,她手是温的,不暖,温。
我说,你上来坐坐。
她说,好。
我们在客厅坐下,周美华从厨房出来,擦擦手,在她对面坐着,两个人眼睛里有一些相似的东西,像一种线,在她们的眉眼里穿过去。
我这次没说那句“端正了态度再回来”,我把一杯水放在她面前,说了句,“你想怎么过,你说。”
她看我一眼,像在确认我是不是一个假人,她的表情像在按一个按钮,看看有没有功能。
她说,我在一个出版社打临工,被一个朋友介绍进去,做一些校对,钱不多,但不会给人当小朋友。
我说,好。
她说,我在租的屋里做饭,有一个房客老是把锅油到一层黄,我不跟他吵,我就把自己的锅贴着贴纸写名字。
我说,好。
她看着我,说,爸,我不结婚不代表我不像一个正常人活着。
她说,我也可以喜欢人,我也可以被喜欢,我不是被某个组织追着跑的材料。
我揉了揉自己的额头,像要把过去的一层硬膜撕掉,露出底下那个软的。
我说,我在麻将馆里跟他们说你不好,是我坏,嘴坏,心也坏。
她说,爸,你也不必打自己。
她说,你就是老了,你也怕一些东西,你怕一个空,你怕未来像一条白白的纸。
她说,那也没什么,我们一起怕。
她那几句话像把我抱了一下,但没有碰到身体,是抱到了我心里一个不被摸到的角落。
她拿出一个纸袋,里面有一叠她以前写的东西,大大小小,有一个是她在公司被优化那段时间写的,对话打印出来,重点划了四条。
她说,要我看吗。
我说,你自己讲吧。
她说,他们把我叫进去,坐在一个会议室,背后是一个玻璃墙,那墙里有一排绿植,像被塑料包扎过的植物。
她说,他们问我“对未来的计划”,问我“是否考虑家庭与职业平衡”,问我“是否注意到自己的年龄”,我当时就笑了,我说,我注意到你的年龄了吗。
她说,那人脸上塞了一团空气,他没听懂我的幽默。
她讲,最后他们用一种特别像礼貌的粗鲁,把我送到门外,说“你可以考虑一下离开”。
她说,我就离开了。
她说,这件事我没跟你们讲,我怕你们把它变成一种你们可以安排我未来的理由。
我坐着,一直摸那个杯子的边缘,杯子边缘有一处小小的缺口,那缺口让我的手指停了一下。
她说,爸,你那天叫我“剩女”,我不是生气,我是觉得你好像从来没看见我这个人。
她说,我不是一个题目,我不是一个群里的笑话,我是李苒,我有喜欢的咖啡,我会迷路,我会坐在菜市场看别人杀鱼。
她说,我也会在晚上想不起睡着。
我眼睛热了一下,但没有让它掉出来,这个年纪的男子,眼泪像一条偷偷的耗子,如果放出来就会在家里乱跑。
周美华在旁边按着她的手,说了一句,“苒啊,你要回来就回来。”
她看着她妈,说,那你们不再在饭桌上把我的人生当做某种胜负讨论吗。
周美华说,不。
我说,不。
我说,不敢了。
我说,如果有人在群里说,我就退出群。
她笑了,说,退出也没用,他们还会在楼下说。
我说,那我就站在楼下说你们不要说。
我们三个人坐在那里,像拿着三个不同大小的杯子,想喝同一杯水。
她那晚没住下,她说她要回去,她的房间里有她种的两盆草,每天晚上要喷一点水,她怕它们饿。
我从她后面走到门口,看着她,把手放在门框上,她说了一句,“爸,你也要端正你的态度。”
她说这句的时候,眼神里有一点坏,像小时候偷吃了糖,看我反应。
我说,好。
她出门之后,我把门关上那一刻,觉得这扇门像换了一层皮,摸起来不那么粗了。
第二天我去拉活,心里有点清爽,我一个乘客说我笑得有点莫名,我说今天风好。
中午我回家,在桌上写了一张字条,给自己,也给她。
我写,“李苒,等我端正了态度再请你回家。”
我把字条贴在冰箱上,冰箱门上油油亮亮的,贴纸的边缘翘起来一点,像一个不完美的承诺。
接下来几天,我开始做一个难的事情,我去跟那些人的嘴交锋。
我在麻将馆里坐,提高声音不吼,说了一句,“以后谁再拿我女儿在群里说话,我就不在这儿混了。”
老许看我,嘴角抖了一下,说,你这是来砸场子。
我说,我不是,我是来给你们一个限度。
王姐经过,笑起来,那个笑笑得太快,一下就垮了,我没看她,我看着我的手,我的手正好可以往桌上一拍,拍出一个不大不小的声音。
他们从那天起收敛一些,我知道他们收敛不是因为他们懂了,是因为我把一个东西从桌上拿走了,他们不敢摸。
我也把群退了,退群那一刻,手机屏幕跳出来一个“你已退出”,这几个字让我居然有一点解脱。
晚上我去接我妈,陪她走了两个街区,她脚步慢慢的,她拎着那个保温杯,杯子上贴着一个黄色的笑脸贴纸,那是她贴的。
我妈突然说了一句,“你跟苒好好说话,她现在其实比你还懂。”
这句话像从她嘴里拿出来的一把钥匙,开了我脑子里一个门,我走进去,里面没有灯,但是慢慢有一种光出来,是从底下发出来的。
我开始给她发一些东西,不是那些“快回来”的话,而是各种细节。
我给她发我在路边看见的一只猫,猫坐在垃圾桶旁边,眼神像人。
我给她发我在厂区拉的一个客人,他的帽子上写了“安全第一”,他儿子在他旁边睡着了。
她回我这个那个,她说,猫看起来像你。
她说,她同事今天把“优化”写成了“优花”,她笑半天。
我觉得这种聊法让我和她变成了两个真正的人,不是父女两个扮演角色。
她有一天发来一张图,图是她做的面包,很难看,表面有裂纹,像个被晒裂的地。
她说,第一次做,失败。
我回她,失败也好看。
她说,好看的东西不怕失败。
我说,丑的也不怕。
她发一个倔强的表情,我很喜欢这个表情,它像她拿着一个小本子写东西的样子。
她慢慢回家来吃饭,不是住,是来吃饭,坐在那个桌子上,她会给她妈把青菜的根用手折掉,不用刀,她说这样菜保持生气。
我们聊天时,她小心地绕开那些过去压着她的话,我们也用力地不把那些东西拿出来。
风一直在窗外,窗帘被风拖着,像一条慢慢的河流。
某次她吃到一半,问我,“你还会催我吗?”
我说,我在催我自己,催我把那些过去的段子从嘴里掉出来。
她说,你可以把它们放到纸上,写写,你这嘴,不是不能写。
我拿起一支笔,写了几个字,写得乱七八糟,但我还是写了。
我写“女儿”。
我写“门”。
我写“态度”。
我写“群”。
我写“麻将馆”。
我写“桥”。
她看了看我写的,笑,说,有点像诗。
我说,我不是诗人,我就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她说,出租车司机也可以写诗。
她说,我在你车上坐过那么多次,那个玻璃上你用纸擦过的圆圈其实特别像一首诗。
我那一刻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她看见的人,这种被看见的感觉让我心里一松。
她也跟我们讲了她的过去,讲了那个差点嫁的男人。
她说,那男人见面讲价,像买东西。
他说,结婚后你得回家,不能加班,不能有你自己的钱。
她说,结婚了就牵手,不是牵着一个手去绑自己。
她说,我当时就走了。
她说,她不是怕孤独,她怕被人用一个温柔的理由让她把自己丢掉。
我们听着,不评论,不把它变成一个酒桌上可以谈的材料。
我们让它在夜里发出一点声音,这一点声音像一个人在房间里起身,去窗边,拉开窗帘那个轻轻的动。
那年春天来了,樱花开了,那个产业园门口那三棵开得还算凑合,风吹一下,花瓣掉了两枚,落在地上,踩上去软。
我带她去看桥,桥身在日光里像一个练过多年瑜伽的人,柔软又稳。
她说,她喜欢这个桥,它从河这端走到那端,走过去也不强调自己。
我说,我喜欢桥下那个钓鱼的人,他一直钓不上来,但他不急。
她说,我也不急。
她说,我这一辈子还有好多年,不可能在三十五这一年就把全部的答案写完。
我点点头,我说,我以前总想早点看到答案,好让我睡觉睡得稳,我现在觉得答案不重要,重要的是别在答题的时候把手指按断。
她说,你这比喻,也不赖。
我们就这样过了几个月,我去拉她,顺路送她去地铁,她在地铁口把口罩戴好,说,爸你不要往里开,保安会赶你。
我说,我不往里开,我就看着你进去。
她说,别看。
她说,我会走路的。
她说,我不是小孩。
她走进去,我还是看了一眼,我觉得我每看一眼就会少一些那种恐惧,那种恐惧像空气里的细菌,只要你开窗它就会飞出去一点。
她某天说,她要去杭州开一个会,坐高铁,她让我不要送,她说她会自己到车站,她说,她能自己把箱子提上去。
我说,好。
她说,好。
这两个“好”像我们把一个石头放回地上,不再搬着。
她回来的那天,我在车里睡着了,微信弹了一个消息,她发了一张她坐在车站里吃饭的照片,饭很简单,两个菜一个米饭。
她在底下写,“我自己点的,我喜欢吃。”
我在旁边留了一小段时间看这个“喜欢”,它像一个被她捏出来的小小的世界,没有外面的人来插手。
她慢慢过得更像她自己,我们慢慢过得更像我们两个人而不是家属,我开始学着把她当一个朋友。
我去见老许,老许说你变了。
我说,我没有变,我就是把那把坏的刀从嘴里拿出来了。
老许说,你认识她三十五年,现在才把刀拿出来,有点晚。
我说,晚也比没有好。
老许笑,我也笑,我们两个人笑的时候有一些真诚,像把烟放远了一点。
我妈的身体慢慢好起来,她的血压从那本子上被一条条数字替换,她很专业,像一个工作了多年的护士。
她说,她舍不得那个群里的热闹,我说你别舍不得,热闹有时候像糖,吃多了掉牙。
她说,你怎么现在会讲这种话了。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觉得这么讲好听。
她说,你还是少抽烟。
我说,好。
她说,你给我买的包上次有点漏,我用胶带补了。
我说,我再给你买一个。
她说,不用,她说补着也挺好,她说补在那儿提醒我这个家不是新的,它是一个补过的家。
这个“补过的家”让我晚上回到房间坐在床边想了很久,我觉得我把她撵出去那晚,其实我把这个家剥了一层皮,现在我们把它缝回去,缝得不漂亮,但能用。
我的电话里偶尔会有一些来自亲戚的声音,他们给我发一些相亲资料,发一些“不错的男孩”,他们把照片发来那瞬间,其实像丢了一个三明治到我的窗里。
我就不回,我把这些东西一个一个按删除,有一次我把手滑了一下,点开了,看见一个照片里的男人穿着一件条纹衬衫,他的眼神像篮子里的菜,没听过风。
我还是删掉。
我对他们说,我女儿过得好,不用你们操心,他们说你这人死心眼,我说我死心眼不是今天才死。
他们说你以后会后悔,我说我后悔的是过去,不是将来。
他们不回了,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这一笔也算结掉了。
某个夏天的晚上传来蛙声,八楼都听得见,窗帘上有一些花,我不喜欢,周美华喜欢,她说这些花让她心里暖。
她在厨房里做了一锅粥,粥外面起了一层厚厚的泡泡,我用勺子一点点把它们开了,这种开泡的过程比我以前的生活更像生活。
她当晚过来,穿着短袖,手臂上有一块被太阳晒出来的颜色,她说她去看展了,她说那个展很一般,但好的是她在里面坐一个小时。
她说,她在一个画前面坐着,把那个画看到不动,看到它像一堵墙,她在那堵墙前面举不起手,也不想举手,她一身轻。
我说,我也有这种感觉,我在车里打开广播,看着那个路,我就不想动。
她说,你就是开始会觉得自己人一点。
她的笑轻一点,她的眼神也软一点,我们之间的路没有那么费劲。
她某天问我,要不要去把她房间的门打开,她说她想搬回来住一阵子,她说她想和我们在一起吃一段时间饭。
我说,门一直是开的。
她说,你当时是关上了。
我说,我现在把钥匙插上了。
她笑,说,爸,你这话也不算有文采,但挺真。
她搬回来住了一个月,她的东西不多,她放了一两件衣服,放了一本书,书的封皮是蓝的,书名简单,像一个普通人的名字。
我们晚上一起看电视,她参与了我们的小日子,她会突然起身去把电饭锅关掉,像一个拥有这个家的权利的人。
她在这个月里把我们家的垃圾分类做得有条有理,她在厨房贴一个小小的表,把每种东西标了颜色,她说,你们可以不做,但我不能不做。
她还把我们家的窗台上一个小土堆翻了翻,把那个被我们忽略的芦荟根理了理,她说,这个东西可以救急。
她在那个一月里和她妈吵了一次,是因为洗衣机里有人把白衬衫和红袜子一起放了,她妈说不是她,她说也不是她,我嫌这事小,没说话,她们自己缓和了。
李苒说,她要再出去住,她说她的工作要开始进一个忙的阶段,她说她需要自己一个空间。
我说,去吧。
她说,她会每周来两次,她会帮我们检查一些东西,她说她不是某种担任“孝顺”的角色,她说她就是想帮。
她在门口换鞋的时候,抬头看我,说,“爸,你现在说‘端正态度再回来’这句话,会换成‘我们互相端正态度再一起吃饭’吗?”
我说,会。
我说,我早改了。
她说,那我放心。
她过了那条斑马线,车灯打在她的外套上,光滑。
我站在门口,她远远地在街角停了一下,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一眼像把我刚写出来那几句粗糙的诗按了一下,让它们不用那么紧张。
后来,她找了一个人,不是我们介绍的,是她自己认识的,是在她那个出版社帮忙的一个摄影老师,他年纪也不小,四十出头,长得像一个让人觉得他知道怎么自然地走路的人。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一个书店里,我们在里面喝咖啡,那咖啡有一点苦,我喝了两口就放在桌子上,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我们俩都有点尴尬。
他笑着说,叔,我一直想见你。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手指轻松地在桌面上敲了一下,像打了个小小的拍子。
他说,他喜欢苒,他说他也怕她把自己弄没了,他说,他愿意跟她一起怕。
我觉得这个愿望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它不像某些人在相亲里说的那些话,那些话像一张干净的纸,经不得拿。
我没有给他任何承诺,我只是说了一句,我希望我不要像以前那样把别人从门里把走。
他笑,说,他会给她买鞋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让我心里暖了一下,买鞋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这个细节里有了一个文字的空气。
他们后来一起去看了一场电影,电影挺长,中间有一个无聊的段落,李苒回来跟我们讲的时候说,她在里面看到了自己的某种慢,她不急。
她说,她不怕她现在还有很多人没赞同她,但她觉得她自己和她喜欢的人都在一起说了一句“好”。
我坐在饭桌上听,觉得这一桌饭把我们过去的那些情绪一点点熬开了,里面冒出来一些新的东西,淡淡的,像小米粥。
李苒在饭后帮我们把锅洗了,她把锅底的那层黑用土方法抠掉了一点,我说这个锅旧,她说旧的东西也有好。
她说,旧的东西总知道它在哪里。
我看她这个人,觉得她在这个世界上终于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站位,不是队伍里的那种“编号”,是某条空地。
我有时候还会犯错,我还会在某个沉默的傍晚突然想起过去的那些强硬话,嘴巴痒痒,想说,我就去阳台走一圈,让风把它吹掉。
我的电话里偶尔会收到一些,看似关心实际是闲话的消息,我现在会回一个笑脸,然后让它在厚厚的消息堆里迷路。
我知道我一辈子都会把这件事情拎起来看,我把她撵出家门那天和今天我们坐在桌边吃饭那天远远地对望,它们中间隔着这么多天,我不能用一个简单的词把它们概括。
我也知道我会在某个明年某个不太重要的日子,在我的车里从前座拿起一个她前几天忘在车上的手套,手套是灰色的,上面有一点薄的棉,我会捏着它,想到她那句“我们一起怕”。
我会笑一笑,然后继续开车,车窗外有我们这个城市所有的碎片,黑的、白的、亮的、暗的,它们在我眼前过去,我在里面看见我女儿,和我自己。
我知道我没有赢,也没有输,我只是把我自己放到一个不那么硬的地方。
我也知道,我再也不会说那句“端正了态度再回来”,我会说,“我们一起把这句端正了的态度放在桌上,让它不再像个刀。”
我们坐在桌边,每一口饭吃下去,都会觉得这个家不再是谁的胜负,它是我们一起的生活。
也许这个就是我们最后能做的那点事,细小但足够抵抗一个没那么具体的世界。
等你,盼你,我要和你在一起
你知道吗?那些深夜翻来覆去睡不着的人,80%都在想同一个人。
这不是什么情感鸡汤,而是心理学研究给出的答案。
2023年《心理学日报》的数据显示,长期思念一个人会导致皮质醇水平升高,而这种压力激素的堆积,会直接影响免疫系统和睡眠质量。
有人把这种状态形容为"甜蜜的折磨"——明明心里装着一个人,却因为各种原因不能立刻相见。可能是异地恋的无奈,可能是工作太忙的妥协,也可能是还没勇气说出口的暗恋。
最煎熬的不是等待本身,而是不知道等待有没有结果。
见过凌晨三点的朋友圈吗?那些欲言又止的动态,那些分享到一半又秒删的歌曲,都是想说又不敢说的心事。有个读者曾经留言:"每次手机震动都以为是他,每次都不是,但每次还是忍不住期待。"
科学家说,这种期待感会刺激多巴胺分泌。就像玩老虎机的人明知道大概率不会中奖,还是忍不住一次次投币。爱情里的等待也是如此,明知可能落空,却控制不住去幻想重逢的场景。
但等待不该是单向的消耗。
研究发现,健康的情感关系应该像呼吸一样有来有往。单方面的付出和等待,最终消耗的是自己的能量。那些修成正果的异地恋,往往都保持着稳定的情感互动频率——不一定是每天视频,但一定会让对方感受到"我在这里"。
有个很妙的比喻:好的感情应该像Wi-Fi信号,不需要时时刻刻满格,但关键时候绝不能掉线。
最动人的情话不是"我爱你",而是"我懂你"。
见过太多人把思念熬成了自我感动。发几十条得不到回复的消息,买用不上的礼物,在对方根本看不到的地方写小作文。但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可能是加班时的一杯咖啡外卖,可能是生病时的一句"药吃了吗",可能是随口一提的小心愿被默默实现。
心理学家说,亲密关系里最珍贵的不是轰轰烈烈的仪式感,而是那些"被看见"的瞬间。就像深夜加班回家发现留着的灯,就像感冒时床头突然出现的药盒。
等待可以很美好,前提是两个人都在数日子。
有个结婚十年的朋友说,他们恋爱时异地三年,但从来不觉得苦。因为会把见面的日子写在日历上,每天划掉一格;会约定同时看同一部电影,假装坐在同一个影院;会攒车票做成纪念册,每次吵架翻一翻就心软了。
现在他们家的玄关还挂着那本发黄的票根册子。孩子总问这是什么,他们就笑着说:"这是爸爸妈妈的青春。"
如果你也在等一个人,记得留三分力气爱自己。
见过太多人在等待中枯萎。放弃社交,暂停爱好,把生活过成了待机状态。但真正值得的等待,不该是生命的暂停键。
有个瑜伽老师的故事特别打动人。她和男友异国恋五年,每次想对方就去练瑜伽。等男友回国时,她不仅等到了爱情,还意外考下了教练资格证。现在他们的工作室就叫"等待时光"。
等风来不如追风去。
所有修成正果的等待,本质上都是两个人的双向奔赴。就像机场永远比火车站见证更多真挚的拥抱,因为知道这次见面是用多少张机票换来的。
所以,如果那个人值得,等多久都没关系。但别忘了,真正的爱情不会让你永远活在等待里。它会在某个清晨突然敲门,带着一路风尘和全部真心。
文档上传者
热门标签
相关文档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