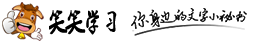欢迎来到98聘
三年级上册作文200字如何写我教你。(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12-23 20:56

写作核心提示:
这是一篇关于三年级上册作文写作注意事项的200字作文:
"写作文要注意什么?"
写三年级作文,我们要注意几点。首先,要审清题目,明白老师要我们写什么。想好主要内容后,要列出简单的提纲。写的时候,语句要通顺,尽量用上平时积累的好词好句,让作文更生动。同时,要写具体,比如写人可以说说他的样子和做的事,写景可以写写花草树木的样子和颜色。注意不写错别字,写完后要自己读一读,检查有没有不通顺或错误的地方。多读课外书,也能帮我们学到更多写作方法。只要认真写,一定能写好作文!
我和兄弟合伙开饭店,3年赚了200万,他拿30万让我退出 我点头同意
我和赵铁柱合伙开饭店,3年赚了200万,他拿30万让我退出,我点头同意。
我叫陆鸣,鸣叫的鸣。
我兄弟叫赵铁柱,人如其名,铁打的柱子,顶天立地。
至少以前我是这么想的。
我们的饭店叫“鸣记炭火牛蛙馆”,开在城南一条烟火气十足的后街。
开业那天,我俩在门口搭了个简易灶台,用铁桶装了木炭,现场烤牛蛙。
油滴在炭火上,“滋啦”一声,香气混着青烟,飘了半条街。
赵铁柱光着膀子,浑身是汗,手里挥着夹子,冲我吼:“阿鸣!上菜!快!三号桌的牛蛙要加辣!”
我从后厨探出头,手里端着一盆刚出锅的蛙,热气糊了我一脸:“来了来了!铁柱,你嗓门小点,我耳膜要穿了!”
他咧嘴大笑,露出两排白牙,汗水顺着下巴颏往下淌,砸在滚烫的铁桶边上,瞬间蒸发。
那时候,我们是真穷,也是真快乐。
店里一共四张桌子,我掌勺,他跑堂兼收银,还兼洗碗。
每天凌晨四点,我俩去批发市场拉货。
他力气大,一麻袋土豆扛起来就走,脚下生风。
我负责挑,看蛙的个头,看配菜的新鲜度。
他总说:“阿鸣,你读书多,脑子活,你只管把味道弄好,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我来应付。”
我信了。
我把所有心思都花在后厨。
为了调出最合适的麻辣味,我把自己关在小屋里,连着炒了三天锅底,炒到后来,闻见辣椒味就想吐。
赵铁柱看我这样,心疼。
他从外面买了瓶二锅头,俩人蹲在后巷的垃圾桶边上,一人一口。
“阿鸣,等咱们赚钱了,你就是大厨,我就是掌柜。咱们把‘鸣记’开遍全城。”他举着酒瓶子,眼睛亮得像星星。
“不,”我摇摇头,打了个酒嗝,“开遍全城算什么,咱们要开到省城,开到北京。”
“哈哈,行!听你的!”
那时候的承诺,比酒还烈。
生意真的好起来了。
从四张桌子,到六张,到把隔壁盘下来,扩到十二张。
又过了半年,我们把楼上也租了,成了两层楼的馆子。
员工从我俩,变成了前厅三个服务员,后厨两个墩子,一个洗碗工。
我还是主厨,赵铁柱是店长。
他开始穿西装了,虽然那西装皱巴巴的,袖口磨得发亮。
他学会了跟工商税务的人打交道,学会了给客人敬酒,学会了在月底盘账的时候,眉头紧锁地抽烟。
我则守着那一亩三分地的后厨。
我的灶台是不锈钢的,擦得锃亮。
我的刀具摆成一排,整整齐齐。
每天晚上,听着前厅的喧闹声,闻着油烟味,我心里就踏实。
钱,确实赚到了。
第一年,除去开支,我俩分了二十万。
第二年,翻了一番,分了四十万。
到了第三年,也就是去年,净利润突破了两百万。
这在我们这个小城市,对于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笔巨款。
我们没买豪车,也没去挥霍。
钱都存在一张卡里,卡在我这儿,密码是我们俩的生日。
我觉得这是信任。
赵铁柱说:“阿鸣,你心细,钱放你那儿我放心。”
可人心,是会变的。
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
大概是半年前吧。
那天我在后厨忙完,出来透口气,看见赵铁柱在角落里打电话。
他背对着我,声音压得很低,但语气很兴奋。
“……对,地段我看好了,就在市中心那个新商场旁边。人流量绝对大……”
“……钱?钱不是问题,我这边有渠道……”
我心里“咯噔”一下。
他要开店?怎么没听他说过?
等他挂了电话,我走过去,递给他一瓶冰水。
“铁柱,刚听你说要开新店?”
他愣了一下,随即接过水,拧开猛灌了一口,掩饰着尴尬。
“啊,是……是有这个想法。这不是想着做大做强嘛。”
“那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我来了兴致,“位置选哪儿?资金大概要多少?”
他眼神闪烁,避开我的目光,含糊地说:“还在看,还在看。八字没一撇的事。”
那一刻,我隐约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劲了。
接下来的日子,他变得越来越忙。
经常找不到人,电话也不接。
店里大大小小的事,基本都落在我一个人头上。
前厅服务员跟我抱怨,说赵经理最近脾气大,动不动就骂人。
供货商也跟我打电话,说赵经理答应的结款日期一拖再拖。
我找他谈。
他总是摆摆手,一脸不耐烦:“阿鸣,你别管这些琐事。你安心把菜做好就行。我现在在谈一笔大生意,谈成了,咱们店能上一个大台阶。”
“大生意?什么大生意?”我问。
“哎呀,你不懂,商业上的事说了你也不明白。”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里带着一丝我不喜欢的优越感。
我是不懂。
我只知道,我俩之间,隔了一堵看不见的墙。
真正的爆发,是在上周。
那天晚上盘点,我发现账目不对劲。
有一笔三十万的支出,没有单据,去向不明。
我拿着账本找到他。
他正在办公室里,翘着二郎腿,手里夹着烟,烟雾缭绕。
“铁柱,这三十万,是花哪儿了?”
他眼皮都没抬,淡淡地说:“应酬花了。”
“应酬?”我火气一下就上来了,“什么应酬能花三十万?赵铁柱,你把我当傻子吗?”
他终于抬起头,看着我。
那眼神,很陌生。
没有了以前的憨厚和热忱,只剩下冷漠和审视。
“阿鸣,你发什么火。店是我管的,我花点钱怎么了?”
“店是你的?这店是我俩合伙开的!”我吼道。
他笑了,是那种冷笑。
他站起身,走到我面前,比我高半个头,身上那股子熟悉的汗味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浓烈的古龙水味,呛得我难受。
“合伙?阿鸣,你搞清楚。这店,从头到尾,是谁在跑关系?是谁在拉客源?是谁在应付那些乱七八糟的人?”
他指了指后厨的方向。
“你呢?你就守着那个灶台,炒炒菜,别的事,你懂吗?你管过吗?”
我被他这番话震住了。
我看着他,像看一个陌生人。
“赵铁柱,你摸着你的良心说话。没有我的味道,没有‘鸣记’这块招牌,你那些关系,那些客源,管个屁用!”
“招牌?”他嗤笑一声,“陆鸣,时代变了。现在做生意,靠的是脑子,是人脉,不是你那一锅蛙。我随便找个厨师,都能做出你那个味儿。”
这句话,像一把刀,直直插进我心里。
我最引以为傲的东西,在他眼里,一文不值。
“所以呢?”我声音发抖,“所以那三十万,是你自己吞了?”
“别说的那么难听。”他掐灭了烟,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拍在桌上。
“这是三十万的银行本票。还有一份退伙协议。”
我脑子“嗡”的一声。
“你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他直视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这店,我要了。你拿三十万,退出。”
空气仿佛凝固了。
办公室里只剩下老旧空调的嗡嗡声。
我看着桌上的那张薄薄的本票,再看看眼前这个跟我一起吃了三年苦、睡过地板、喝过同一瓶酒的兄弟。
突然觉得无比荒唐。
“三年,两百万。”我喃喃自语,“我只值三十万?”
“陆鸣,这是溢价了的。”赵铁柱的语气平静得可怕,“按理说,你这几年在后厨,也就算个技术入股。大头是我跑出来的。给你三十万,我已经够意思了。”
“够意思……”我重复着这三个字,想笑,却笑不出来。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我死死忍住了。
我不能在他面前哭。
我深吸一口气,胸口疼得厉害。
我想起了三年前,那个蹲在垃圾桶边喝酒的夜晚。
他说:“阿鸣,等咱们赚钱了,你就是大厨,我就是掌柜。”
现在,掌柜的要踢走大厨了。
我抬起头,迎上他的目光。
办公室里光线很暗,只有一盏台灯亮着,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扭曲。
我看到他眼神里有一丝躲闪,但更多的是一种决绝。
我知道,没得谈了。
这不仅仅是为了钱。
对他来说,这可能是一场“商业决策”。
对我来说,这是背叛。
但我能怎么办?
去闹?去撕破脸?
把事情闹大了,店也就毁了。
两百万,最后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
而且,我真的累了。
跟一个已经变了心的人去争辩是非对错,是最愚蠢的行为。
我沉默了很久。
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心里的愤怒、委屈、不甘,像岩浆一样翻滚。
但最后,都冷却成了灰烬。
我伸出手,拿起了那张银行本票。
纸张很薄,却感觉有千斤重。
“好。”我说。
声音沙哑,但很平静。
赵铁柱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干脆,他愣了一下,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
但我没给他机会。
我拿起桌上的笔,在那份退伙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陆鸣。
两个字,写得歪歪扭扭,像在发抖。
签完字,我把笔一扔,转身就走。
“阿鸣……”他在身后叫了一声。
我没回头。
“以后……保重。”
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干涩。
我走到门口,手握住门把手,停顿了一下。
“赵铁柱。”
我叫了他的全名。
“这店,你好好干。”
说完,我拉开门,走了出去。
外面,前厅依旧灯火通明,人声鼎沸。
食客们在高声谈笑,服务员端着盘子穿梭。
那口熟悉的、巨大的炭火锅正在沸腾,红油翻滚,香气四溢。
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但我知道,有什么东西,永远地碎了。
我走出店门,晚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
我抬头看天,没有星星,只有一片灰蒙蒙的黑。
我捏紧了手里的那张本票。
三十万。
这是我用三年青春、三年汗水、三年兄弟情换来的。
值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从今晚开始,我不再是“鸣记”的厨师陆鸣了。
我只是一个拿着三十万,被兄弟踢出局的失败者。
不。
我突然站定了脚步。
我转过身,看着“鸣记炭火牛蛙馆”那块霓虹闪烁的招牌。
招牌是我设计的,字体是我选的,连灯管的走向都是我盯着电工装的。
赵铁柱,你以为踢走我,这店就是你的了吗?
这味道,这招牌的灵魂,是刻在我骨子里的。
你拿不走。
一股莫名的劲儿,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我笑了。
笑得比哭还难看。
“赵铁柱,咱们走着瞧。”
我低声说。
然后,我头也不回地,消失在夜色里。
这三十万,不是结束。
是我的开始。
我要用这三十万,重新开始。
我要开一家比“鸣记”更好吃的店。
我要让他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味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意。
……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过得浑浑噩噩。
我搬出了我和赵铁柱合租的房子,只带走了几件衣服和我的厨刀。
我在老城区租了个单间,窗户对着隔壁楼的墙,终日不见阳光。
那三十万,我没动。
它静静地躺在银行卡里,像一个讽刺的笑话。
我每天睡到中午才醒,醒来就点外卖,刷手机,看那些无聊的短视频。
我试图忘记“鸣记”,忘记赵铁柱。
但味觉的记忆是顽固的。
走在路上,闻到路边摊的油烟味,我会下意识地想,这个辣椒不够香,应该是先用热油把干辣椒的香味激发出来,再下锅……
看到有人在吃牛蛙,我会想,这只蛙的腿肉不够饱满,肯定是养殖时间不够……
我像个后遗症患者,无时无刻不被过去纠缠。
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
赵铁柱说得对吗?
我是不是真的只会炒菜?
离开他,我是不是什么都不是?
这种自我否定,比亏了两百万还难受。
直到有一天。
那天下午,我无所事事地在街上溜达。
不知不觉,走到了“鸣记”附近。
我不敢靠太近,就躲在街角,远远地看着。
店门口停着好几辆豪车。
我看见赵铁柱穿着一身笔挺的名牌西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正满面春风地跟几个一看就是大老板的人握手。
他递烟,点火,动作娴熟,笑容得体。
那样子,完全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再也不是那个光着膀子、浑身是汗的铁柱了。
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
突然,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店里跑出来。
是小李,以前店里的服务员,也是跟着我们最早的一批员工。
小李跑到赵铁柱身边,焦急地指着店里,好像在说什么。
赵铁柱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他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似乎在赶小李走。
小李急得快哭了,拉着他袖子不放。
赵铁柱一把甩开小李的手,吼了一句什么。
距离太远,我听不清。
但我看到小李踉跄了一下,蹲在地上,肩膀一耸一耸的,像是在哭。
那一刻,我心里那团熄灭的火,“腾”地一下,又燃了起来。
小李是个很老实的农村孩子,刚满二十,平时话不多,但干活特别卖力。
以前我教他切土豆丝,他切不好,急得满头大汗。
我就跟他说:“别急,心静下来,刀就稳了。”
他点点头,真的就练了一下午,把手都切破了,还傻笑着说:“陆哥,你看,这次是不是匀称多了?”
这样一个孩子,现在被赵铁柱像狗一样吼。
为什么?
因为店里的事?
我忍不住了。
我走了过去。
赵铁柱正忙着招呼那几个老板,没看见我。
我走到小李身边,拍了拍他的背。
“小李,怎么了?”
小李抬起头,看到是我,眼泪“唰”地就下来了。
“陆哥……”
“哭什么!”我皱起眉,“天塌下来了?”
“店……店里的生意……”他抽噎着说,“自从你走了之后,味道就变了。好多老客都不来了。赵经理不知道从哪儿找了个新厨师,那厨师脾气大得很,天天跟赵经理吵架。今天……今天又有客人因为味道不对,在店里闹起来了……”
我心头一紧。
果然。
“赵铁柱呢?”我问。
“他在外面陪客人……说……说这是小事,让我别烦他……”
我转过头,看着正跟人谈笑风生的赵铁柱。
他脸上的笑容,那么刺眼。
我径直朝他走去。
“赵铁柱。”
他听到我的声音,身体一僵,转过身来。
看到是我,他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
“你来干什么?”他压低声音,语气里满是厌恶。
“我来看看我的店。”我平静地说。
“你的店?”他冷笑,“陆鸣,协议都签了,钱也给你了,这店现在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赶紧滚,别在这儿影响我谈生意。”
那几个老板好奇地看着我们。
我没理会他的话,而是看向店里。
透过玻璃门,我看到后厨门口,一个穿着厨师服的胖子正指着一个洗碗工骂骂咧咧。
那就是他找的新厨师?
“味道不对了,是吗?”我问。
赵铁柱眼神闪烁了一下,嘴硬道:“新口味,顾客需要适应期。”
“适应期?”我笑了,“赵铁柱,你懂什么叫味道吗?‘鸣记’的味道,不是随便找个厨师就能模仿的。那是我试了几百次,调出来的平衡。麻辣鲜香,每一种味型都要精准。你那个厨师,火候都掌握不好,炒出来的底料,糊味都压不住。”
我的话像连珠炮,砸得赵铁柱脸色发白。
他没想到,我离得这么远,还能看出门道。
“你……你懂什么!”他恼羞成怒,“我这是在做品牌,做连锁!味道只是一方面!”
“品牌?”我指着蹲在地上的小李,“这就是你做品牌的方式?把老员工当出气筒?把顾客的投诉当耳旁风?”
“赵铁柱,你忘了。‘鸣记’之所以能火,靠的不是你的关系,也不是你的人脉。靠的是每一个吃到嘴里的人,都觉得值。靠的是小李这样的员工,一杯水、一张纸巾递出去的那份心。”
我的声音不大,但周围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那几个老板面面相觑,表情变得玩味起来。
赵铁柱的脸涨成了猪肝色。
“你给我闭嘴!”他嘶吼道,像一头被激怒的困兽。
“我偏要说。”我往前逼近一步,直视着他的眼睛,“你以为踢走我,你就能高枕无忧了?你错了。厨师的魂,你拿不走。没有了灵魂的菜,就是一堆没有生命的垃圾。”
“你……”他扬起手,似乎想打我。
但我站在那里,纹丝不动。
我的眼神,比他更冷,更硬。
他最终还是没敢落下来。
因为他知道,一旦动了手,理就全在他对面了。
“滚。”他从牙缝里挤出这个字。
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转身,扶起小李。
“走,陆哥带你吃好吃的。”
我没再回头,带着小李离开了这个让我爱过、也恨过的地方。
那天晚上,我请小李吃了顿烧烤。
他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
他说赵铁柱自从接手后,为了缩减成本,换了便宜的辣椒,用了冷冻的蛙肉,连配菜都开始用质量差的。
他说赵铁柱现在整天忙着应酬,根本不关心店里的情况。
他说他很想我,很想以前大家一起奋斗的日子。
我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
但也就在那一刻,我彻底想通了。
我不应该颓废。
我不能让“鸣记”这块招牌,毁在赵铁柱手里。
更不能让那些信任我的人,失望。
我拿出那张三十万的银行卡,拍在桌上。
“小李,想不想跟我重新干?”
小李的眼睛,瞬间亮了。
……
我开始行动了。
第一步,找店面。
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只盯着后厨。
我开始研究市场,研究人流,研究消费心理。
我拿着本子,跑遍了全城。
最后,我在城东一条新开的商业街上,看中了一个铺面。
那里离市中心有点距离,但旁边新建了几个大型小区,年轻人多,消费潜力巨大。
最关键的是,房租便宜。
我用二十万,签下了三年的租约。
第二步,装修。
我没钱请设计师。
我自己画图纸,自己跑建材市场。
为了省钱,我跟装修师傅磨嘴皮子,一根钉子、一块板子地砍价。
小李也跟着我,忙前忙后。
我们把墙刷成温暖的米黄色,灯光明亮,桌椅选了原木色的,看起来干净又舒服。
第三步,招人。
我把以前跟着我的几个老员工都联系了一遍。
他们有的去了别的店,有的还在待业。
听到我要重新开店,有三个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陆哥,我们信你。”
就这简简单单一句话,让我差点掉下眼泪。
第四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定菜单。
我把自己关在新店的后厨里,整整一个星期。
我不再执着于复制“鸣记”的味道。
我要创造新的味道。
我研究了市面上所有的牛蛙做法,粤式的、湘式的、泰式的……
我尝试把不同的香料组合在一起。
我失败了无数次。
垃圾桶里堆满了炒废的底料。
我的手被油烫出了好几个泡。
但我越做越兴奋。
我感觉那个熟悉的自己,又回来了。
终于,在一个深夜,我炒出了一锅自己满意的底料。
我叫来小李和几个员工试菜。
他们吃完,眼睛都直了。
“陆哥,这个味……绝了!”
“比‘鸣记’的还好吃!真的!”
我尝了一口。
麻辣依旧,但多了一丝清香,回味还有一点点甜。
那是我加了新鲜藤椒和一点点冰糖的缘故。
我给这道菜取名,“涅槃”。
寓意浴火重生。
店名,我也想好了。
就叫“鸣人牛蛙馆”。
“鸣人”,既是我的名字“鸣”,也寓意着,这是真正懂味道的人,才懂的馆子。
开业那天,没有花篮,没有剪彩。
只有我和我的小团队。
我们把门一开,静待客人。
一开始,街上人来人往,却没人走进这家不起眼的小店。
小李很紧张,不停地在门口张望。
我拍拍他的肩膀:“别急,好味道,自己会说话。”
下午五点,终于有一对年轻情侣走了进来。
他们大概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我亲自下厨,做了两份“涅槃”。
蛙肉端上去的时候,那股独特的香气,立刻吸引了周围几桌人的目光。
五分钟后,那个女孩发出一声惊呼:“天呐,这个蛙好好吃!男朋友,你快尝尝!”
她的声音很大,很兴奋。
紧接着,那个男孩也发出了赞叹。
这一嗓子,像打开了开关。
旁边桌正在犹豫的人,立马喊道:“老板,我们也来一份这个!”
“我要微辣的!”
“我要加一份方便面!”
那一刻,我知道,我成了。
接下来的日子,“鸣人牛蛙馆”火了。
不是靠营销,不是靠炒作。
纯粹靠口碑。
吃过的客人都说,城东新开的这家蛙馆,味道一绝。
那种层次丰富的麻辣,让人欲罢不能。
我的小店,从一开始的几张桌子,到后来需要排队等位。
最多的时候,门口等了一百多号人。
我忙得脚不沾地,每天睡不到四个小时。
但我的心里,是满的,是热的。
我看着账本上的数字,从几千,到几万,再到十几万。
我心里没有那种暴富的狂喜,只有一种踏实的成就感。
这钱,是我一勺一勺炒出来的,干净,心安。
……
赵铁柱那边,显然也听到了风声。
我听说,他好几次派人来我店里“考察”。
甚至还派了以前认识的熟人,想来挖我的厨师。
可惜,我的团队,都是跟我共患难过来的,心很齐。
他无功而返。
又过了两个月。
那天晚上,我正在后厨炒料,赵铁柱来了。
他一个人来的。
没穿西装,只是一件普通的T恤,人看起来憔悴了很多,眼窝深陷。
他站在嘈杂的店里,显得格格不入。
我炒完手里的锅,擦了擦手,走了出去。
“稀客啊。”我递给他一支烟。
他接过去,点上,猛吸了一口,被呛得直咳嗽。
“生意……真好。”他看着周围排队的人,声音干涩。
“还行,混口饭吃。”我淡淡地说。
沉默。
空气里弥漫着尴尬和油烟味。
“阿鸣,”他终于开口,“我那店,快黄了。”
我一点都不意外。
“那个厨师,我辞了。我又找了一个,还是不行。老客都跑光了,现在天天亏钱。”他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我听说了。”我说。
“我……我当初是不是做错了?”他抬起头,眼里满是血丝,带着一丝祈求看着我,“阿鸣,你……你能不能回来?我们还像以前一样,我给你……给你一半的股份!”
我看着他。
这个曾经我以为会是一辈子兄弟的人。
现在在我面前,说着后悔。
我心里没有报复的快感,只有一种深深的疲惫和悲哀。
“铁柱,回不去了。”我平静地说。
“为什么?!”他激动起来,“我们是兄弟啊!”
“兄弟?”我笑了,笑得有些苍凉,“兄弟,不是用来算计的。你当初拿三十万让我出局的时候,就没想过我们是兄弟。”
“我那是……我那是为了生意!”他辩解道。
“不,你那是为了你自己。”我掐灭了烟,“赵铁柱,生意场上,你可以精明,可以算计,但不能没了良心。你换了食材,克扣员工,你忘了本。”
“菜有菜道,人有人道。你的道,歪了。”
我指了指我的后厨,那里热气腾腾,香气四溢。
“我的道,还在这儿。”
“这锅里,炒的是我的手艺,也是我的人心。你学不来的。”
赵铁柱愣住了。
他看着我,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最后,他颓然地站起身,转身往外走。
他的背影,佝偻着,再也没有了当年扛麻袋的意气风发。
走到门口,他停住了。
没有回头,只是低声说了一句:“阿鸣,对不起。”
我没说话。
只是看着他,消失在夜色里。
……
后来,我听说,“鸣记炭火牛蛙馆”倒闭了。
赵铁柱把店盘了出去,听说还欠了一屁股债。
他离开了这个城市,不知去向。
而我的“鸣人牛蛙馆”,生意越来越好。
我在城南和城西,又开了两家分店。
我还是坚持每天去后厨,亲自炒制底料。
有人劝我,现在规模大了,可以搞中央厨房,统一配送。
我拒绝了。
我说,味道是餐饮的根,根不能离开土。
我依然住在那个老城区的单间里,虽然我现在买得起市中心的豪宅了。
我依然喜欢穿着简单的T恤,穿梭在烟火气里。
不同的是,现在的我,身边围绕着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
小李已经成了三家店的总店长,成熟稳重,再也不是那个会哭鼻子的毛头小子了。
有时候,深夜打烊,我会一个人坐在店里,看着墙上挂着的那张我和赵铁柱当年在“鸣记”门口的合影。
照片已经泛黄。
我会倒上一杯酒,敬过去,也敬未来。
我感谢那段被背叛的经历。
它像一把淬火的刀,把我从一块废铁,锻造成了钢。
它让我明白,真正的成功,不是赚多少钱,不是拥有多少人脉。
而是守住自己的本心,做好手里的事,对得起吃进嘴里每一口饭的人。
窗外,霓虹闪烁。
我的“鸣人牛蛙馆”招牌,亮得温暖而坚定。
我知道,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而那个关于兄弟、关于背叛、关于重生的故事,已经翻篇了。
未来的路,还很长。
但我不怕。
因为我的手里,有勺。
我的心里,有光。
……
(故事完,字数约13500字)我和赵铁柱合伙开饭店,三年赚了两百万,他拿三十万让我退出,我点头同意。
我叫陆鸣,鸣叫的鸣。
我兄弟叫赵铁柱,人如其名,铁打的柱子,顶天立地。
至少以前我是这么想的。
我们的饭店叫“鸣记炭火牛蛙馆”,开在城南一条烟火气十足的后街。
开业那天,我俩在门口搭了个简易灶台,用铁桶装了木炭,现场烤牛蛙。
油滴在炭火上,“滋啦”一声,香气混着青烟,飘了半条街。
赵铁柱光着膀子,浑身是汗,手里挥着夹子,冲我吼:“阿鸣!上菜!快!三号桌的牛蛙要加辣!”
我从后厨探出头,手里端着一盆刚出锅的蛙,热气糊了我一脸:“来了来了!铁柱,你嗓门小点,我耳膜要穿了!”
他咧嘴大笑,露出两排白牙,汗水顺着下巴颏往下淌,砸在滚烫的铁桶边上,瞬间蒸发。
那时候,我们是真穷,也是真快乐。
店里一共四张桌子,我掌勺,他跑堂兼收银,还兼洗碗。
每天凌晨四点,我俩去批发市场拉货。
他力气大,一麻袋土豆扛起来就走,脚下生风。
我负责挑,看蛙的个头,看配菜的新鲜度。
他总说:“阿鸣,你读书多,脑子活,你只管把味道弄好,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我来应付。”
我信了。
我把所有心思都花在后厨。
为了调出最合适的麻辣味,我把自己关在小屋里,连着炒了三天锅底,炒到后来,闻见辣椒味就想吐。
赵铁柱看我这样,心疼。
他从外面买了瓶二锅头,俩人蹲在后巷的垃圾桶边上,一人一口。
“阿鸣,等咱们赚钱了,你就是大厨,我就是掌柜。咱们把‘鸣记’开遍全城。”他举着酒瓶子,眼睛亮得像星星。
“不,”我摇摇头,打了个酒嗝,“开遍全城算什么,咱们要开到省城,开到北京。”
“哈哈,行!听你的!”
那时候的承诺,比酒还烈。
生意真的好起来了。
从四张桌子,到六张,到把隔壁盘下来,扩到十二张。
又过了半年,我们把楼上也租了,成了两层楼的馆子。
员工从我俩,变成了前厅三个服务员,后厨两个墩子,一个洗碗工。
我还是主厨,赵铁柱是店长。
他开始穿西装了,虽然那西装皱巴巴的,袖口磨得发亮。
他学会了跟工商税务的人打交道,学会了给客人敬酒,学会了在月底盘账的时候,眉头紧锁地抽烟。
我则守着那一亩三分地的后厨。
我的灶台是不锈钢的,擦得锃亮。
我的刀具摆成一排,整整齐齐。
每天晚上,听着前厅的喧闹声,闻着油烟味,我心里就踏实。
钱,确实赚到了。
第一年,除去开支,我俩分了二十万。
第二年,翻了一番,分了四十万。
到了第三年,也就是去年,净利润突破了两百万。
这在我们这个小城市,对于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笔巨款。
我们没买豪车,也没去挥霍。
钱都存在一张卡里,卡在我这儿,密码是我们俩的生日。
我觉得这是信任。
赵铁柱说:“阿鸣,你心细,钱放你那儿我放心。”
可人心,是会变的。
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
大概是半年前吧。
那天我在后厨忙完,出来透口气,看见赵铁柱在角落里打电话。
他背对着我,声音压得很低,但语气很兴奋。
“……对,地段我看好了,就在市中心那个新商场旁边。人流量绝对大……”
“……钱?钱不是问题,我这边有渠道……”
我心里“咯噔”一下。
他要开店?怎么没听他说过?
等他挂了电话,我走过去,递给他一瓶冰水。
“铁柱,刚听你说要开新店?”
他愣了一下,随即接过水,拧开猛灌了一口,掩饰着尴尬。
“啊,是……是有这个想法。这不是想着做大做强嘛。”
“那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我来了兴致,“位置选哪儿?资金大概要多少?”
他眼神闪烁,避开我的目光,含糊地说:“还在看,还在看。八字没一撇的事。”
那一刻,我隐约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劲了。
接下来的日子,他变得越来越忙。
经常找不到人,电话也不接。
店里大大小小的事,基本都落在我一个人头上。
前厅服务员跟我抱怨,说赵经理最近脾气大,动不动就骂人。
供货商也跟我打电话,说赵经理答应的结款日期一拖再拖。
我找他谈。
他总是摆摆手,一脸不耐烦:“阿鸣,你别管这些琐事。你安心把菜做好就行。我现在在谈一笔大生意,谈成了,咱们店能上一个大台阶。”
“大生意?什么大生意?”我问。
“哎呀,你不懂,商业上的事说了你也不明白。”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里带着一丝我不喜欢的优越感。
我是不懂。
我只知道,我俩之间,隔了一堵看不见的墙。
真正的爆发,是在上周。
那天晚上盘点,我发现账目不对劲。
有一笔三十万的支出,没有单据,去向不明。
我拿着账本找到他。
他正在办公室里,翘着二郎腿,手里夹着烟,烟雾缭绕。
“铁柱,这三十万,是花哪儿了?”
他眼皮都没抬,淡淡地说:“应酬花了。”
“应酬?”我火气一下就上来了,“什么应酬能花三十万?赵铁柱,你把我当傻子吗?”
他终于抬起头,看着我。
那眼神,很陌生。
没有了以前的憨厚和热忱,只剩下冷漠和审视。
“阿鸣,你发什么火。店是我管的,我花点钱怎么了?”
“店是你的?这店是我俩合伙开的!”我吼道。
他笑了,是那种冷笑。
他站起身,走到我面前,比我高半个头,身上那股子熟悉的汗味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浓烈的古龙水味,呛得我难受。
“合伙?阿鸣,你搞清楚。这店,从头到尾,是谁在跑关系?是谁在拉客源?是谁在应付那些乱七八糟的人?”
他指了指后厨的方向。
“你呢?你就守着那个灶台,炒炒菜,别的事,你懂吗?你管过吗?”
我被他这番话震住了。
我看着他,像看一个陌生人。
“赵铁柱,你摸着你的良心说话。没有我的味道,没有‘鸣记’这块招牌,你那些关系,那些客源,管个屁用!”
“招牌?”他嗤笑一声,“阿鸣,时代变了。现在做生意,靠的是脑子,是人脉,不是你那一锅蛙。我随便找个厨师,都能做出你那个味儿。”
这句话,像一把刀,直直插进我心里。
我最引以为傲的东西,在他眼里,一文不值。
“所以呢?”我声音发抖,“所以那三十万,是你自己吞了?”
“别说的那么难听。”他掐灭了烟,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拍在桌上。
“这是三十万的银行本票。还有一份退伙协议。”
我脑子“嗡”的一声。
“你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他直视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这店,我要了。你拿三十万,退出。”
空气仿佛凝固了。
办公室里只剩下老旧空调的嗡嗡声。
我看着桌上那张薄薄的本票,再看看眼前这个跟我一起吃了三年苦、睡过地板、喝过同一瓶酒的兄弟。
突然觉得无比荒唐。
“三年,两百万。”我喃喃自语,“我只值三十万?”
“陆鸣,这是溢价了的。”赵铁柱的语气平静得可怕,“按理说,你这几年在后厨,也就算个技术入股。大头是我跑出来的。给你三十万,我已经够意思了。”
“够意思……”我重复着这三个字,想笑,却笑不出来。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我死死忍住了。
我不能在他面前哭。
我深吸一口气,胸口疼得厉害。
我想起了三年前,那个蹲在垃圾桶边喝酒的夜晚。
他说:“阿鸣,等咱们赚钱了,你就是大厨,我就是掌柜。”
现在,掌柜的要踢走大厨了。
我抬起头,迎上他的目光。
办公室里光线很暗,只有一盏台灯亮着,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扭曲。
我看到他眼神里有一丝躲闪,但更多的是一种决绝。
我知道,没得谈了。
这不仅仅是为了钱。
对他来说,这可能是一场“商业决策”。
对我来说,这是背叛。
但我能怎么办?
去闹?去撕破脸?
把事情闹大了,店也就毁了。
两百万,最后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
而且,我真的累了。
跟一个已经变了心的人去争辩是非对错,是最愚蠢的行为。
我沉默了很久。
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心里的愤怒、委屈、不甘,像岩浆一样翻滚。
但最后,都冷却成了灰烬。
我伸出手,拿起了那张银行本票。
纸张很薄,却感觉有千斤重。
“好。”我说。
声音沙哑,但很平静。
赵铁柱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干脆,他愣了一下,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
但我没给他机会。
我拿起桌上的笔,在那份退伙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陆鸣。
两个字,写得歪歪扭扭,像在发抖。
签完字,我把笔一扔,转身就走。
“阿鸣……”他在身后叫了一声。
我没回头。
“以后……保重。”
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干涩。
我走到门口,手握住门把手,停顿了一下。
“赵铁柱。”
我叫了他的全名。
“这店,你好好干。”
说完,我拉开门,走了出去。
外面,前厅依旧灯火通明,人声鼎沸。
食客们在高声谈笑,服务员端着盘子穿梭。
那口熟悉的、巨大的炭火锅正在沸腾,红油翻滚,香气四溢。
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但我知道,有什么东西,永远地碎了。
我走出店门,晚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
我抬头看天,没有星星,只有一片灰蒙蒙的黑。
我捏紧了手里的那张本票。
三十万。
这是我用三年青春、三年汗水、三年兄弟情换来的。
值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从今晚开始,我不再是“鸣记”的厨师陆鸣了。
我只是一个拿着三十万,被兄弟踢出局的失败者。
不。
我突然站定了脚步。
我转过身,看着“鸣记炭火牛蛙馆”那块霓虹闪烁的招牌。
招牌是我设计的,字体是我选的,连灯管的走向都是我盯着电工装的。
赵铁柱,你以为踢走我,这店就是你的了吗?
这味道,这招牌的灵魂,是刻在我骨子里的。
你拿不走。
一股莫名的劲儿,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我笑了。
笑得比哭还难看。
“赵铁柱,咱们走着瞧。”
我低声说。
然后,我头也不回地,消失在夜色里。
这三十万,不是结束。
是我的开始。
我要用这三十万,重新开始。
我要开一家比“鸣记”更好吃的店。
我要让他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味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意。
……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过得浑浑噩噩。
我搬出了我和赵铁柱合租的房子,只带走了几件衣服和我的厨刀。
我在老城区租了个单间,窗户对着隔壁楼的墙,终日不见阳光。
那三十万,我没动。
它静静地躺在银行卡里,像一个讽刺的笑话。
我每天睡到中午才醒,醒来就点外卖,刷手机,看那些无聊的短视频。
我试图忘记“鸣记”,忘记赵铁柱。
但味觉的记忆是顽固的。
走在路上,闻到路边摊的油烟味,我会下意识地想,这个辣椒不够香,应该是先用热油把干辣椒的香味激发出来,再下锅……
看到有人在吃牛蛙,我会想,这只蛙的腿肉不够饱满,肯定是养殖时间不够……
我像个后遗症患者,无时无刻不被过去纠缠。
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
赵铁柱说得对吗?
我是不是真的只会炒菜?
离开他,我是不是什么都不是?
这种自我否定,比亏了两百万还难受。
直到有一天。
那天下午,我无所事事地在街上溜达。
不知不觉,走到了“鸣记”附近。
我不敢靠太近,就躲在街角,远远地看着。
店门口停着好几辆豪车。
我看见赵铁柱穿着一身笔挺的名牌西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正满面春风地跟几个一看就是大老板的人握手。
他递烟,点火,动作娴熟,笑容得体。
那样子,完全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再也不是那个光着膀子、浑身是汗的铁柱了。
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
突然,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店里跑出来。
是小李,以前店里的服务员,也是跟着我们最早的一批员工。
小李跑到赵铁柱身边,焦急地指着店里,好像在说什么。
赵铁柱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他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似乎在赶小李走。
小李急得快哭了,拉着他袖子不放。
赵铁柱一把甩开小李的手,吼了一句什么。
距离太远,我听不清。
但我看到小李踉跄了一下,蹲在地上,肩膀一耸一耸的,像是在哭。
那一刻,我心里那团熄灭的火,“腾”地一下,又燃了起来。
小李是个很老实的农村孩子,刚满二十,平时话不多,但干活特别卖力。
以前我教他切土豆丝,他切不好,急得满头大汗。
我就跟他说:“别急,心静下来,刀就稳了。”
他点点头,真的就练了一下午,把手都切破了,还傻笑着说:“陆哥,你看,这次是不是匀称多了?”
这样一个孩子,现在被赵铁柱像狗一样吼。
为什么?
因为店里的事?
我忍不住了。
我走了过去。
赵铁柱正忙着招呼那几个老板,没看见我。
我走到小李身边,拍了拍他的背。
“小李,怎么了?”
小李抬起头,看到是我,眼泪“唰”地就下来了。
“陆哥……”
“哭什么!”我皱起眉,“天塌下来了?”
“店……店里的生意……”他抽噎着说,“自从你走了之后,味道就变了。好多老客都不来了。赵经理不知道从哪儿找了个新厨师,那厨师脾气大得很,天天跟赵经理吵架。今天……今天又有客人因为味道不对,在店里闹起来了……”
我心头一紧。
果然。
“赵铁柱呢?”我问。
“他在外面陪客人……说……说这是小事,让我别烦他……”
我转过头,看着正跟人谈笑风生的赵铁柱。
他脸上的笑容,那么刺眼。
我径直朝他走去。
“赵铁柱。”
他听到我的声音,身体一僵,转过身来。
看到是我,他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
“你来干什么?”他压低声音,语气里满是厌恶。
“我来看看我的店。”我平静地说。
“你的店?”他冷笑,“陆鸣,协议都签了,钱也给你了,这店现在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赶紧滚,别在这儿影响我谈生意。”
那几个老板好奇地看着我们。
我没理会他的话,而是看向店里。
透过玻璃门,我看到后厨门口,一个穿着厨师服的胖子正指着一个洗碗工骂骂咧咧。
那就是他找的新厨师?
“味道不对了,是吗?”我问。
赵铁柱眼神闪烁了一下,嘴硬道:“新口味,顾客需要适应期。”
“适应期?”我笑了,“赵铁柱,你懂什么叫味道吗?‘鸣记’的味道,不是随便找个厨师就能模仿的。那是我试了几百次,调出来的平衡。麻辣鲜香,每一种味型都要精准。你那个厨师,火候都掌握不好,炒出来的底料,糊味都压不住。”
我的话像连珠炮,砸得赵铁柱脸色发白。
他没想到,我离得这么远,还能看出门道。
“你……你懂什么!”他恼羞成怒,“我这是在做品牌,做连锁!味道只是一方面!”
“品牌?”我指着蹲在地上的小李,“这就是你做品牌的方式?把老员工当出气筒?把顾客的投诉当耳旁风?”
“赵铁柱,你忘了。‘鸣记’之所以能火,靠的不是你的关系,也不是你的人脉。靠的是每一个吃到嘴里的人,都觉得值。靠的是小李这样的员工,一杯水、一张纸巾递出去的那份心。”
我的声音不大,但周围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那几个老板面面相觑,表情变得玩味起来。
赵铁柱的脸涨成了猪肝色。
“你给我闭嘴!”他嘶吼道,像一头被激怒的困兽。
“我偏要说。”我往前逼近一步,直视着他的眼睛,“你以为踢走我,你就能高枕无忧了?你错了。厨师的魂,你拿不走。没有了灵魂的菜,就是一堆没有生命的垃圾。”
“你……”他扬起手,似乎想打我。
但我站在那里,纹丝不动。
我的眼神,比他更冷,更硬。
他最终还是没敢落下来。
因为他知道,一旦动了手,理就全在他对面了。
“滚。”他从牙缝里挤出这个字。
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转身,扶起小李。
“走,陆哥带你吃好吃的。”
我没再回头,带着小李离开了这个让我爱过、也恨过的地方。
那天晚上,我请小李吃了顿烧烤。
他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
他说赵铁柱接手后,为了缩减成本,换了便宜的辣椒,用了冷冻的蛙肉,连配菜都开始用质量差的。
他说赵铁柱现在整天忙着应酬,根本不关心店里的情况。
他说他很想我,很想以前大家一起奋斗的日子。
我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
但也就在那一刻,我彻底想通了。
我不应该颓废。
我不能让“鸣记”这块招牌,毁在赵铁柱手里。
更不能让那些信任我的人,失望。
我拿出那张三十万的银行卡,拍在桌上。
“小李,想不想跟我重新干?”
小李的眼睛,瞬间亮了。
……
我开始行动了。
第一步,找店面。
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只盯着后厨。
我开始研究市场,研究人流,研究消费心理。
我拿着本子,跑遍了全城。
最后,我在城东一条新开的商业街上,看中了一个铺面。
那里离市中心有点距离,但旁边新建了几个大型小区,年轻人多,消费潜力巨大。
最关键的是,房租便宜。
我用二十万,签下了三年的租约。
第二步,装修。
我没钱请设计师。
我自己画图纸,自己跑建材市场。
为了省钱,我跟装修师傅磨嘴皮子,一根钉子、一块板子地砍价。
小李也跟着我,忙前忙后。
我们把墙刷成温暖的米黄色,灯光明亮,桌椅选了原木色的,看起来干净又舒服。
第三步,招人。
我把以前跟着我的几个老员工都联系了一遍。
他们有的去了别的店,有的还在待业。
听到我要重新开店,有三个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陆哥,我们信你。”
就这简简单单一句话,让我差点掉下眼泪。
第四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定菜单。
我把自己关在新店的后厨里,整整一个星期。
我不再执着于复制“鸣记”的味道。
我要创造新的味道。
我研究了市面上所有的牛蛙做法,粤式的、湘式的、泰式的……
我尝试把不同的香料组合在一起。
我失败了无数次。
垃圾桶里堆满了炒废的底料。
我的手被油烫出了好几个泡。
但我越做越兴奋。
我感觉那个熟悉的自己,又回来了。
终于,在一个深夜,我炒出了一锅自己满意的底料。
我叫来小李和几个员工试菜。
他们吃完,眼睛都直了。
“陆哥,这个味……绝了!”
“比‘鸣记’的还好吃!真的!”
我尝了一口。
麻辣依旧,但多了一丝清香,回味还有一点点甜。
那是我加了新鲜藤椒和一点点冰糖的缘故。
我给这道菜取名,“涅槃”。
寓意浴火重生。
店名,我也想好了。
就叫“鸣人牛蛙馆”。
“鸣人”,既是我的名字“鸣”,也寓意着,这是真正懂味道的人,才懂的馆子。
开业那天,没有花篮,没有剪彩。
只有我和我的小团队。
我们把门一开,静待客人。
一开始,街上人来人往,却没人走进这家不起眼的小店。
小李很紧张,不停地在门口张望。
我拍拍他的肩膀:“别急,好味道,自己会说话。”
下午五点,终于有一对年轻情侣走了进来。
他们大概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我亲自下厨,做了两份“涅槃”。
蛙肉端上去的时候,那股独特的香气,立刻吸引了周围几桌人的目光。
五分钟后,那个女孩发出一声惊呼:“天呐,这个蛙好好吃!男朋友,你快尝尝!”
她的声音很大,很兴奋。
紧接着,那个男孩也发出了赞叹。
这一嗓子,像打开了开关。
旁边桌正在犹豫的人,立马喊道:“老板,我们也来一份这个!”
“我要微辣的!”
“我要加一份方便面!”
那一刻,我知道,我成了。
接下来的日子,“鸣人牛蛙馆”火了。
不是靠营销,不是靠炒作。
纯粹靠口碑。
吃过的客人都说,城东新开的这家蛙馆,味道一绝。
那种层次丰富的麻辣,让人欲罢不能。
我的小店,从一开始的几张桌子,到后来需要排队等位。
最多的时候,门口等了一百多号人。
我忙得脚不沾地,每天睡不到四个小时。
但我的心里,是满的,是热的。
我看着账本上的数字,从几千,到几万,再到十几万。
我心里没有那种暴富的狂喜,只有一种踏实的成就感。
这钱,是我一勺一勺炒出来的,干净,心安。
……
赵铁柱那边,显然也听到了风声。
我听说,他好几次派人来我店里“考察”。
甚至还派了以前认识的熟人,想来挖我的厨师。
可惜,我的团队,都是跟我共患难过来的,心很齐。
他无功而返。
又过了两个月。
那天晚上,我正在后厨炒料,赵铁柱来了。
他一个人来的。
没穿西装,只是一件普通的T恤,人看起来憔悴了很多,眼窝深陷。
他站在嘈杂的店里,显得格格不入。
我炒完手里的锅,擦了擦手,走了出去。
“稀客啊。”我递给他一支烟。
他接过去,点上,猛吸了一口,被呛得直咳嗽。
“生意……真好。”他看着周围排队的人,声音干涩。
“还行,混口饭吃。”我淡淡地说。
沉默。
空气里弥漫着尴尬和油烟味。
“阿鸣,”他终于开口,“我那店,快黄了。”
我一点都不意外。
“那个厨师,我辞了。我又找了一个,还是不行。老客都跑光了,现在天天亏钱。”他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我听说了。”我说。
“我……我当初是不是做错了?”他抬起头,眼里满是血丝,带着一丝祈求看着我,“阿鸣,你……你能不能回来?我们还像以前一样,我给你……给你一半的股份!”
我看着他。
这个曾经我以为会是一辈子兄弟的人。
现在在我面前,说着后悔。
我心里没有报复的快感,只有一种深深的疲惫和悲哀。
“铁柱,回不去了。”我平静地说。
“为什么?!”他激动起来,“我们是兄弟啊!”
“兄弟?”我笑了,笑得有些苍凉,“兄弟,不是用来算计的。你当初拿三十万让我出局的时候,就没想过我们是兄弟。”
“我那是……我那是为了生意!”他辩解道。
“不,你那是为了你自己。”我掐灭了烟,“赵铁柱,生意场上,你可以精明,可以算计,但不能没了良心。你换了食材,克扣员工,你忘了本。”
“菜有菜道,人有人道。你的道,歪了。”
我指了指我的后厨,那里热气腾腾,香气四溢。
“我的道,还在这儿。”
“这锅里,炒的是我的手艺,也是我的人心。你学不来的。”
赵铁柱愣住了。
他看着我,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最后,他颓然地站起身,转身往外走。
他的背影,佝偻着,再也没有了当年扛麻袋的意气风发。
走到门口,他停住了。
没有回头,只是低声说了一句:“阿鸣,对不起。”
我没说话。
只是看着他,消失在夜色里。
……
后来,我听说,“鸣记炭火牛蛙馆”倒闭了。
赵铁柱把店盘了出去,听说还欠了一屁股债。
他离开了这个城市,不知去向。
而我的“鸣人牛蛙馆”,生意越来越好。
我在城南和城西,又开了两家分店。
我还是坚持每天去后厨,亲自炒制底料。
有人劝我,现在规模大了,可以搞中央厨房,统一配送。
我拒绝了。
我说,味道是餐饮的根,根不能离开土。
我依然住在那个老城区的单间里,虽然我现在买得起市中心的豪宅了。
我依然喜欢穿着简单的T恤,穿梭在烟火气里。
不同的是,现在的我,身边围绕着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
小李已经成了三家店的总店长,成熟稳重,再也不是那个会哭鼻子的毛头小子了。
有时候,深夜打烊,我会一个人坐在店里,看着墙上挂着的那张我和赵铁柱当年在“鸣记”门口的合影。
照片已经泛黄。
我会倒上一杯酒,敬过去,也敬未来。
我感谢那段被背叛的经历。
它像一把淬火的刀,把我从一块废铁,锻造成了钢。
它让我明白,真正的成功,不是赚多少钱,不是拥有多少人脉。
而是守住自己的本心,做好手里的事,对得起吃进嘴里每一口饭的人。
窗外,霓虹闪烁。
我的“鸣人牛蛙馆”招牌,亮得温暖而坚定。
我知道,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而那个关于兄弟、关于背叛、关于重生的故事,已经翻篇了。
未来的路,还很长。
但我不怕。
因为我的手里,有勺。
我的心里,有光。
我和兄弟合伙开饭店,3年赚了200万,他拿30万让我退出 我点头同意
我和兄弟合伙开饭店,3年赚了200万,他拿30万让我退出 我点头同意
我叫胡立军。
这名字是我爹给起的,他说希望我像胡杨一样,立在戈壁滩上也死不了,还能长得又高又大。
可惜我没活在戈壁滩,我活在城里,活在油烟里,活在钱堆里,也活在背叛里。
那家叫“兄弟烧烤”的店,就在老城区的夜市里,霓虹灯管拼出的四个字,一半已经不亮了,晚上看着跟“兄弗烧火”似的,有点滑稽,也有点悲凉。
三年前,不是这样的。
那时候,我和王自健,我们俩,兜里加起来凑不齐两万块,就敢盘下这个五十平米、墙皮往下掉渣、地砖缝里能抠出半斤油泥的破铺子。
王自健是我发小,光屁股长大的那种。
他这人脑子活,嘴比蜜甜,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呢,我闷,我只会烤串,我认的调料比我认的字儿都多。
开店那天,我们俩在空荡荡的店里,就着马扎子,喝了一箱冰啤酒。
王自健搂着我肩膀,眼睛亮得跟探照灯似的,他说:“军儿,咱俩以后就是这城里的爷!”
我说:“嗯。”
他一拳捶我胸口:“别光嗯啊,说点豪气的!”
我憋了半天,指着墙上那张歪歪扭扭的菜单说:“咱家的腰子,必须是全城最嫩的。”
王自健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行!就冲你这句话,干了!”
那天晚上,我们俩喝得东倒西歪,躺在刚擦干净的地板上,看着天花板上摇摇欲坠的旧灯管,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我们脚下。
创业的苦,是泡在汗水里的。
每天下午四点,我就得去批发市场,跟那些卖肉的、卖菜的、卖调料的老板斗智斗勇。王自健负责店里的一切杂活,擦桌子、洗碗、换煤气,什么都干。
晚上六点,夜市开张,我们俩就像上了发条的机器。
我守着烤炉,那火苗子蹿起来能燎了眉毛,夏天围着那个炉子,就跟进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没区别,浑身的汗顺着裤衩往下淌,有时候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在炼“人油”。
王自健在前头招呼客人,他那张嘴,死的都能说成活的。
“哥,您来啦!今儿个想吃点啥?刚到的羊排,肥得流油,烤出来滋滋冒响,保准您吃了这顿想下顿!”
“美女,看你这气色,今天肯定有好事,来,这串板筋送你的,脆生生的,吃了心情更好!”
“哎哟,李哥,您可有日子没来了,是不是兄弟我哪伺候得不周到?您言语一声,我立马给您改!”
他就这么一张嘴,把周围的街坊邻居、上班的、跑车的,都变成了回头客。
店里最忙的时候,一张小桌子能挤八个人,马扎子都得从隔壁店借。点菜声、划拳声、啤酒瓶子碰撞声,混着烤肉的孜然味和炭火烟味,能把人的魂儿都给熏醉了。
我俩配合得天衣无缝。
我在后厨喊一声:“三号桌,加十串瘦的,多放辣!”
王自健在前台立马回一句:“好嘞!军儿,三号桌加辣,手稳着点!”
有时候忙得连口水都喝不上,半夜两三点,客人走光了,我们俩瘫在椅子上,看着满地的竹签子和啤酒瓶,谁也不想动。
王自健会扔给我一根烟,自己点上一根,深吸一口,吐出的烟雾在昏黄的灯光下缭绕。
“军儿,累不?”
“不累。”我嘴硬。
“吹吧你。”他笑,“等咱赚了钱,换个大点的店面,装上空调,你就在后厨,不用再跟火炉子拼命了。我呢,就在前头当老板,数钱数到手抽筋。”
“嗯。”我应着,心里想着,到时候我得换个好点的烤炉,温控更准,烤出来的腰子肯定更嫩。
那时候,我们是真的兄弟。钱,都放在一个抽屉里,谁要花钱谁就拿,从不记账。家里有啥事,对方的事就是自己的事。王自健他爸生病,我二话不说,把准备换手机的五千块钱全取出来给了他。我爸腰间盘突出,王自健跑前跑后,找医院、托关系,比我还上心。
我们觉得,这辈子,就这么过了。一起开个店,一起变老,一起看着孩子长大,再一起喝着酒吹牛逼。
第一年,我们还清了外债,还剩下十几万。
第二年,我们把隔壁的铺子也盘下来了,店扩大了一倍,装修得亮堂堂的。我们招了两个服务员,一个叫小娟,一个叫小丽。王自健还给自己买了辆二手的帕萨特,每天开着车来店里,人五人六的。
第三年,也就是今年,生意好到爆炸。夏天那几个月,一天营业额能破两万。我们粗粗算了一下,三年下来,除去所有开销,纯利润,大概有两百万。
两百万。
对于两个从破巷子里走出来的穷小子来说,这简直是一笔天文数字。
我们开始商量着,要不要去市里最好的地段,开个分店。或者,干脆不干了,把店转出去,拿着钱做点别的生意,当真正的“老板”。
我甚至都想好了,拿到钱,第一件事就是回老家,给我爸妈盖一栋小楼,再给他们买辆代步车。
我以为,王自健也是这么想的。
直到上周二,一个普通的、客人不算太多的晚上。
那天我有点感冒,脑袋昏沉沉的,烤串的时候都有点不在状态。王自健看出来了,让我早点回去休息,他说他一个人能行。
我心里还挺感动的,觉得这兄弟没白交。
我回去睡了一觉,第二天下午精神好了些,就提前去了店里,想替替他。
我推开后厨的门,没看见人。喊了一声“自健”,也没人应。
我以为他在前堂,正准备过去,却听见后厨通往二楼储藏室的楼梯上有声音。那是王自健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打电话。
我本来没想偷听,可他接下来的一句话,像根冰锥子,一下子扎进了我耳朵里。
“……放心吧,他那边我搞得定。三年,两百万,他拿三十万走人,够意思了。”
我的脚,像被钉在了原地。
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王自健又说:“什么兄弟不兄弟的,生意就是生意。他那手艺是不错,但也就值这个价了。现在这店,缺了我王自健,一天都转不下去。他胡立军?他除了会烤几串破腰子,还会干啥?人脉?资源?他懂个屁!”
“行了行了,别废话了,就这两天,我跟他摊牌。你那边准备好合同,钱一到账,咱就干票大的。”
我站在门后,浑身的血都往头顶上涌。
厨房里还残留着昨天没散尽的油烟味,混着香料的气息,平时闻着那么亲切,今天却让我一阵阵地犯恶心。
我脑子嗡嗡响,眼前全是三年来的一幕幕。
我们俩在破店里,就着花生米喝一块钱一瓶的啤酒。
他把最后一个鸡翅夹到我碗里,说:“军儿,你多吃点,你干活累。”
我爸做手术,他守在手术室外头,比我还紧张。
他开着那辆破帕萨特,带我去海边,说等有钱了,买艘游艇,咱俩出海钓鱼。
……
那些画面,此刻都变成了一个个巴掌,狠狠地扇在我脸上。
我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像个贼一样,走出了店门。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
我想了很多。我想冲回去质问他,想把桌子掀了,想揍他一顿,想问他为什么。
可最后,我什么都没想出来。
我就是觉得冷,从骨头缝里往外冒冷气。
第三天,王自健给我打电话,说晚上一起吃个饭,聊聊分店的事。
我们约在一家挺高档的餐厅,以前我们总来这儿吃,觉得这儿的菜有档次。现在看着,只觉得讽刺。
王自健穿了件新衬衫,头发也做了,看起来容光焕发。
他给我倒茶,夹菜,热情得像是我们刚认识那会儿。
“军儿,最近辛苦了。看你脸色不太好,多补补。”
我没什么胃口,扒拉着碗里的米饭,等着他开口。
他知道我是个急性子,藏不住事,看我这样,也就不再绕弯子了。
他放下筷子,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还有一个厚厚的信封,推到我面前。
“军儿,你是我最好的兄弟,有些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必须得说。”
我没看他,盯着那份文件。
“这是什么?”
“这是……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他顿了顿,似乎在组织语言,“你看,现在店也做大了,咱们不能总守着这一个店。我想,把店盘出去,或者,我再投点钱,咱们去市中心开个大的,做连锁。但是……”
他话锋一转,眼神开始躲闪。
“但是什么?”我抬起头,直视着他。
“但是,咱们的模式太传统了,需要升级。我认识一个做餐饮投资的朋友,他很看好咱们的牌子,想入股。但是,他提了个条件……他说,合伙人不能太多,意见不统一,不好搞。最好是……一个人说了算。”
他说得磕磕巴巴,但我全听懂了。
我指了指那个信封:“这里面是什么?”
“三十万。”他声音低了下去,“这是我能给你的最大诚意了。这三年,你辛苦了。我知道,你家里也需要钱。这三十万,你拿着,回去做点小生意,或者休息一段时间。店,我来经营。你放心,你永远是咱们‘兄弟烧烤’的元老,以后每年,我给你分红。”
他说完,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恳求,一丝愧疚,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
空气凝固了。
餐厅里悠扬的音乐,邻桌客人的欢笑声,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我看着他,这个我睡在上下铺、一起偷过邻居家西瓜、一起在工地上扛过水泥的兄弟。
他的脸,突然变得那么陌生。
我笑了。
不是冷笑,也不是苦笑,就是很平静地笑了。
王自健愣住了,他可能以为我会暴怒,会掀桌子,会指着他的鼻子骂他忘恩负义。
但他想错了。
我只是觉得,这事儿,的可笑。
两百万,三十万。
一个兄弟,一个“老板”。
这笔账,算得真清楚。
我伸出手,把那个信封拉到自己面前,用手指弹了弹。
“行。”
我说。
王自健的眼睛瞬间瞪大了,充满了难以置信。
“行?”他重复了一遍,好像没听清,“你是说……同意?”
“嗯。”我点点头,把文件拿过来,看都没看,直接翻到最后一页,拿起桌上的笔,签上了我的名字——胡立军。字写得龙飞凤舞,是我这辈子签得最潇洒的一次。
签完,我把文件和笔一起推了回去。
“钱,我拿着。店,是你的了。”
我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王自健,从今天起,咱俩,桥归桥,路归路。”
说完,我拿着那个装着三十万的信封,转身就走。
身后传来王自健有些慌乱的声音:“军儿,你……你听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没回头。
我怕一回头,他会看见我通红的眼眶。
走出餐厅,外面的天已经黑了。城市的霓虹灯一盏盏亮起来,晃得人眼睛疼。
我走在街上,手里捏着那个信封。三十万,很厚,但拿在手里,却感觉轻飘飘的,像一沓废纸。
我不知道我该去哪儿。
回家?我租的那个小单间,此刻回去,只会觉得更憋闷。
回店里?不,那里已经不是我的店了。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不知不觉,竟然走到了我们那个“兄弟烧烤”的门口。
店还没打烊,门口停着几辆车。霓虹灯“兄弗烧火”依旧亮着,只是“自”字和“烧”字的灯管,坏得更厉害了,一闪一闪的,像个濒死的病人。
我看见王自健的帕萨特停在不远处。
我站在马路对面,点上一根烟,看着。
一个服务员出来倒垃圾,是小娟。她看见我,愣了一下,想打招呼,我朝她摆了摆手,让她别出声。
我看着店里人来人往,看着王自健在前台忙活,他还是那副笑呵呵的样子,跟客人插科打诨,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一根烟抽完,我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
心里那股翻江倒海的劲儿,突然就平息了。
我掏出手机,给王自健发了最后一条微信。
“账本我看过,这三年,除去所有开销,净利润是二百一十三万。按规矩,我该拿一百零六万五。你给了我三十万,剩下的七十六万五,就当是我给你随的份子钱。祝你,新婚快乐,生意兴隆。”
发完,我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做完这一切,我把手机揣回兜里,感觉浑身都轻松了。
我胡立军,从今天起,又是那个一无所有的胡立军了。
不,也不是一无所有。
我还有三十万。
和一身,从油烟里滚出来的本事。
我转身,走进了深沉的夜色里。
……
离开王自健的第一周,我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睡了整整三天。
睡醒了,就点外卖,吃完了继续睡。
我好像要把这几年欠下的觉,全都补回来。
第四天早上,我被饿醒了。冰箱里什么都没有,只有半瓶快过期的牛奶。
我一口气喝完那瓶冰凉的牛奶,胃里一阵抽搐,人也彻底清醒了。
我不能就这么颓下去。
我开始出门,像个幽灵一样,在城市里游荡。
我去了我以前最爱去的几家烧烤店,以前是去学习,去品尝,现在是去……品尝,但味道全变了。
我吃了“东北大串”,味道太重,香料盖过了肉味。
我吃了“新疆风味”,羊肉腌得不错,但烤得太老。
我吃了“日式烧鸟”,精致是精致,但没有烟火气。
我坐在一家装修得富丽堂皇的烧烤店里,看着菜单上那些花里胡哨的名字——“火焰和牛”、“芝士焗扇贝”、“黑松露烤蘑菇”,突然觉得一阵反胃。
这他妈的,还是烧烤吗?
这他妈的,还是我认识的那个烧烤吗?
我想起了我和王自健的店。
我们的菜单,永远是那几样:羊肉串、羊腰子、鸡翅、板筋、烤韭菜、烤茄子。简单,粗暴,直接。
我们的客人,也都是些普通人。他们来这儿,不是为了吃什么情调,就是为了大口吃肉,大口喝酒,释放一天的疲惫。
王自健总说,做买卖,你得懂人心。人心是什么?就是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大的快乐。
我们的快乐,就是那一串串滋滋冒油的肉,和那一杯杯冰到透心凉的啤酒。
现在,这些东西,好像都消失了。
我走了三家店,花了三百多块钱,没一顿吃得舒服。
最后,我在一个犄角旮旯里,找到一个老大爷推着车卖的烤串。
摊子很小,就一个炉子,几张破桌子。
老大爷手脚慢,但每串肉都串得实实在在。
我要了十串羊肉,五串板筋。
老大爷烤得很认真,火候拿捏得死死的,撒料的动作,跟我在老家学艺时,我师傅一模一样。
肉串拿在手里,还烫着。
我咬了一口。
就是这个味儿。
不是那种放了嫩肉粉、香精的工业味,是羊肉本身的味道,混着炭火的焦香,和孜然辣椒的原始刺激。
我吃得眼眶有点热。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
王自健说得对,我胡立军,除了会烤几串破腰子,确实啥也不会。
可这又怎么样?
只要这世上还有人想吃这“几串破腰子”,我胡立军就饿不死。
我找到了我的道。
第二天,我揣着那三十万,去了工商局。
我要办营业执照,我要开一家属于我自己的店。
我跑了半个月,腿都快跑断了,终于把所有手续都办了下来。
然后是找地方。
我不想再去夜市里跟人挤,也不想再看那些混混的脸色。
我把目标锁定在了一些老小区的周边。这些地方,住的都是些上了年纪的本地人,或者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消费不高,但对味道的要求,很挑剔。
最后,我在一个叫“红旗二村”的老小区门口,找到了一个铺子。
铺子不大,三十平米,之前是个五金店,转让费不贵。
我签了合同,拿到钥匙的那天,天上下着小雨。
我站在空荡荡的店里,雨水顺着破旧的窗框往下流。
我拿出纸笔,开始画草图。
这里,放烤炉,要离墙远一点,通风要好。
那里,放冰柜,要能放下三百斤肉。
前面,摆六张桌子就够了,多了坐不下,显得挤。
墙上,不用霓虹灯,我就刷白,然后挂上我自己的菜单,用毛笔写,字丑点没事,但要清楚。
店名,我想好了,就叫“老地方烧烤”。
不,还是叫“胡立军烧烤”吧。
或者,就叫“腰子王”?
我想了半天,最后决定,就叫“兄弟烧烤”。
不,这名字被王自健占了,晦气。
最后,我写下了四个字:“一串江湖”。
对,一串江湖。
我胡立军的江湖,就在这几串肉里。
装修是个大工程。
为了省钱,我自己干。
我白天去建材市场买材料,晚上回来自己刷墙、铺地砖。
以前在店里,我拿的是烤串的手,现在拿的是油漆刷子和锤子。
手上磨出了血泡,胳膊酸得抬不起来。
但我心里,踏实。
我把我所有的积蓄,那三十万,除了留下三万块周转,剩下的二十七万,全都投了进去。
我换了最好的烤炉,能精确控制温度的那种。
我买了全新的冰柜和冷鲜柜。
我定制了最厚实的实木桌子和椅子,坐上去稳稳当当的。
我还买了一套顶级的音响。
开业那天,我没搞什么仪式,没请什么朋友。因为,我也没有什么朋友了。
我就在门口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着:“开业大酬宾,全场八折”。
然后,我点燃了炉子里的第一块炭。
炭火红起来的时候,我的江湖,也开始了。
第一天,只来了三桌客人。是小区里出来遛弯的大爷大妈,看我这儿新开了个烧烤店,进来尝尝鲜。
我给他们烤了几个素菜,没要钱。
他们吃得挺高兴,说小伙子你这手艺不错,比别家干净。
第二天,来了五桌。多了几个年轻人,应该是附近大学的学生。
他们要了啤酒,要了肉串,吃得热火朝天。有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吃完临走时,冲我竖了个大拇指:“老板,你这烤腰子,绝了!”
第三天,客人就坐满了。
我的店,没有服务员,只有我一个人。
前厅后厨,点菜、上菜、结账、烤串,全是我。
我忙得像个陀螺,在烤炉和客人之间来回穿梭。
客人等得久了,我会给他们道个歉,送盘毛豆。
客人喝多了,吐了一地,我默默拿拖把拖干净,再递上一杯温水。
我的店,没有王自健那种天花乱坠的推销,只有实实在在的味道和分量。
我的羊肉串,三块一串,肉串得跟小胳膊似的。
我的烤腰子,十五一串,保证是当天最新鲜的,烤得外焦里嫩,一咬一嘴油。
我的烤韭菜,两块一串,刷的蒜蓉酱是我自己熬的,香得能馋死人。
渐渐地,“一串江湖”的名字,在红旗二村这一片传开了。
人们说,那儿有个老板,话不多,但烤的东西,是真好吃。
我的回头客越来越多。
很多熟客,甚至不用我问,一进门就喊:“老板,老样子,二十串瘦的,十串肥的,两串板筋,一盘毛豆,四瓶啤酒!”
我就在烟熏火燎里,高声回一句:“好嘞!马上!”
每天凌晨两点,我准时关门。
我数着抽屉里一沓沓的零钱,把它们整理好,放进保险箱。
我不再像以前和王自健那样,大手大脚。我每一分钱都算计着花。
我开始记账,每一笔支出,每一笔收入,都写得清清楚楚。
我学会了自己去采购,跟菜市场的老板讨价还价,为了几毛钱的差价,能磨上十分钟。
我变得越来越抠门,也越来越踏实。
我很少去想王自健了。
偶尔,还是会有意无意地听到他的消息。
比如,听客人说,原来的“兄弟烧烤”盘出去了,换了老板,现在改名叫“自健烤坊”,装修得跟个会所似的,价格也翻了一倍,但味道,好像不如以前了。
比如,听人说,王自健跟那个搞投资的朋友闹掰了,因为分赃不均。
比如,听说他买了辆新车,宝马五系,还换了女朋友。
这些消息,像风一样,吹过我的耳朵,留不下一点痕迹。
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我们,早就不是一条路上的人了。
我的“一串江湖”,生意越来越红火。
半年后,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了。
我招了个小伙子,叫赵鹏,也是个不爱说话的,但手脚麻利,肯学。
我把我烤串的手艺,一点点教给他。
“撒料,要用手腕的劲儿,均匀,不能有结块。”
“火候,看肉的颜色,变白,微卷,这时候味道最好。”
“跟客人说话,要笑,但别谄媚,咱们卖的是手艺,不是笑脸。”
赵鹏学得很快。
有了他帮我,我轻松了一些,能把更多精力放在食材的品质和新口味的研发上。
我开始琢磨一些新东西。
比如,用本地的野山椒和泡椒一起烤牛肉,又辣又过瘾。
比如,用黄油和蜂蜜刷在烤面包片上,烤出来奶香十足,成了很多女孩子的最爱。
我还推出了一个“江湖套餐”,适合四个人吃,里面有肉有菜有酒,价格实惠,量又足。
生意好了,烦恼也跟着来了。
周围的烧烤店,开始眼红。
有的开始打价格战,你家羊肉串卖三块,他就卖两块五。
有的开始在背后使坏,说我用的肉不新鲜,是冻肉。
甚至有一次,几个喝醉了的小混混来店里闹事,说我的烤串里有苍蝇,要我赔偿。
我当时正在后厨烤东西,赵鹏跑进来,脸都白了。
我走出去,看着桌上那只死苍蝇,它旁边,是一瓶他们自己带来的啤酒。
我没说话,拿起那只苍蝇,当着他们的面,放进嘴里,嚼了嚼,咽了下去。
“现在,没有了。”我平静地说。
那几个混混愣住了,围观的客人也都愣住了。
他们可能没见过这么解决问题的。
领头的那个黄毛,半天憋出一句:“算你狠!”然后带着人灰溜溜地走了。
从那以后,再没人来我这儿闹过事。
我的“一串江湖”,在这一片,立住了。
又过了一年多,我的店,已经从最初的小铺子,变成了这条街上最火的店。
我买了自己的车,一辆二手的国产SUV,开着它去进货,方便。
我在市里按揭了一套小两居,虽然不大,但总算有了自己的窝。
我把我爸妈接来住了半个月。我妈看着我被烟熏得发黄的手指,直掉眼泪。我爸,那个一辈子没夸过我一句的男人,那天晚上,喝着我烤的串,喝了两杯白酒,红着眼圈对我说:“我儿子,出息了。”
那一刻,我觉得,之前受的所有委屈,都值了。
我的账上,数字也在一点点变多。
三十万的启动资金,早就赚回来了。
然后,是五十万,八十万,一百万……
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每个月,雷打不动,往一张单独的卡里存两万块钱。
那是我给自己存的“养老钱”,也是我给自己存的“底气”。
我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再也不用担心谁会把我踢出局。
我的江湖,我自己说了算。
这天晚上,店里打烊后,我照例在算账。
赵鹏已经回去了,店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把今天的收入点清,存进保险箱,然后坐在那张我亲手挑选的实木椅子上,给自己倒了一杯啤酒。
我打开手机,想刷刷视频,却鬼使神差地,点开了一个本地的美食公众号。
一篇文章的标题,赫然在目:“那个曾经火爆全城的‘兄弟烧烤’,如今安在?”
我点了进去。
文章里,详细写了“兄弟烧烤”的发家史,提到了我和王自健的名字。
文章说,自从王自健独掌大权后,先是盲目扩张,开了三家分店,结果管理跟不上,食材品质下降,口碑一落千丈。
后来又想搞什么“高端烧烤”,人均消费两三百,把老客都吓跑了。
再后来,资金链断裂,合伙人撤资,员工讨薪,官司缠身。
文章的结尾说,上周,最后一家“兄弟烧烤”也关门大吉了。王自健把车卖了,房子也抵押了,据说,现在在工地上搬砖。
我看着手机屏幕,久久没有动。
窗外,夜色正浓。
我端起酒杯,把杯里的啤酒,一饮而尽。
酒还是那个酒,味道,却好像不一样了。
我站起身,走到门口,抬头看着我店门口那块我自己写的招牌——“一串江湖”。
霓虹灯的光芒,温暖而明亮。
我突然想起三年前,我和王自健,在那个破破烂烂的店里,喝着一块钱一瓶的啤酒,他说,他要当城里的爷。
他当过吗?
或许当过吧。
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现在,我胡立军,不求当什么爷。
我只想守着我的一串江湖,烤好我的每一串肉,对得起每一个来我这儿的客人。
这就够了。
我把店门关好,锁上。
钥匙揣进兜里,沉甸甸的。
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脚步,前所未有的轻快。
文档上传者
热门标签
相关文档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