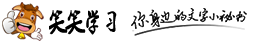欢迎来到98聘
氓作文如何写我教你。(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8-31 11:56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氓”的作文,无论是作为文学评论、历史分析还是个人感悟,都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
"1. 明确“氓”的指代对象和范围 (Clarify the Reference):"
"核心含义:" “氓”在古文中,最核心的含义是指“民”、“百姓”,有时也特指“贫民”、“流民”或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在《诗经·卫风·氓》中,它特指那位被遗弃的女子所控诉的前夫。 "具体语境:" 你需要首先明确你作文中讨论的“氓”是指哪个语境下的群体。是《诗经》中的那个特定人物?是古代社会普遍的贫民?是特定历史时期(如战乱、饥荒)的流民?还是现代社会中处于困境的某个群体?"清晰的界定是全文的基础。"
"2. 深入理解“氓”的境遇和特征 (Deeply Understand Their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生活状态:" 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是贫困、饥寒交迫、战乱频仍,还是缺乏尊严和话语权?具体的生活细节是怎样的? "社会地位:" 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什么位置?受到哪些压迫或不公?他们的权利和保障是什么? "心理状态:" 他们可能有什么样的思想、情感、希望、绝望或反抗?他们的精神
氓的含金量还在升高,在这一刻体现的淋漓尽致!姑娘千万别傻了
氓的命,女人的赌
有一天翻到高中课本那页,《氓》。哎,记得那会儿,大家都说,这女的怎么这么惨?可真糊涂。那么情深意重,最后图个啥呢?岁数大了才发现——其实不只是古代小姑娘,现在的小姑娘,碰上这种事儿,也没几条路能走出去。
那句“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不是随口写着好听的,是说到骨子里的事。你看,那些年我们班上谈起恋爱的男生,失恋了喝两瓶啤酒,大不了发个朋友圈骂骂咧咧,还能照常考试、打球。可女生就不一样——掉眼泪,写小作文,成绩忽上忽下,还要装作若无其事。明明心都碎成一地,还得硬撑着。
想起来最近刷到的一个视频,讲的就是女生的亲身经历。她说,谈了两三年朋友,觉得终于遇到对的人,两家也都同意了,就这么走进了婚姻里。可结婚才半年,那男的变了。吵架摔门,说话越来越冲。隔着屏幕看她掉眼泪,我突然就想起《氓》里的那句——“言既遂矣,至于暴矣”。这世上,多少人恋爱是春风和煦,婚后却云开雨打?故事是古人写下的,现实是今天继续上演的。
说到底,结婚真的是场赌局。姑娘们都知道要小心翼翼,可一旦身子迈进那扇门,怕的就是人心难测啊。我们常说“生米煮成熟饭”,煮完了,不合口味还能倒回去嘛?锅干饭熟,想悔都悔不掉了。
《知否》里盛明兰的话,我每次听都直打心眼儿里赞同。你可以和一个人风花雪月好多年,但一旦成为一家子,終究绕不过对方“最低处”的那个自己。人品、教养、脾气——关键时刻都瞒不住。恋爱时候没发作出来的臭毛病,日子长了,总得露个马脚。你能不能忍住、撑住,这婚姻最后就是忍字当头。
我高中时候,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聊起这个《氓》,说古人的规矩,其实处处都是考验。男子抱着丝和布来求亲,结果不走正道,非要玩什么“走后门”。被拒绝呢,反倒怒气冲天,还一脸委屈想让姑娘来哄。这样的男人,老师冷笑了一声,说:“起家就不厚道,拖家带口你指望他能有多稳重?”我那会儿还嫌她“碎嘴子”,现在倒觉得她真有先见之明。
从前读《氓》只觉女子可怜,抱屈的是她一头热心肠、满纸痴情,甘愿赴汤蹈火。后来慢慢明白,哪里是她一个人的错?这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故事,代代都有。我们身边多少姑娘,也总是那样:为爱投入、受了伤,最后还是自己哄自己。说到底,真爱像月光,真生活却像路上的土。扎手、脏兮兮,可你还得走。
后来升学考到《范进中举》,当时哪懂呢?以为就是笑话。找工作时对着《孔乙己》发呆,觉得自己比谁都懂人情冷暖。等真到了成家那会儿,看着《孔雀东南飞》,才知道,哎,这些书其实早就把一切都写在纸上,只是咱们那会儿不信,也看不到。
你有没有觉得,读书就像种子,小时候埋进心里,没什么声音。真正等到某天撞了南墙,才发现字里行间全是你我。大人们嘴上说的“过来人”,本来也不是骗你的。只是你不撞南墙不回头,读多少遍《氓》,该摔的还是要摔。
我那天刷到的评论,有个人说:“教育其实是一场延迟爆炸,老师、书本、老祖宗,都跟你说了一遍,等你自己踩上去才响。”这话我至今忘不了。她说得真对,我们以为过去的文章、一个个老师的唠叨,只是听个响,其实有时候真的能救命。只是没人提前告诉你,命运哪一天给你安排考试。
你看,让人一声叹息的是,不管哪个年代,姑娘的困境没怎么变过。做什么都得先把自己的心捧好,别指望天上掉馅饼,掉下来往往是锅盖子。你说,男子恋爱的退路,总还有人拉一把、找回自我。姑娘的退路,有么?生了孩子,还能说走就走?能离开的,都得搭上半辈子的力气和勇气。难。
话说回来,咱们这时代总归是好了些,离婚不再是天塌地陷,姑娘们可以工作挣钱,也有人撑腰。但门一关,灯一灭,婚姻里的气冷暖暖,还是自己知道。外人谁能分得清究竟谁的错?
这故事里没有十全十美的结局,只有在泥里挣扎的你我。也许过几年,教科书还得改,女主不再流泪,换她甩了婚书,自己过余生。谁知道呢。人生哪有剧本,我们都是摸黑往前走。你说说,千年过去,爱与恨,怎么就总绕不开那条旧路?
李一氓回忆:县城里最先剪辫子是我三哥,后来成为反清的积极分子
我的家乡是四川彭县,天府之国的一角。我出生在那里——说是县,但在唐宋时那可是“彭州”,地位不低,可跟成都掰手腕。县北边有座丹景山,那地牡丹好得很,陆游写过《天彭牡丹谱》,把这里的花说得能和洛阳的比得上——你说老祖宗会夸,实际也是实打实的美景。
小时候,就觉得彭县是个挺不安分的地方。城里热闹,河上卧龙桥,菜馆飘香,街口总有人嚷嚷。可听爷爷讲起那些陈年往事,却总让人心里一跳。他说,彭县虽是土地为根,可到了清末,手工业和商号都爬起来了,外来人的生意经也进了县城。钱庄被陕西帮掌握,盐店归安徽桐城的方家……像大树根系,盘结得密密麻麻。生活有点乱,却也有点意思——什么盐票钱票,还有“折子”,买东西赊账都凭它,一年三回结清。咱家柜子里折子攒了一堆,药铺的,绸缎行的,杂货铺的,隔三差五就扣着心算那一栏账。过了时,总归是要还,但能拖也就拖;日子也这么稀里糊涂地过下去了。
你要说当地人,其实也稀奇。县城里传说真正的“老四川人”只有杨姓一家,剩下的大半是福建、陕西祖籍的移民。福建人建天后宫,办了闽省小学;陕西人在三元宫,也办了秦省小学。到我上学时,算是“自家孩子”,不收学费,老师教国文还会写钟鼎文——想想也挺自豪。会馆里有神庙,有小学,有人气,逢年过节庙前扎堆,烧香喊号子,好不热闹。就算家里也成了“杂”——我身上贴着“原籍陕西泾阳”,谁问都得带着这一层身份打烙印,里外不是人又是人。
彭县是个水大的地方,归了都江堰内江灌区,有清白江横穿而过,水车旁边总有鹅卵石砌的泉眼,清水汩汩流,真是“天赋”。一年两熟,春秋收成不差,地边上的小村子只种红苕、玉麦(红薯和玉米),土薄水少,只够糊口。不像城里,街头都是各色生意:东街扎罐卖陶器,北街铺着绫罗绸缎,西街全是酒肆菜馆,南街糖面杂货,十字路口一碰头,哪家大爷不认得街坊?这格局一转眼就过了几十年,居然还大致没改,不觉有点怀旧。
商业活跃的背后,其实也是啥都混杂。外地人大权位多,福建、陕西会馆自有小学,四川人建川主宫,只是没办学。乡下还有一撮客家人,说自己广东腔。到底怎么那么多族群搬来?谁也说不清,不知是乱世避祸还是发财投奔,总之,彭县的身份卡上都得加一栏“原籍”,就是认祖归宗的符号罢了。
我还记得童年那点灵气和糊涂劲儿。上小学的课程不复杂,国文、算学、格致、地理,还有体操手工,作文一律“今夫人生天地之间”,后面瞎拼一句。老师讲课断断续续,但菊花种得真细——从打叉到扎枝一手包办,连校园都像花圃。小学同学里出了何秉彝这样的大人物,后来牺牲在上海成了烈士,谁能想得到自己小时候趴在同一张桌子瞎写题目的家伙,未来竟这样不平凡呢?
要说那会儿小孩,调皮是肯定的。春节偷酒偷菜,冒充大人拼酒,酒量根本不会把控,结果一群人醉倒在船厅的大木炕上,家里找人找得焦头烂额,最后全捡回来,差点小命出岔子。从那以后,我沾酒就心慌——估计是小时候的阴影,到大了也没能彻底摆脱。
家里风俗也奇怪。头疼脑热总要“叫魂”,点香鸡蛋,大喊名字跑到门外,等鸡蛋站起来就算魂儿回来了。生大病请端公——专做法事捉鬼的。瓦房顶上沙沙一响,说是鬼被赶走了。其实多半是中药药到病除,但小孩子听了还是相信端公法力无边。现在和人讲起那阵法事,还觉得趣味满满——不明白那些响动是怎么来的,反正心头有个谜。
说到变革,就不得不提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彭县传统和新潮并存,大户地主之下,小地主、富农遍地,经济格局并没太大改变。但洋务运动和变法的风吹进了校园,普照寺里的菩萨都让位给了实验室和数学教员,还请来日本老师讲理化,说是现代化,县里孩子都瞠目结舌。我的几位哥哥在县立中学读书,算是见识了一点新鲜路数。
1911年,辛亥革命风起云涌。我才八岁,那一年县里的事,大人们都说不定哪天会出乱子。保路同志会鼓噪起来,为了铁路归属问题,把地主资本强制转成官有,地绅、哥老会、本地百姓混成一锅粥,各怀鬼胎。家里担心,暂时把我送去山里亲戚家避个风头。头回进山,见天地宽阔,觉得新鲜,只是没几天就被接回来。哥老会满城风雨,三哥成了先锋,率先剪掉辫子,还主动去给同志会写文书,街头巷尾都在坚持“造反”。后来他看清形势,把心一横,去了成都考军官学堂,从此走上了另一条路,成了靠笔杆子和军装混世的爷们。
革命的阵仗不光是闹热,更多的是矛盾。最初家门口挂着“汉”字白旗,后来换成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一块旗代表一种身份,谁也说不清这是进步还是折腾。清末那些旧习老气未散,县城的哥老会还仗着老办法称王称霸,结果闹出了一场命案,让整个小城鸡飞狗跳。
记得在1912年,城里陕西钱庄店员和哥老会头目的妻子私通,冲突激化,杀人逃跑,被抓回来,女人被活剐,游街示众。那种残酷的刑罚,别说小孩,就是现在想起来都毛骨悚然。满街传说,黄昏有人哭喊“要火”,随葬俗,没人敢去送。最后好歹有个胆大的人去了一趟,风声才算平息。那一阵子,我一到傍晚就心里发怵,不敢出门。后来成都警察厅长带兵突袭城里,把作恶的头目抓走,这才算一锤定音,哥老会也由此收敛了许多。
这些事儿,细想来都像是在雾里看花。既有变革的声音,也有回头的影子;既有新式学堂和实验室,也有会馆、巫师扎根在街头。童年读书,日子简单,数学和自然学得稀里糊涂,英文也不过“Come Go Open Door”几句童话。回头看去,家里几个兄弟,没谁是真正的学者或工匠,大都是摸爬滚打混日子的平凡人。
一辈子往事,好像随手翻过一页,有影子、有声音、有吵闹、有忐忑。彭县的水流、桥梁、庙宇、巷口、旗帜、折子、锅灶、菊花、闹鬼,风俗人情交杂一锅,谁也说不清命运会把小孩带到哪里。我们总想追问那瓦上的声音,到底鬼有没有真被捉走?那些剪了辫子的年轻人,最后都去了什么地方?彭县的街道七八十年过去还没变,但人的心,其实早已起伏跌宕——能不能静下来看清,谁又说得明白呢。
文档上传者
热门标签
相关文档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