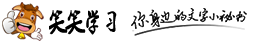欢迎来到98聘
精心挑选《她变了 作文》相关文章文案。(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9-04 11:41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她变了”的作文,可以遵循以下步骤和注意事项:
"作文题目:她变了"
"写作注意事项:"
1. "明确中心思想 (Clear Central Theme):" 你要表达的核心是什么?是她的性格变了?价值观变了?行为习惯变了?还是她对某个事物/人的态度变了? 变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令人欣慰的还是令人惋惜的? 在动笔前想清楚你要通过这个“变化”说明什么道理或抒发什么情感。
2. "选择合适的切入点 (Choose a Specific Angle):" “变”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你需要聚焦。是围绕某一件具体的事情来写她的变化?还是通过几个不同场合的表现来展现她的变化?或是对比她变化前后的状态? 例如:可以写一次重要的经历(如考试失利、家庭变故、一次旅行)如何让她发生了改变;或者通过她对待朋友、学习、家务等不同方面前后的对比来写。
3. "生动刻画变化前后的状态 (Vividly Describe Before and After):" "变化前:" 详细描绘她原来的样子。可以用具体的事例、语言、动作、神态、穿着等细节来刻画。要力求真实、具体,让读者能想象出她那时的形象。这为后文的“变”做铺垫,也
妻子乳腺癌过了三年她变了我变了我们的小家也变了_1529
妻子乳腺癌过了三年,她变了,我变了,我们的小家也变了
三年前的那个冬天,妻子在乳腺科门口攥着报告单,手抖得像筛子。丈夫站在旁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听见自己心跳声大得吓人。谁也没想到,这场病会把两个人都重新“洗”一遍。
先说妻子。化疗结束那天,她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用了十年的旧锅扔了。新锅、竹桶、空调、热水器,一口气全换。邻居笑她“败家”,她回一句:“我怕明天没力气拧开关。”
她开始学竹桶米饭,米香混着竹子的清甜,厨房像开了小森林。阳台的花从三盆变三十盆,连楼下保安都收到过她塞的薄荷苗。她说:“以前省,是怕以后没的用;现在花,是怕今天白过了。”
丈夫的变化更隐蔽。以前一点就着,现在吵架前先数五秒。晨跑从三公里加到八公里,跑完回家写小作文,写完贴在冰箱门。妻子化疗最难受那阵,他把“今天没哭”四个字写得歪歪扭扭,像小学生交作业。
有天他写:“我学会了闭嘴,也学会了不闭嘴。”妻子看完笑出眼泪,说:“你终于把脾气存银行了。”
家里最显眼的是那张贴在墙上的作息表:几点晒太阳、几点喝豆浆、几点关手机。刚开始像军训,后来成了背景音乐。女儿放学回来,第一句话从“作业好多”变成“今天咱家阳台的番茄红了”。
美国癌症协会的数据冷冰冰,说积极心态能提高生存率。可在这儿,数字变成了炖汤的咕嘟声、跑步的呼哧声、竹桶开盖时的白汽。没人提“战胜病魔”这种大词,他们只是把每一天过成了节日。
有人问:“花那么多钱买电器值吗?”妻子答:“省下的力气,够我多看一次日落。”丈夫补一句:“省下的吵架时间,够我写三首诗。”
现在回头看,那场病像一把钝刀,慢慢削掉了他们的急躁、凑合、还有“以后再说”。留下的,是一个会数花瓣、会闻米香、会写错别字的家。
你家阳台有没有一棵植物,是某次吵架后买回来的?
知青追思:当年在公社当文书,我的一个小动作却改变了她的命运
电话里的第一句话像在河面上丢进一枚小石子,清清脆脆却带着一丝追问的涟漪。
“老刘,你当年,是不是故意把那张通知贴在我家窗下的。”
我握着话筒,指尖有些发热,茶桌上的白瓷壶吐着温温的气。
我忍不住笑了笑,笑里既有惊讶也有旧日从泥土深处升上来的暖。
“你咋还记这个呢。”
那头轻轻地笑了一下,像秋末一束风扫过金黄的桦叶。
“你说呢。”
电话挂断后,屋里一时静得只剩半导体收音机里轻轻的电流声。
我端起搪瓷缸,白底蓝边,口沿有一处小磕,像老朋友额角留着的故事。
我把手指在那磕口上来回摩挲,仿佛能摸出一段年头的纹理。
那一年是1977年的秋天,霜打得早,榆树叶上边缘一圈银光,像沿着季节走的针脚。
我在公社大院里当文书,屋檐下挂着风干的玉米,风一来,玉米须像胡子一样颤。
屋内的桌上摆着算盘、墨盒、票据夹,还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嗡嗡像只守夜的虫。
墙上一块黑板报是我每日的“窗”,粉笔架里插着长短不一的粉笔,末端白粉粘着我的指肚。
我穿一件蓝布褂,胸口口袋别着英雄钢笔,笔帽常在晨雾里泛着一层冷意的光。
土炕上铺着芦苇席,一躺下去,草梗扎得背上起密密的小疙瘩。
夜里油灯的灯芯要一寸寸剪整齐,抻长了冒黑烟,抻短了又不亮,心里不免嘀咕一句。
咋整呢。
老会计坐在我对面,算盘拨得清脆,珠子在竹档之间跳来跳去,像一群麻雀在谷场上觅食。
他嘴里念叨,账是要对上,心也要端正,别把细小处糊弄了。
我听他念叨,心里却像有股温热的水在慢慢流。
甭操那心。
这些话我没出口,只在心里轻轻地敲了敲。
她常来公社大院,在黑板报前停一会儿,在票据夹边踟蹰一下,在窗台上抖落指尖的泥尘。
她叫秀兰,是东头人家里头一个孩子,肩上扛着家里的一篮子事。
她穿蓝布褂,袖口洗得发白,布面一朵一朵华纹像反复的日子。
她系一根黑皮筋,干净利落把头发往后一扎,露出不大却干净的额头。
她走路脚下有风,像身后有一条看不见的路径催促她快一点、再快一点。
她的手背上常有麦芒划出的细痕,粉粉的,像一条浅浅的小河在手背上走。
她看黑板报看得认真,像把字一笔一画地装进心里。
她有时伸手在黑板报角上一掸,粉灰扬一道轻烟,阳光一照,像轻雪在春天里飘。
可不咋的。
她家老屋顶上爬满了南瓜藤,秋天的时候,南瓜一个挨一个,像小灯盏挤着对门笑。
她母亲身体不大中用,一到农忙季节就喘得紧,她弟弟妹妹还小,衣襟总是被风吹得鼓鼓的。
她的眼睛不大,但里面有亮亮的光,像冬夜一盏小油灯,弱却稳。
那年八月,中午的太阳被薄云遮成了一个温柔的白圆,半导体收音机里传出一条重磅消息。
恢复高考。
屋里一时间静得只剩电流声“滋滋”作响,像每个人的心里都被什么轻轻按了一下。
我把消息抄在黑板报最醒目的位置,字写得规整,一笔一画像在磨一块石头。
我用粉笔画了几个小方框,写清时间、地点和要准备的材料,末了还在角上画了一支小小的钢笔图样。
我往后退两步,吹了口气,粉笔末子跳着跃起,像一群被惊起的小灰雀。
老会计走过来,眯着眼看一遍,算盘珠子在他指间还没有停稳。
他笑了一下,说天要开晴了,说人心也要开了窍。
可不咋的。
来问的人多了,问要不要耽误农活,问考上了家里咋办,问要不要交钱,问从哪起步。
我把流程一条条写到黑板报下半边,像铺在地上的一条条白线,攥紧人的心。
她也站在人群里,站在人群边,拉着扁担的绳,眼神落在那几行字上,像悄悄按在水面上一枚小石子。
她没有多说话,只轻轻点一次头,又抿一下嘴角,像在对自己说一声好。
她回去的时候从大榆树下走过,树皮裂着沟,像老会计掌心里的岁月。
她抬头看了一眼,眼里那点光静了一下,又灵动了一下。
那一晚我在土炕上翻了几次身,油灯的火苗一会儿紧一会儿松,像心口那点热意被风吹拂。
我想起我母亲过去在城里,夜里把旧桌布铺在膝上,眯着眼纳鞋底的背影。
我想起她在黑板报前的那一眼,然后又看向自己的手,手心里仿佛也有粉末的触感。
第二天清早,我带上浆糊和刷子去街口贴通知。
我照着要求贴到了供销社边的墙上,贴到了大队部门口,贴到了粮站门外的木板上。
我又拿出一张,走去了东头井台旁。
那口井是她每天要路过的地方,是她肩头的扁担和她家的水桶每日要停的地方。
我把通知贴得偏低了一点,低到她站直了就能看清的高度。
我看着纸角被晨风吹起一下又贴合,像对着她眨了一下眼。
我心里说这也算顺手,算不得越线。
行唄。
午后太阳暖了一些,井边的石缝里长了一线线小草,勇气像小草那样从缝里往上拱。
她挑着扁担来,木桶里水面晃着一圈一圈的光,像一池小小的日头。
她在井台前停了一下,放下扁担,又站直,目光轻轻落在纸上,落得谨慎也落得踏实。
她把那几行字读过去,然后把扁担又挑到肩上,嘴角的弧度从容又小心。
她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像把心里的那盏灯再看一眼。
那天傍晚她来公社,手里攥了一张报名表,纸上有折痕,折痕的每一道都像她犹疑的每一次起伏。
她把表递给我,眼里有一丝湿润,但没有慌张。
她问该怎么填,我指给她看名字、住址、学历,再告诉她要用正楷。
她没有带笔,我从胸口口袋里把英雄钢笔拔下来,墨水是前一天我才加满的,尖儿利,写在纸上应该像在水里划一道线。
她接笔的时候手背上那道新划的小口还没完全收口,粉红色的皮肉像刚冒芽的一点嫩。
我看了一眼,又看向纸面。
我告诉她填完要核对一遍,把生僻字写在旁边注一下,别误了。
她在我的桌角坐下,身子微微前倾,指尖又干又稳,笔尖在纸上走得平平正正。
她填完,把笔攥了一下,然后便要还给我。
我把笔接回,又从票据夹旁边的小木匣里摸出几张邮票。
邮票是我攒了半年的,边缘的齿口有一点毛刺,摸上去有那么一点扎手。
我把邮票夹在她的报名表里,纸张之间那点厚度像往她心里悄悄垫了一块。
别抠搜。
我心里说一句,既说给自己听,也像说给那个一直克制的时代。
她愣了一下,抬眼看我,然后点了一下头。
她没有多推托,只把感谢收在眼里,像收起一缕冬日的阳光。
报名之后,她去了夜校。
夜校在供销社后的平房里,门口一盏黄色的灯泡挂着,灯圈不大,却把黑暗里的字照得足够清楚。
黑板上是代课老师写的公式和古诗,粉笔灰浮在空气里,像一阵轻薄的雾。
她每天都去,脚底踩过结霜的地,回来时把鞋底在门槛上敲两下,落下来的霜粉像撒了一撮盐。
她每次到大院,总会接一缸热水。
我用那只搪瓷缸给她装满,开水的热气腾上来,把她冻裂的手背烫得又疼又暖。
她把缸捧在手心,我听见水撞在缸壁上的叮咚声,像把一口井里的水点了一下,活起来了。
甭怵。
我在心里说。
她坐在窗下背诗,秋风吹动窗纸,纸响像轻微的鼓点。
她算题的时候,食指在桌面上轻轻点,一下一下,像算盘珠被看不见的手在拨。
她的发梢有时溜到耳后,又顽皮地落回来,她用食指一抹,整洁得像字帖上一横一竖。
慢点不磕碜。
我看她抬笔落笔,心里冒上一句,不急不忙,把握住自己的节奏便是。
公社把各大队的名单往区里送,我把名单用毛笔写了一遍又一遍,墨淡了加,字偏了重来。
我不允许自己在这样的事上马虎一丝,因为一丝就可能是一个人家一辈子的走向。
老会计站在一旁报数,算盘珠子在他的指下像落雨敲在檐前。
他看了我一眼,说心软要有板儿,板儿是劲,软是暖。
我点点头,让自己在两者之间找一个不偏不倚的位置。
心里有数就成。
我对自己说。
到了考试那天,天寒路滑,早上的雾气像白布一般搭在田野上。
她来得有点晚,眉间一丝倦意,显然是清早被一些家里的小事阻了手脚。
她说牛栏出了一点状况,耽误了一阵,我看墙上的钟,指针离报名处关门的时间只剩一点点缝。
别犯瓢。
我心里又冒出一句,随手把公社里靠墙的永久牌车推了出来。
车把上缠着黑胶带,铃铛有点旧,按下去的时候抖三抖才响透。
她把包往怀里一抱,上了后座,脚尖轻轻点着轴,生怕让车摇晃。
我蹬上踏板,风从耳旁刷刷划过去,既像刀有锋,也像羽有柔。
土路有一段松软,车轮陷了一下,我一脚下去,泥点溅起,落在裤腿上并成开花的图案。
她小声提醒慢一点,声音里有怕迟的急,也有怕摔的慎。
我压住呼吸,再往前蹬两下,车身稳了,风里的凉像一只手替我们把热气往前推。
我们赶到公社的时候,门口的人还在排着队,队伍像一条秩序井然的小河弯进屋里。
她回头看我一眼,她眼里那一瞬的亮,像晨光撞进井里,光柱直通心底。
她说谢谢的时候声音不高,却让我的心肺跟着松一下又紧一下,像被轻轻敲了一记。
甭怵。
我冲她点点头,抬手把她的垫肩理了一下。
我没有多话,话到了嘴边又憋回去,怕一出口就变成了多余的热闹。
那晚她从夜校出来,给我拿来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一块点心和两个鸡蛋,温温的,透着窝里的香。
她说让收下,算她一份心意,我不肯,她说她心里要平衡。
有一说一。
我看她眼里那股执拗,便把布包接下,鸡蛋的温热仿佛把我的手心也抚平了一块。
冬天像一个心性稳重的老人,日子在他的臂弯里缓缓移动,雪落几次,屋檐下挂起一行细细的冰凌。
她的手裂口更深了一些,她把手背往搪瓷缸上方探一下,再把手背上抹一点猪油膏,裂口像小花开开合合。
她终于等到了开春的风。
柳树抽出浅浅的新绿,地皮冒出一排排齿一般的小草,像是土地在笑。
老会计从镇上回来,帽檐上粘着几根柳絮,他把一封信拍在我桌上,眼睛笑成了弯弯的一道。
他说让自己猜,我心里先跳了一下,再把跳落回去,忍住了不先伸手。
我终究拆了那封信,纸面有一点硬,字印得很清,三个字亮在白纸上像刚晒出来的米。
录取通知书。
她被地区师范录取了。
我看着那几个字,周遭的一切都像被轻轻按了静音,只有心里有一口温热的气,从田埂那边,一节一节走到胸口。
我把信夹好,又倒了两缸热水,搪瓷缸里的水影晃了一下,像一只小鱼撞了缸壁又游开。
她走进大院时,帽子上沾了细小的柳絮,肩上有一层很薄的风尘,眼神却稳稳地像一块铺在地上的石头。
我把信递给她,她接过去,手微微颤,纸在她指尖轻轻响,像小鸟在她掌心扑扇了一下翅。
她笑了,笑里有水,也有光,光在水里跳来跳去,像孩子在春天的河边追着自己的影子。
她没有说太多话,她只是把信收好,在心里把一扇门推开了一条缝。
那晚大院里更热闹一些,人群像春天的风,带着暖意绕着老榆树转。
大家说出息了,说给咱们这片地增了一分亮,说让娃娃们看见了一条路的样子。
我站在夜色里,仰头看榆树梢,风把枝条吹得一下一下点地,像大地在点头。
不白折腾。
我心里说了一句,既说给她,也算说给那几年里依着手边微薄的光往前摸索的我们。
她去了地区师范,写信回来的字一封比一封正,每一横每一竖都像在田里走出的一行直垄。
她说宿舍窗台排着用完的墨水瓶,瓶口边还围着一圈淡淡的蓝。
她说老师严格却温和,同学们从不同的方向走来,在同一间教室里把脚步踏整齐。
她说有一回去邮局寄包裹,看到邮票的齿口边缘,忽然就想起我塞在她报名表里的那几张。
她说那几张邮票像一盏小灯,时间越久,亮得越稳。
我回信不多,也不擅长写那些漂亮的词,我只把眼前的东西写清楚,像把桌面擦干净。
我说公社的牌子要换了,大家嘴上还叫惯了原来的称呼,心里却都知道是往好的方向走。
我说供销社进了新货,玻璃柜台里的糖果从散装变成一小袋一小袋,孩子们拿着布票排队的样子像小燕子排成队。
我说大队部架起了黑白电视,晚上开机的时候,院子里一片人影,你趁我不注意拿凳子占地方,我瞄你一下,你再给我挪回来一点。
我说老会计把我的婚事看得比账还认真,说小周是个实在人,笑起来嘴角有浅浅的梨涡,做饭手脚利落,心口也有火。
我说后来我被调去了镇上的文化站,再后来去了印刷厂,当起了统计,算盘又有了新的节奏。
她回信里说她放假要回来看大家,她说路上有风,有光,有在课堂上笑过的声音。
又隔了几年,她提着一个包回来了,肩上斜挎一只帆布包,包上印着四个红字,字体正气,不抢眼却显眼。
她把包放在我的桌上,拿出一个新的搪瓷缸,白底红字,字上写着她就读的学校名称。
她说这个杯子给我。
我说瞎花钱,她笑着摇头,说花在这儿心里头踏实。
她又从包底摸出一支笔,是那支英雄钢笔,笔帽被她的手磨得亮亮的,夹子没有歪,身板也没变形。
她把笔放在桌上,手指在笔帽上轻轻摁了一下,像对这支笔说一声“回头见”。
她说你要我还我就还,你要我留我就留。
我把笔推回去,让它继续在她指间做一支正经的笔。
别打怵。
我在心里说,她点了点头,把笔收在包里,把那只新杯子留在我的桌上。
后来的日子,像一条不急不慢的河,从石头边绕过去,又从草丛间淌出来,声音不大,水色清润。
公社的牌子在1983年换了名字,供销社的玻璃柜台被擦得比早先更亮,永久牌自行车的后座绑起了孩子的书包,铃铛旧声里多出一点欢喜。
印刷厂换了一拨又一拨设备,铅字慢慢退了场,机器的轰鸣换了个声腔,纸上的字印得更清,人的眉头也舒开了些。
我和小周成了家,我们在镇上分到一间小房,窗台上摆了两盆吊兰,叶子垂下来像两只温顺的小手。
小周把屋子收拾得干净,抹布在她手里像一块会发光的布,擦过的地方亮得像新生的皮。
她每次拿起那只白底红字的搪瓷缸,都要用干布一下一下擦边沿,还不忘轻声说一句。
这杯子有福气。
可真带劲。
我笑她迷信物件,她笑我口硬心软,家里的笑声像锅里烧开的水,咕嘟咕嘟热得欢。
她成了一名老师,又做了教务主任,后来理顺了许多事情,她的脚步踏实,她的语气平稳,学生们提起来的眼睛一天天亮。
她没有回城,她把脚印留在了县里的学校门口,把名字写在孩子们的练习册边,把时间花在一间间教室里头。
九十年代的镇上,早市里有了更多货物,行当也多起来,摩托车轰鸣着把清晨的雾打散了一些。
我守在印刷厂的数据前,逐一核对数字,眼睛里像一把放大镜,不放过一个小数点的移位。
我拿余暇的时间在文化站帮忙,给孩子们讲讲阅览室的规矩,给老人们续杯热水,手边总有书纸微微的香气。
两千年后,手机慢慢普及,老邻居之间的消息像风,轻轻一吹就传遍了街角,街边的梧桐树也一天比一天高。
我退休了,又去了社区的图书屋做志愿者,早晨开窗通风,擦桌子的时候太阳在桌面上移动,光斑像小孩子的脚印跳着走。
搪瓷缸一直摆在我的手边,我时常用它接水,水面微微晃动,像把旧时光里的一个句子重新读了一遍。
我也总想起那支英雄钢笔,在她的教案边,在她的黑板旁,在孩子们的作文本上,划出一条一条稳当的线。
不打怵。
我想,人只要不打怵,脚下的路就不会拐成死弯。
可不咋的。
这些年头,许多事情都变了,变得快也变得稳,就像她在一封封信里的字一笔一画慢慢变正。
2015年的秋天,梧桐落叶铺了一地,阳光把叶脉照得穿透,像一张张精致的地图。
电话响起,她的声音从那头传来,像秋风从田里经过,带着粮香,带着岁月的温度,又带着一丝当年的认真。
她问我当年那张通知,我顺口说你咋记得这么细,她笑,说你说呢。
第二天她就来了。
她站在门口,肩上像还搭着路途的风尘,眼睛里却清清亮亮,像一口水井刚刚被打捞通。
小周在厨房里盛汤,汤面上飘着一层薄薄的油花,香气脚步轻快,拐过门槛就上了桌。
她一进门就看到了那只搪瓷缸,走过去把缸拿在手里,手指在磕口上停了一瞬,像在给老朋友理好鬓角。
她坐下,从包里拿出一样东西,是那支英雄钢笔,笔帽仍旧光亮,像被岁月熨平了一遍又一遍。
她说想把它带回来让我再看一眼,我说你留着它,它知道你的手劲和你的字,也知道你的坚执和温柔。
她笑,说那就放在她的书桌上压作业,笔下那条线会更稳。
她端起搪瓷缸,轻轻吹一口热气,热气从她的面颊旁掠过,像当年夜校门口那盏黄灯静静罩在我们头顶。
她忽然抬头看我,目光像一条安静的河忽然照见了月亮。
她说当年你贴的那张通知,你借的那支笔,你塞的那几张邮票,算不算越线的帮。
我笑笑说算不得,是顺手,是把该看到的字放在该看到的眼前,把该握住的笔放在该握住的手里。
她点点头,她说那就是她命里的一个台阶,是她在家门口的台阶之后,又多出的一个台阶。
她说她后来每次帮一个犹疑的孩子填表,每次在黑板报上写报名须知,每次给孩子们讲案例的时候,心里都会冒出这三个小动作的影子。
她说她在食堂里看到有孩子肚子还空着,就把饭盒分出一半给他,也不是图别的,只是觉得心里那盏灯不能只照着自己。
她说她在校门口看着孩子们背着书包排成一队,铃声一响,脚步整齐,像一支小小的队伍走进光里。
她说她在教师会上说过一句话,说知识是把路面铺平的砖,铺多少,心里自个儿清楚。
我听着,像在一块温热的石头上坐定,一点一点感到身上的汗出得恰到好处。
甭操那心。
我心里又冒出这句老话,像老会计在耳边一拨算盘珠,提醒我别把小事看轻,也别把大事看重得喘不上气。
小周把汤端出来,嘱咐烫,小心,筷子在碗沿上轻轻敲了一下,声浪在屋里绕了个小圈。
她说这一回能坐下好好唠唠了,别总是你在那头她在这头。
可不咋的。
我笑,笑是从心里往外冒的,像壶开了,盖子向上鼓鼓的。
送她出门时,风有一点凉,但不刮脸,风像一把细细的梳子,温柔地给世界再理一遍纹路。
她站在门口,回头看我一眼,眼里那点光安安稳稳,像黄昏时分一盏路灯准点亮。
她走了,影子在地面上和树影交叠,一离一合,像从前的日子在如今的日光下重新排了一次队。
我回到屋里,拿起那只搪瓷缸去倒水,水沿着壶嘴倾下,热气腾起,像一朵洁白的云飘到我面前。
我把缸放在桌上,木头被瓷器轻轻一敲,发出一声不高不低的响,像从心底升起的一句缓缓的安。
我看着窗外的吊兰,叶子在日光里盈盈发亮,像有人在暗处不动声色地擦拭。
我听半导体收音机里播报天气,主持人的嗓音温和,像一只手在我肩头轻轻落下。
我忽然意识到,那三个小动作早已不只是当年的三个小动作。
那是把通知贴到她必经的眼前,是把笔递给一个愿意写下自己名字的手,是把邮票塞进一封要上路的信里。
那是把一盏灯芯轻轻拧直,是把一块火慢慢添旺,是在夜里把窗纸戳开一个不大不小的洞。
搁这儿。
我心里又说了一句,是的,搁这儿人就明白了。
我想起1977年秋天的老榆树,想起黑板报角落扬起的粉灰,想起永久牌的铃铛抖了三抖才响透的声。
我想起她带着温度的那两个鸡蛋,想起邮票齿口的毛刺,想起她手背上粉红色的伤口一点点淡下去。
我也想起她回来的那只新杯子,白底红字,在我手心里暖了这么些年,边沿的那道小磕像一道浅浅的微笑。
人过日子,火一点点旺,心也一点点热。
不多不少,刚好一把合手的火,刚好一盏稳稳的灯。
我把这杯水端到窗前,阳光照在水面上,光波一圈圈往外走,像日子自己在对我说话。
日子说,小动作不小,别轻看。
日子说,甭怵,慢慢来。
日子说,可不咋的。
我没有再打电话回去,也没有给她写一封多么讲究的信。
我只是把那只搪瓷缸洗干净,又放回桌上它熟悉的位置,像把一段路放回它该在的方向。
窗外的风把窗帘轻轻吹起一角,阳光又往屋里走了一步。
我看着那道光落在桌上,心里忽然平静而饱满。
我知道,有些事到这儿就好。
我知道,往后还会有人在黑板报前停住脚步,还会有人把笔递给陌生的手,还会有人把邮票塞进给未来的信封里。
我把这口水慢慢喝下,热度从舌尖一直走到胃里,再慢慢散开到四肢。
我没有再想该不该,值不值,越不越线。
我只听见心里有一声轻轻的回响。
行唄。
光从窗台的吊兰上一节节地爬下,安静地,耐心地,像在把一段话说完。
我把搪瓷缸放稳,手心的温度还在。
我慢慢地坐回椅子上,脑子里突然冒出一句很朴素的话。
这辈子,做几件这样的顺手事就值了。
值不在别处,值在那盏灯亮起来时,谁都能看见一点光。
我笑了一下,又不笑了。
我听见外面有孩子跑过,橡皮球在地上弹跳的声音像一串干净的鼓点。
我抬头看窗外,光线更透了一点。
我心想,就这样吧。
我的手背搭在桌沿,微微有一点热意残留。
像久远的秋天被我从记忆里端回来,又悄悄地放回原处。
不动声色,却让人心里亮了一下。
文档上传者
热门标签
相关文档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