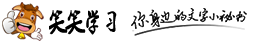欢迎来到98聘
推荐《崴脚作文》相关写作范文范例(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9-13 17:41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崴脚”的作文,无论是记叙文、说明文还是议论文,都需要注意以下几个事项,才能使文章更清晰、生动、有深度:
"一、 明确写作目的和文体 (Clarify Purpose and Genre)"
1. "你是想写什么?" "记叙文 (Narrative):" 讲述一次自己或他人崴脚的经历?重点在于过程、感受和事件发展。 "说明文 (Expository):" 介绍崴脚的原因、类型、处理方法、预防措施、恢复过程等?重点在于知识性、客观性和条理性。 "议论文 (Argumentative):" 讨论崴脚带来的启示(如安全意识、关爱他人等)?重点在于观点、论据和逻辑性。 "混合文体:" 结合记叙、说明、议论等元素。 2. "确定核心内容:" 你的作文是侧重于崴脚瞬间的惊险、处理伤口的痛苦、康复期间的坚持,还是崴脚带来的对安全的思考?
"二、 紧扣主题,内容具体 (Focus on the Theme, Be Specific)"
1. "选好切入点:" 围绕“崴脚”这个核心事件或概念展开。如果是写经历,选择一个最典型或印象最深的一两次来写。如果是写说明文
82年我去县城考试,把一崴脚姑娘送去医院,她说3个月后老地方见
那年夏天热得跟蒸笼似的,我背着个破帆布包就往县城赶。
说起来也怪,那会儿我正琢磨着怎么应付明天的招工考试呢,走到县医院门口,就听见有姑娘喊"哎哟"。
回头一看,一个穿白衬衫的姑娘坐在台阶上,脸皱得跟包子褶似的,右脚踝肿得老高。
"咋了这是?"我赶紧跑过去。
"刚才下台阶,一脚踩空了。"姑娘声音挺好听,就是疼得直咧嘴。
我蹲下身子看了看,这脚踝肿得不轻,皮肤都发紫了。
"走,我背你进医院。"
"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走。"姑娘摆摆手,想要站起来,可是刚一动脚就疼得倒抽凉气。
"别逞强了,这脚再耽误下去更麻烦。"
我也不管她愿意不愿意,蹲下身子就把她背起来了。
这姑娘挺轻,也就八九十斤的样子,身上有股淡淡的肥皂香味。
背着她往医院里走,我心跳得跟打鼓似的,这辈子头一回背姑娘啊。
医院里人来人往的,不少人都往我们这边看,我脸红得跟猴屁股似的。
急诊科的大夫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戴副老花镜,满头花白头发。
"又是下台阶摔的?"大夫头也不抬地问。
"嗯,一脚踩空了。"我替她答着。
大夫让拍个片子,我又背着她去了放射科。
那年头拍片子可不像现在,要等好一会儿,我们就在走廊里坐着等。
"你真是个好人。"姑娘小声说。
"这算啥好人,换了别人也会帮的。"我挠挠头。
她摇摇头:"不见得,我刚才在那儿坐了快十分钟了,路过的人不少,都是看一眼就走了。"
听她这么说,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片子出来了,大夫看了看说:"软组织挫伤,没伤到骨头,回去好好养着就行,这几天别沾水。"
开了点跌打损伤的药,又拿了绷带包扎。
我在一边帮着递这递那的,忙活了小半个钟头。
"多少钱?"我掏出钱包,里面就剩下五块多钱了,这还是我留着明天考试后吃饭用的。
"不用不用,我自己有钱。"姑娘赶紧摆手,从口袋里掏出个小布包。
"你这脚都这样了,还跟我客气啥。"我已经把钱递给收费的了。
一共花了三块二,我心里算了算,剩下的钱够明天吃顿饭就行。
从医院出来,姑娘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我看着心疼。
"你家在哪儿?我送你回去。"
"就在前面不远,真的不用了。"姑娘指了指东边,那边是县里的老街区。
"那咋行,万一再摔一跤咋办。"
我坚持要送她,她也拗不过我。
一路上她话不多,就是偶尔说声谢谢。
我也不知道说啥好,就问她在哪儿上班。
"我...我在纺织厂上班。"她停顿了一下说,声音有点不自然。
"纺织厂挺好的,咱们县里数一数二的大厂呢。"我羡慕地说。
"嗯...是挺好的。"她点点头,没再说话。
走了十几分钟,到了一个小胡同口,胡同里青砖灰瓦的房子排得整整齐齐。
"就到这儿吧,我家就在里面。"姑娘说。
"那你好好养着,这几天别乱走动,买菜啥的能让家人帮忙就别自己去了。"
"谢谢你。"她转身要走,又回过头来,脸有点红,"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建军,家在柳河村,离县城二十多里地呢。"
"王建军。"她重复了一遍,笑了笑,"三个月后,还是今天这个时间,县医院门口见,可以吗?"
我愣了一下,这姑娘说这话啥意思?
"为啥?"
"就是想再见见你,好好谢谢你今天帮我。"她低着头,声音小得跟蚊子似的。
"那...好吧。"我点点头,心跳又快了起来。
看着她一瘸一拐走进胡同,我心里五味杂陈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第二天考试,我发挥得还不错。
题目不算太难,就是些基础的语文数学,还有点时事政治。
语文考的是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我洋洋洒洒写了八百多字。
数学有几道题挺绕的,但我小时候数学底子打得牢,基本都做出来了。
时事政治问的都是些国家大事,好在我平时爱听广播,答得八九不离十。
考完试我就回村了,心里忐忑不安的,不知道能不能考上。
回到家,娘正在院子里喂鸡,看见我回来了,赶紧迎上来。
"考得咋样?"娘眼里满是期待。
"应该没问题,题目不算太难。"我说。
"那就好,要是能进县里上班,咱家日子就好过了。"娘眼里有了光,"你爹在地里干了一辈子活,腰都累弯了,就盼着你能有个好出息。"
我点点头,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考上,不能让爹娘失望。
这三个月里,我老是想起那个姑娘。
她为啥要约我三个月后见面?是不是对我有意思?还是就是单纯想谢谢我?
村里的老婶子们知道我去县城考试的事,天天问我有没有看上哪个城里姑娘。
"建军啊,你也不小了,该考虑找对象的事了。"
"就是,城里姑娘见多识广,比咱村里的强。"
我每次都是红着脸摆手,心里却想着那个白衬衫姑娘。
她会不会真的来?还是只是客气话?
日子一天天过去,招工的结果还没下来。
我心里跟猫挠似的,又盼着又怕。
村里的老支书倒是挺乐观:"建军这孩子从小就聪明,肯定能考上。"
可我心里没底,万一考不上咋办?继续在村里种地?
到了约定的日子前一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要是去了她不来咋办?要是她来了我该说啥?
第二天一早,我起了个大早,穿上最好的那身衣服,又往县城赶。
路上碰到村里的二狗子,他看我穿得这么正式,开玩笑说:"建军,这是去相亲啊?"
"瞎说啥呢,我去县里办点事。"我红着脸说。
到了县城,我先在街上转了一圈,买了根雪糕降降温。
82年的夏天特别热,柏油马路都快被晒化了。
站在县医院门口,我紧张得手心都出汗了。
会不会她根本就不来?会不会她只是随口一说?
等了半个小时,还是没见人影。
我心里开始打鼓,是不是自己想多了?
正准备走呢,就听见有人喊:"王建军!"
回头一看,还真是她!
今天穿了件蓝色的连衣裙,头发扎得整整齐齐,脸上还化了淡淡的妆。
看起来比上次精神多了,完全不像个纺织厂的工人。
"你真的来了。"我有点不敢相信。
"我说过要来的。"她笑着说,"你的脚好了?"
"早就好了,一点事儿都没有了。"她走路的样子确实正常了。
"那就好,我还担心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呢。"
我们在医院旁边的小花园里坐下,那里有几棵梧桐树,正好遮阴。
"其实...我有件事要跟你说。"她的脸有点红,声音也变小了。
"你说。"我心跳加快,不知道她要说什么。
"那天我没说实话,我不是纺织厂的工人。"她低着头,不敢看我。
我瞪大了眼睛:"那你是...?"
"我是县医院的护士,在内科病房工作。"
我半天说不出话来,这丫头骗我?
"你别生气,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她急忙解释,眼里都快急出泪了。
"那你为啥要说假话?"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因为我想看看,现在还有没有像你这样的好人。"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很真诚。
"那天我是故意摔的,就是想试试会不会有人帮我。"
我更糊涂了:"为啥要这么做?"
"因为前段时间有个男的追我,是县供销社的,条件挺好的。"她说着,声音有点颤抖。
"表面上对我挺好,送花送糖的,嘴上说得比蜜还甜。"
"可是有一次我们一起上街,看见一个老大爷推着架子车摔倒了,东西撒了一地。"
"我想过去帮忙,他却拉住我说,多管闲事干啥,万一老头讹人咋办。"
她说到这里,眼圈都红了。
"我就想,这样的人能真心对人好吗?表面上对我好,会不会也是假的?"
"所以我就想了这个办法,看看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善良的。"
我听了心里五味杂陈,原来她是在考验我的人品。
"那我算是通过你的考验了?"我开玩笑地问,心里的不快慢慢消散了。
"不光是通过,是满分通过。"她笑得很甜,"你不光帮了我,还花自己的钱给我看病,连问都没问我要。"
"后来我找机会打听了一下,知道你是来参加招工考试的乡下孩子,身上肯定没多少钱。"
"可你还是毫不犹豫地帮了我,这样的人现在真的不多了。"
听她这么说,我心里暖暖的。
就在这时候,有个小护士急匆匆跑过来:"小李,主任找你呢,说有急事!"
"好,我马上就去。"她站起身来,对我说,"我叫李淑华,是医院内科的护士。"
"李淑华。"我也重复了一遍她的名字,挺好听的。
"对了,你那个招工考试结果下来了吗?"她关心地问。
"还没呢,估计这几天就有消息了。"我心里也挺着急。
"那你要是能进县里工作就好了,咱们以后就能经常见面了。"
听她这么说,我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我也希望能考上,这样就不用回村种地了。"
"你肯定能考上的,我相信你。"她鼓励我说。
看着她匆忙跑回医院的身影,我心里感慨万千。
没想到这个看起来文静的姑娘,心思这么细腻,还有这样的考验人的办法。
第二天我就收到了通知,招工考试我考了第三名,被县机械厂录取了。
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刻,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娘看见了,眼泪都下来了:"咱家祖坟冒青烟了,建军终于有出息了!"
爹也高兴得不行,平时不爱说话的人,那天晚上喝了二两酒,话特别多。
"建军啊,你是咱老王家第一个进城工作的,可不能给咱丢脸。"
"进了城可不能忘了咱乡下人的本分,要踏踏实实做人做事。"
村里的老支书也过来祝贺:"建军考上了,咱村里又出了个有出息的。"
邻居们都来道喜,我娘忙着招待,脸上的笑容就没断过。
我也激动得不行,赶紧收拾东西准备进城。
其实也没啥可收拾的,就是几件换洗衣服,还有几本书。
到了县里报到,厂里给安排了宿舍。
虽然是集体宿舍,住八个人,但对我来说已经是天堂了。
宿舍里有上下铺的铁床,每人一个小柜子,还有公用的洗脸盆架。
同宿舍的都是新来的工人,有县里的,也有乡下的,大家很快就熟悉了。
安顿好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去县医院找李淑华。
到了内科病房,护士站里坐着几个穿白大褂的护士。
"请问李淑华在吗?"我问。
"小李去换药了,你等一下。"一个年纪大点的护士说。
过了一会儿,李淑华拿着托盘从病房里出来,看见我眼睛都亮了。
"建军!你怎么来了?"
"我考上了,被县机械厂录取了!"我高兴地说。
"真的?太好了!"她也很为我高兴,"恭喜你,进城了!"
"还得谢谢你那天的'考验'呢,要不是遇见你,说不定我考试都没信心。"
"瞎说,是你自己有本事才考上的。"她笑着说。
从那以后,我和李淑华就成了好朋友。
下班后经常一起在县城里转转,看看电影,逛逛新华书店。
82年的县城还不大,就是几条主街,但对我们来说已经很繁华了。
那时候看电影五分钱一张票,我们常去看《少林寺》《牧马人》这些片子。
她是个很有文化的姑娘,读过不少书,家里有个小书柜,里面放着《青春之歌》《红岩》什么的。
跟她在一起,我觉得自己也长了不少见识。
有时候她值夜班,我就给她买点夜宵送过去。
那年头的夜宵也简单,就是包子、油条、豆浆啥的。
有时候我加班,她也会给我炖点汤补补身子。
她炖的银耳莲子汤特别好喝,甜丝丝的,比我娘做的都好。
日子过得平淡但是很充实。
我在厂里表现不错,干活认真,人也实在,师傅们都喜欢我。
很快就被提拔为班组长,工资也从28块涨到了35块。
李淑华也因为工作认真负责,被评为了优秀护士,奖了五块钱和一个搪瓷缸子。
那个搪瓷缸子上印着"为人民服务"几个红字,她宝贝得不得了。
回想起那个夏天,如果我没有选择帮助那个"崴脚"的姑娘,如果我只是匆匆走过,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样?
我常常想,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选择的时刻。
有时候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善举,就能改变整个人生的轨迹。
那天在县医院门口,我只是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却收获了一份真挚的友谊,还有一个全新的生活。
善良这东西,看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不容易。
但是只要你真心去做,总会有回报的,就像我娘常说的,好人有好报。
82年的那个夏天,我不光通过了招工考试,还通过了人生更重要的一场考试。
那就是做人的考试,关于善良,关于真诚,关于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能不能伸出手来。
现在想想,李淑华的那个"考验"虽然有点特别,但确实很有道理。
一个人的品格,往往就在那些不经意的小事中体现出来。
82年我去县城考试,把一崴脚姑娘送去医院,她说3个月后老地方见
天还没全亮的时候,我提着那只白底蓝边的搪瓷缸出门了。
桥面是青石板,夜里落了露,鞋底踩上去打着微滑的响。
街口的高音喇叭在电线杆上吱吱啦啦,像有人在半梦半醒之间叨叨念着该起床了。
蒸笼的热气先冒出来,豆浆味儿贴着鼻翼走,油饼在铁锅里翻身,发出清脆的“吱啦”。
我把缸沿护在掌心,口沿有一条缺口,是去年在戈壁一次夜里出勤时磕出来的。
那阵儿风大,驼背上颠,缸没摔碎,我心里就给它记了个“有数”。
我挎着帆布包,包里一叠证件,还有母亲缝的蓝格子手帕。
手帕角上绣了两枝红柳,针脚细密,院里的老邻居说这叫“手稳”。
我赶着去县里的进修考试,心里像揣着一把小鼓,节奏不急不缓。
桥背前头一人影儿一斜,竟然坐倒在路牙子上。
她提着一个灰布袋,袋里叮当轻响,像是玻璃瓶子碰在一起。
她扶着膝盖要站,又疼得吸了一口气。
“别扶,我自己来。”她抬眼看我,眉峰紧,声音却平平稳稳。
我伸出去的手在空中滞了滞,收回来,再伸出去,又收回来,心里不是滋味。
她脚踝处肿起一团,白袜子干净,沾上一点灰,就那样倔着不让人看见疼。
“医院在前头。”我说。
她看了一眼我胸前的扣子,又看了看我肩上的军包,眼里闪了一下,没多说什么。
“你赶时间。”她说。
我点头,脚尖却不往前挪。
“别磨叽。”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句。
我把缸塞进挎包,腾出双手,一弯腰就把她背了起来。
她的布袋挂在我手腕上,瓶子挨着皮肤,凉意一丝一丝往里钻。
路口卖钉鞋掌的老人眯着眼看了一眼,笑了一下,嘴角干净得像一条笔画。
县医院玻璃门把手有点冷,门上贴了张油印的纸,写着“外伤分诊”四个字。
我把她放在走廊的长木椅上,木头抛了光,坐上去滑。
挂号窗里的人戴着口罩,眼睛一抬,手一伸,收了我的两角钱,递来一个硬纸壳号牌。
外科小医生穿着白大褂,袖子卷到肘弯,说话时眼睛看着脚踝,手上利索,按住,抹药,包纱,动作像打结一根绳子。
我往饮水机打了杯热水,杯嘴对着她的唇边,她摇头,示意先放在旁边。
“有手帕吗。”医生说。
她从布袋里摸出一方蓝格子手帕,边角压得很平,递给我,让我按住药棉,说别让药棉跑位。
我的手心微微发烫,指腹下是她脚踝的温度,脉跳不急不慢,疼意一点点退。
走廊墙上的挂钟比我心里的鼓点慢了一拍,指针却不偏不倚地走。
她抬眼看我,目光稳,像一杯温水里泡着一片白糖。
“你去考试。”她说。
我“嗯”了一声,站起来,准备收拾东西。
我把挎包背好,又去拿搪瓷缸,猛然想起缸在刚才接水时借用着押在她膝盖边的药棉上了。
我手伸出去,又收回来。
她按住药棉,冲我点了一下头,示意我别管。
“我替你看着。”她说。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很自然,像和我已经约好了什么。
“桥头石狮子。”她又说了一句。
我一愣,明白过来她在说地方。
“三个月,老地方见。”她补了一句。
这话落地不响,却扎实。
我抬了抬挎包,说了声“好”,转身就往外跑。
门卫张叔拿着小扫帚正扫门口,他眼睛一抬,朝门缝处让了一寸。
“快。”他只说了一个字。
我钻过去,楼梯间有股潮味儿,像昨夜的雨在角落里没散尽。
考场里黑板擦过一遍,有水痕,粉笔渍还留在缝里。
监考老师眼镜腿上绕着一圈细胶带,像缝缝补补过的日子。
卷子摊开,作文是“我心中的光”,题目不花,却扎心。
我想起戈壁夜里的红灯,想起母亲的煤油灯,想起连队帐篷外沙粒与风的拉锯声。
我笔尖一沉,先写了风,写了红柳在风里折不断的筋骨,写了班长夜里替我们盖军大衣的背影。
我写那只口沿有缺口的搪瓷缸,写它盛过水,盛过面汤,盛过来回奔波里一口喘息。
我写那个姑娘递我手帕时眼里的那一点亮,说不出什么话,却把“合该”两个字落在我心里。
我没多用形容,字一笔一画往下落,像把绳结一圈一圈收拢。
交卷时手心出了汗,握笔的虎口上有一条浅红,像刚走过的一条路。
出门时日头升起来,县城醒透了,摊位前围着人,锅里的油条又鼓起一层泡。
我的挎包轻了一些,那只缸不在,挎在肩上的带子空了半寸。
我心里微微一歉,想着人家还在医院给我看着一件小东西。
晚上住进招待所,院子里晾着几条白毛巾,边角滴着水,一滴一滴落在青石上。
张叔递给我一盏老台灯,说“线路不稳,慢慢来”。
他窥了我一眼,笑,说“上午那姑娘,走路从容,心定”。
我“嗯”了一声,不好意思多说什么。
我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信纸是供销社卖的那种方格软纸,笔尖走起来像踩在春泥上。
我说今天差点耽误,幸得有人拉了我一把。
我没写谁,母亲懂。
夜里台灯下我想起连里的电台红灯,点一点,心里就像有人轻轻按了一下,叫你收住。
夏夜的县城有蚊子,窗外一盏黄灯泡忽明忽暗,像老实人从床头抓了一把故事,又不肯撒开手。
我从柜子里找出招待所配的铝杯接了水,铝的口感薄,贴唇一阵冰,昨天那只缸不在,桌面空出一个印子,像空下的一个人。
第二天我给医院去了趟,想把缸取回。
外科小医生说人已经回家休息了,说东西她替我临时收好,留了话。
我心里踏实了几分,等到手表的秒针走了一圈,才往招待所慢慢走。
我回部队前,县里公示了名单,黑字油印,名字清清楚楚,我的名字后跟着“进修”两个字。
张叔拍着我的肩,手心厚,声音不大,说“成了”。
“妥妥的。”他又补了一句。
我笑,说“慢慢来”。
班长老邢给我塞了一件旧军棉衣,说北边夜里凉,说脚别凉了。
我把他的心意收下,心里暖了一层又一层。
火车从县里缓缓开出,铁轨像两条条直线,平稳把人送往各自的去处。
车厢里有人吃咸花生,壳落在脚下,咔嚓咔嚓,声音像旧钟在走。
我望向车窗外,绿树一层层退后,像人翻过去的一叠旧年画。
秋风一动,县城的树叶“啪啪”落下,桥头石狮子的鼻尖上新添了一点青。
三个月到了,我早早去了桥头。
石桥下的水黄里带清,桥栏杆摸上去凉,带着石头的温吞气。
我把手插在衣兜里,掌心空着,像特意留了一件东西要接。
卖烤地瓜的小推车冒着白汽,地瓜的香甜像穿过两条街才走到舌尖上。
人来人往,影子踩过影子,谁也不认识谁。
我看见她时,她正从人群里走出来。
她穿一件洗得泛白的蓝外衣,扎着一根马尾,手里拎着一个小布包,走路一瘸不瘸的,却很稳。
她在我面前停了停,把布包递给我。
我打开,里面躺着我的那只缸。
缸沿上绕了一圈白纱,纱布的头收得很服帖,像她把一件细碎事做到了头。
“你那天急,落下了。”她说。
她说话的时候眼神平,像把东西放在桌面中央,谁也不压谁。
“我给它护了护。”她又说。
我接过缸,手心沉沉的,像把心里的一块石头从手背按回了掌心。
她从兜里又摸出那方蓝格子手帕,说洗了一遍,颜色更平了。
她把手帕放在缸旁,两个东西挨得很近,像生来就该在一起。
“我去医院做护理学员了。”她说。
“我这边进修。”我说。
她点点头,眼角轻轻一动,像风吹过红柳的一片叶。
“我爸在桥西修表,如果你表针慢了,过去叫声叔。”她笑了一下,说这话的时候像是递了一张小纸条上写着“方便”。
“好。”我说。
我们都没把话说满,站在桥边看水,看人,像两块石头在水边站定,哪里都不着急。
她把我的缸又按了一下,让它在我掌里坐稳,说“别再磕了”。
我“嘿”了一下,那是从心里冒出来的小声笑,算一句方言也算一句实话。
后来我们用信联系。
信纸有时带着药水味,信封上有时盖着医院的小章。
她写她练止血结,写她跟师傅学握针的角度,写人心跳的节律,写夜班时窗外的梧桐叶子一层层翻。
她说“别着急”,又说“慢慢来”。
我回她信写沙地里插台线的窍门,写班长如何把旧线掐短再用,写红灯一点一点亮起时心里像有了准头。
我不懂漂亮字,字挤在一块儿,像人挤公交,脸贴着脸,却谁也不踩谁。
搪瓷缸一直在我身边。
我用它接水接面汤,缸沿那圈白纱渐渐有了水痕,却没散。
每次喝水,舌头绕过那道缺口,像绕过一件小心的事。
我把蓝格子手帕叠好,放在枕边,有时夜里醒来会摸一摸,布料凉而稳,像有人在黑里轻轻拍你肩膀,说“行”。
进修的日子跟部队的日子不一样,却也规矩。
我学着用指针表测电阻,红黑表笔夹住后手得稳,不然指针一抖,数字就不真。
师傅说我手稳,说“兵有兵的讲究”。
我说“别夸我,扎实点就行”。
我晚间复习时把搪瓷缸放在手边,灯光一落,蓝边亮一下,像一圈小光圈正在呼吸。
县里那年新开了几家个体饭店,门脸儿不大,红布条子一挂,锅里炒菜声一响,就像一条街活了。
夜里放露天电影,幕布鼓鼓囊囊,每当风过,有人会捂住孩子的帽子,怕一个没拽住就被风卷走。
我站在后排,捧着半缸热水暖手,热气往上冒,眼镜片一糊,我就挪一挪。
电影里有凤凰牌自行车,有人把围巾甩了一个利落的弧度,底下“哄”地一声笑。
我也笑,笑完习惯性摸一摸缸沿,像摸一摸自己的脉。
她母亲在医院食堂蒸馒头,忙里偷空从饭桶里夹一个热乎的给我,说“路上吃了别饿着”。
我接过来,热气烫手,心里也一烫。
“谢了阿姨。”我说。
她摆摆手,说“孩子们照应着一些”。
这一句话像把门在冬天留了一个缝,风小一点,亮多一点。
进修考核那天,师傅让我们做现场检修,我把工具一一摆齐,焊锡、松香、表笔,像把一桌子小人安排到各自的位置。
我焊点的时候手腕微微发紧,心却稳,焊点亮,像一滴水定在原地。
师傅点点头,说“中”。
他说了“中”,我心里就收住了,没往高处想,脚往地下一踩,地面就是我的了。
我回到连队时,秋已深,戈壁的风带着一点盐碱味,鼻腔里一过,就像喝了一口淡淡的汤。
夜里对台,红灯安静得像一只在呼吸的小动物。
我穿上她母亲织的羊毛袜,脚背一下子暖,暖气往上爬,爬到了心窝。
我把搪瓷缸放在手边,水温刚好。
我想起桥头她说的“老地方见”,字在心里立了起来,像两只小木楔稳住了板凳脚。
冬天第一场雪来了,帐篷外白得干净。
我伸手接一片,雪花落在掌心,化成一个水点,凉,清,不带别的味。
我把蓝格子手帕铺在桌面,灯光压在手帕上,格子像一块块整齐的田,静着,等人下种。
县城又过了一年,路边多了摆修自行车的摊子,三角架半天不动一下,一动就是一声清亮的“当”。
供销社门口挂了新布告,说棉线到货,说糖票凭证分发,说人多别挤,一个个来。
我往回家的路上一抬头,看见母亲在小院门口晒棉被,棉被一翻,阳光在棉花里走了一圈。
母亲见到我,笑,嘴角往上,一句“吃了没”,就把全部担心都哏住了。
我把搪瓷缸拿给她看,说口沿让人帮着护了护。
她摸了摸,手上茧子轻轻刮过边。
“金贵。”她说。
她说金贵,不是夸它价格,是夸这份心。
她把手帕接过来,看一眼,放到箱底的衣物里,像把一件小心存的事暂时收起。
我在家住了两晚,夜里听见邻居家老收音机的沙沙声,像风从墙缝里过。
邻居大婶在井边打水,绳子在井沿上摩出一条亮线,水桶上来的时候,井里的光也跟着颤了一下。
我背着挎包往连队走时,母亲把一只小布袋塞我手里,里面是干红枣和两把花生。
我说“够了”,她说“有嚼头”。
这话搁我们当地话里叫“家里有门儿”,意思是想到你了。
我把布袋压在搪瓷缸下面,缸沿的白纱靠在布袋上,像两件物件贴着互相取暖。
春天来的时候,县城的柳树发了芽,细黄像米粒一样一颗颗冒。
我休探回来,在桥头碰见她,她穿了白大褂,胸前别了一个小牌子,写着“护理学员”。
我们在桥边买了两角钱的瓜角,汁水顺着手背往下流,我用手帕一点一点按干。
她说病房里老爷子爱看黑白电视,节目换了他就笑,说“花样真多”。
她说上夜班的时候,窗户缝里有风,护士站的小电炉子上老是温着一壶水。
我把搪瓷缸举起来,对着阳光晃了一下,蓝边上一道亮光滑过去,像有人用细笔描了一笔。
她看着缸,眼里亮了一瞬,又收住。
“缸怕磕。”她说。
“护着。”我说。
我们不说大的话。
话说大了,容易虚。
我们把每一件小事按着来,像把每一颗扣子扣到该扣的眼上。
我偶尔会去桥西看她父亲。
那是个眼睛细而亮的人,修表的时候一呼一吸很稳,放大镜在眼窝里一扣,世界就剩下表针和齿轮。
他问我表走得慢还是快,我说慢一分。
他把表打开,轻轻吹一口气,齿轮像醒了。
“灰。”他说。
他说灰,我就明白,日子里也有灰,吹一吹,指针又走起来。
春末夏初一场暴雨把县里几条街冲洗得干干净净,雨过天晴,地面上一层薄亮,像加了一层光。
我和她站在桥头的小檐下避雨,雨线像撒开的半把针,从屋檐上斜着落下来。
我们说起各自的新活路。
她说学会了配药,知道每一瓶药的味道。
她说“苦的多为好,甜的多为安”。
我说我们台站换了新电源,电压稳了,半夜不用再拍电柜。
我说“稳,比什么都强”。
雨小了,我们才往外走,脚底还带着水光。
她把手帕拧了拧,角上红柳的线更贴服了。
我回连队的路上看见公路上有一队驼队,驼铃不响,只偶尔轻轻一碰,像有人提醒你时间到了。
我把搪瓷缸从包里拿出来,喝一口水,水里有雨后的凉,舌头一圈,绕过缺口。
缺口在,缸也在。
那年秋天,我写了几封信都没寄。
不是写不好,是工作多,往往写到一半就被叫走。
后来我把那些没寄的信收在缸旁边,纸边卷起一小层,像日子里留的边角料。
冬天来得很早,北风一过,地面上就有一层薄霜。
我去台站值夜,手心里搓一搓,就有热。
门口的风给人一脸,像有人拿着一把细梳来回梳。
我把手伸进棉衣里,摸到那方蓝格子手帕,心里稳了。
我想起她说的“慢慢来”。
这三个字像一粒温药,入喉不热,过一阵子热就到了手心和脚背。
春天再来的时候,我们在桥头又见了一回。
她说她转正了,白大褂穿着也不生。
她说她母亲织的第二双袜子线头收得更服帖了。
我说班里来了个新兵,做事快,心也快,我得盯着让他慢一慢。
她笑,说“年轻气盛,慢慢收”。
我们说起桥下的水,春天的水更软,石头边缘被它磨得亮。
我把搪瓷缸递给她,她用手摸了一下蓝边,指肚在口沿的白纱上轻轻蹭了一下。
“还得护着。”她说。
“护着。”我重复了一遍。
我知道这两个字说出去不响,却能在心里扎根。
我在县里多待了半日,给母亲从供销社买了两块蓝印花布。
母亲收下,手在布上抚了一下,说“结实”。
她说结实,是她这一辈子对东西最大的夸奖。
她用布给我再做了两个手帕,边角压严,还在角上各绣了一个小字,一个“稳”,一个“顺”。
我把两个字贴在胸口,心里就有数。
我回连队后,台站的活更细了。
夜里对频,白天检修,手上的茧厚了一层又一层。
我用搪瓷缸给大家接水,缸沿的白纱换了几回,我把旧的收着,折成小块,像收着一段段时间。
班长老邢有时会拿起那缸抿一口,然后把缸沿的白纱顺顺。
他不多话,却明白这东西对我不普通。
我有时夜深了,会把蓝格子手帕铺在台面,看格子一条一条,心里把一天的事一条一条对过去。
对完之后,拿起手帕轻轻一抖,布上的灰落了,心里的小坎坷也就散了。
县里又有新的东西进来。
小卖部里摆上了黑白电视机,玻璃门柜里多了几样牙膏和香皂,带着新鲜气味。
街上骑着二八大杠的男人把车擦得亮亮的,车铃一响,像有人在远处打了招呼。
我们当兵的走在街上,肩背上压着风,脚下有声。
我肩上的挎包里有两个东西,搪瓷缸和蓝格子手帕。
它们像两盏灯,一盏在手里,亮外头,一盏在心里,亮里头。
后来我再一次参加县里的进修考核。
题目不难,难在心里那口气得稳。
我坐下,拿出手帕垫在手下,握笔的指头就不滑了。
监考老师往我们这边看了一眼,又低头看表,表针走得稳。
我写完,抬头看窗外,阳光正好。
阳光从窗框上落下来,落在我的搪瓷缸上,蓝边亮了一圈。
我心里就像有人轻轻拍了一下,说“行”。
考完走在桥上,我顺手摸了一下石狮子的鼻尖。
青石有一点凉,鼻尖被孩子摸得发亮,像年年擦出的光泽。
我站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想。
风从河面上走来,衣角轻轻动。
这时候,我听见对岸有人喊孩子的名字,声音清亮,像一串小铃。
我把缸举起来,轻轻晃了一下,缸里的水就起了一圈小小的波。
波很小,却一圈圈往外扩。
我看着波,心里像在看自己走过来的路。
路不直,却没偏。
我往前走,脚下的石板条一块一块地接着,像把日子接着走。
那一天,我在桥头等了一会儿,等她下班路过。
她远远看见我,抬了一下手,我也抬了一下手。
我们站在桥边说了几句,话都不长。
她问我“最近忙吗”。
我说“忙,稳”。
她点点头。
她说“那就好”,声音里不带别的。
我们各自往前走了一段,又回头看了一眼对方,算是照顾了一下心里的牵挂。
夜里我在台站,风和静之间反复,像两拨人安安稳稳地换班。
我把蓝格子手帕叠好,放在搪瓷缸底下,让缸坐得平一些。
灯光压下来,缸沿白纱上的线头收得更服帖了。
我知道这两个东西会跟我走很久。
它们不说话。
它们只告诉我一个意思。
护着。
我把这两个字压在心里,心里就不慌。
我也知道,有的人在桥这头,有的人在桥那头。
桥在那儿,水在那儿,人心在各自的胸腔里,一上一下,像一个老式钟表一呼一吸地走着。
我做着自己的事,过着自己的日子。
我把灯拧小了一格,红灯的光明灭,帐篷外沙粒敲了两下。
我在桌上轻轻敲了一下,像回敬它。
我把搪瓷缸端起来,抿一口水。
水过喉的时候,我听见不远处有人打了个轻轻的喷嚏,随后是一声笑。
我也笑了一下。
我想起桥头她说的那句“老地方见”。
我知道以后每有个节点,我们都可以走到那儿站一站。
不为别的。
为心里的那一点亮。
它不大。
可够用。
夜深得刚刚好。
文档上传者
热门标签
相关文档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