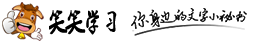欢迎来到98聘
写作《假如有一天作文》小技巧请记住这五点。(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9-26 22:56

写作核心提示:
这是一篇关于“假如有一天”作文应该注意哪些事项的文章:
"点亮想象之光:撰写“假如有一天”作文的注意事项"
“假如有一天……” 这类作文题目,如同一个充满魔力的魔法棒,轻轻一点,便能开启我们通往无限想象的世界。它鼓励我们挣脱现实的束缚,去畅想未来的可能性,描绘心中理想的生活图景,或是思考科技、社会、环境等可能发生的巨大变迁。然而,天马行空的想象固然诱人,但要写出一篇内容充实、逻辑清晰、引人入胜的“假如有一天”作文,还是需要关注一些关键事项的。
"一、 明确核心,立意新颖"
在动笔之前,首先要问自己:这个“假如有一天”的核心是什么?你最想表达什么观点或情感?是想描绘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未来,一个环境完美洁净的世界,还是一个实现个人梦想的场景?一个清晰、集中的核心是文章的“灵魂”。同时,力求立意新颖。虽然“假如有一天”是想象作文,但避免落入俗套,比如千篇一律地畅想拥有无穷财富或任意穿梭时空。尝试挖掘一些独特的视角,比如“假如有一天,人类学会了与自然和谐共生”、“假如有一天,知识不再被垄断”、“假如有一天,我成为了一个守护历史的人”等等,这样更容易让文章脱颖而出。
"二、 合理设境,逻辑自洽"
“假如有一天”的世界是虚构的
如果今天是生命的最后一天,你会怎么过?这一问题,让我瞬间破防
凌晨四点的急诊室,34岁的张磊攥着癌症确诊单,手指在手机屏幕上疯狂滑动——未读的工作群消息99+,女儿幼儿园毕业照的未接来电3个,母亲的“记得吃早饭”语音还停留在三天前。
“原来最痛的,不是化疗针扎进血管,是突然看清:我拼命追的‘未来’,正在偷走我的‘现在’。”
90%的人,都在“错付”生命
某平台做过一个扎心调查:“如果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你会后悔什么?”
2.3万人参与,答案高度一致:
• 78%的人后悔“没多陪家人”;
• 65%的人后悔“没做真正喜欢的事”;
• 52%的人后悔“没好好爱自己”。
张磊的病历本里夹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确诊前一周的行程:
周一:加班到凌晨,错过女儿家长会;
周三:应酬喝到胃出血,没回母亲电话;
周五:为了升职,把年假调岗申请撕了;
周日:女儿哭着说“爸爸是不是不要我了”,他吼了句“忙完这阵就陪你”。
“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可生命从不会等‘准备好’。”
最后一天,聪明人都在做这3件事
如果生命只剩24小时,你会怎么分配?
1. 把“必须做”换成“想做”
张磊在病房里做了件“任性”的事:
• 推掉所有工作电话,给女儿编了整晚的童话;
• 教会母亲用视频通话,说“以后想我了就点开”;
• 甚至偷偷订了束花送到妻子公司,卡片上写着“这些年,辛苦你了”。
“最后一天才明白:‘责任’不该是枷锁,‘爱’才是生命的答案。”
2. 和“遗憾”和解
李医生见过太多“最后一天”的病人:
• 有人死死攥着存折,哭着说“还没给儿子买房”;
• 有人盯着天花板,反复念“要是当初不离婚就好了”;
• 有人突然笑了,说“原来我最爱的,是楼下那棵会开花的树”。
“生命结束时,没人会后悔‘没多赚100万’,只会后悔‘没多笑100次’。”
3. 活成“限量版”,而不是“复制品”
张磊的病房窗台上,摆着三样东西:
• 女儿画的“爸爸和我”;
• 妻子织的歪扭围巾;
• 自己写的“遗愿清单”——第一条是“明天和女儿去抓蝴蝶”。
“最后一天才懂:所谓‘成功’,不是职位多高、钱多少,而是你让多少人感到‘被爱’。”
别等“最后一天”,现在就开始
张磊的主治医生说:“他不是最幸运的病人,却是最清醒的病人。”
化疗疼到浑身发抖,他哼着女儿最爱的《虫儿飞》;
半夜发烧说胡话,他喊的是“宝贝别怕,爸爸在”;
甚至在遗嘱里,他写的是:“把我的骨灰撒在女儿上学的路上,这样我每天都能陪她走一段。”
“我们控制不了生命的长度,但能决定它的温度。”
最后说点实在的
“最后一天”的假设,不是让你恐慌,是帮你看清:
• 别用“忙”当借口,冷落了爱你的人;
• 别用“等”当理由,错过了想看的风景;
• 别用“怕”当枷锁,不敢做真正喜欢的事。
评论区聊聊:
如果今天是最后一天,你最想和谁在一起?最想做什么?
(点赞破10万,下期揭秘“张磊的病房日记”)
作者说:
这个问题不是“诅咒”,是生命的“清醒剂”。我们总以为“还有明天”,可明天和意外,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
从今天开始:
• 推掉一个无关紧要的应酬,陪家人吃顿饭;
• 放下手机10分钟,认真听孩子说句话;
• 哪怕只是对镜子笑一笑,告诉自己:“今天的我,值得被好好对待。”
别让“最后一天”的遗憾,成为你一生的痛。
如果这篇文章戳中了你,请点个赞,转发给那个总说“等以后”的人,关注我,下期教你如何把“普通一天”过成“高光时刻”。
如果有一天,你总觉得自己很缺爱,记住这句话,你就赢了
如果有一天,你总觉得自己很缺爱,记住这句话,你就赢了
晚饭后,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35。新闻联播铿锵有力的片头曲,像一把钝锯,一下下割着我的耳膜。我丈夫陈阳在阳台打电话,儿子乐乐在房间写作业,只有我和我爸,陷在客厅沙发里,被这巨大的声浪包裹。我攥着遥控器,指甲掐进塑料的缝隙,却终究没有按下那个减音键。
抽屉里那张我和妈妈的合影,已经被我摩挲得起了毛边。照片上的妈妈笑得像朵向日葵,而我,扎着羊角辫,咧着没长齐牙的嘴,紧紧挨着她。妈妈走了三年,这个家,就只剩下我和沉默如山的父亲。
陈阳挂了电话进来,眉头紧锁,径直走进卧室,连一个眼神都没给我。他最近总是这样,回家越来越晚,话越来越少,身上带着一股陌生的、不属于我们家的淡香水味。我跟进去,他正脱下外套,随手扔在床上。
“又去应酬了?”我问,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他“嗯”了一声,背对着我,解开衬衫的袖扣。
沉默像黏稠的胶水,糊住了整个空间。我看着他宽阔又陌生的背影,喉咙发紧。我想问他为什么不抱抱我,为什么不和我说说公司的事,为什么我们之间只剩下这令人窒息的沉默。
“其实……”我开了口,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转过身,脸上带着一丝不耐烦的疲惫,“怎么了?有事就说。”
“没什么。”我摇摇头,把所有的话都咽了回去。他眼里的疏离像一根针,刺得我生疼。我转身想走,眼角余光却瞥见他外套口袋里滑出的一角粉色硬卡纸。
是商场的购物凭证。
我心头一跳,趁他不注意,快步走过去,将那张凭证捏在手里。借着客厅传来的电视光,我看清了上面的字:宝格丽,女士项链,消费金额:38800元。
日期是昨天。
我的生日在三个月前,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在上个月。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卡纸,它却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指尖发麻。电视里,播音员字正腔圆地播报着国际新闻,声音洪亮,清晰。可我一个字也听不见,整个世界只剩下我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声。
我爸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我身后,他手里拿着一个削好的苹果,递给我。“吃吧,饭后吃个苹果,刮油。”
他的声音在35分贝的电视声中显得有些模糊。我没有接,只是死死地盯着手里的凭证。
“怎么了?”他问,又把苹果往前递了递。
我猛地抬起头,眼眶发酸,声音都在抖:“爸,你说,是不是人老了,耳朵就不好使了?”
他愣了一下,随即有些局促地笑了笑,“人老了,机器都坏了,何况是人。你妈以前就总说我,耳朵里塞了驴毛。”
他说着,习惯性地拍了拍自己的耳朵。我这才注意到,他右边的耳朵眼,空空的。他那副戴了快十年的助听器,不见了。
而我,竟然今天才发现。
巨大的悲伤和委屈瞬间将我淹没。我觉得自己像个笑话。我在这里为了一段可能已经变质的婚姻而心神不宁,却忽略了身边最亲近的人正在无声地衰老。
我冲进卧室,陈阳正准备去洗澡。我把那张购物凭证狠狠摔在他脸上,“这是什么?陈阳,你给我解释清楚!”
他愣住了,捡起地上的凭证,看了一眼,脸色瞬间变得难看。
“你翻我东西?”他的声音冷了下来。
“我翻你东西?陈阳,你还有理了?你买这么贵的项链给谁?送给哪个?”我的声音尖利起来,完全不受控制。
“你胡说什么!”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吓人,“林蔓,你能不能别这么不可理喻!”
“我不可理喻?”我气得发笑,眼泪却不争气地涌了出来,“你每天早出晚归,回家就跟我装哑巴,现在还背着我给别的女人买几万块的项链!你和我说我不可理喻?”
我们的争吵声惊动了客厅的父亲和房间的乐乐。父亲把电视关了,整个世界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我们粗重的喘息声。
乐乐揉着眼睛站在门口,怯生生地问:“爸爸妈妈,你们在吵架吗?”
陈阳松开我,深吸一口气,走过去抱起乐乐,“没事,爸爸妈妈在讨论问题。乐乐乖,回房间睡觉。”
他抱着乐乐,从我身边走过,甚至没有再看我一眼。我站在原地,浑身冰冷。那个瞬间,我无比清晰地感觉到,这个家,好像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卧室的,只记得父亲一直站在客厅,昏黄的灯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没问我发生了什么,只是默默地把那个已经有些氧化的苹果,又塞到了我手里。
“蔓蔓,”他叫我的小名,声音沙哑,“太晚了,去睡吧。”
我握着那个冰凉的苹果,回到了冰冷的床上。陈阳没有回来睡,我猜他去了书房。黑暗中,我睁着眼睛,一遍遍回想他看我的眼神,那种冰冷的、不耐烦的眼神。
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我因为考试没考好,不敢拿卷子给爸妈签字。妈妈看出了我的不对劲,拉着我的手,温柔地问我怎么了。我哇的一声哭出来,说我怕爸爸骂我。妈妈抱着我,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是什么来着?我拼命地想,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记忆像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模糊不清。
我只记得,那天晚上,妈妈给我煮了一碗桂花小圆子,爸爸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在我的试卷上签了字。第二天早上,我的书包里多了一个新文具盒。
那时候的爱,好像都藏在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里。可现在,我却什么都感受不到了。我只觉得冷,从心底里透出来的冷。
成年人的崩溃,是从怀疑一个拥抱的真伪开始的。而我,现在连一个拥抱都得不到了。
第二天早上,我顶着两个黑眼圈起床,陈阳已经走了。餐桌上放着他买回来的早餐,豆浆还是温的。我却一点胃口都没有。
父亲也起得很早,正在厨房里忙活。他见我出来,指了指桌上的早餐,“陈阳买的,趁热吃。”
我没作声,倒了杯水喝。
父亲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没再说话。他标志性的动作就是这样,每次想说什么,最后都化为一声叹息,然后默默地把所有事情都做了。他把灶台擦得锃亮,把垃圾分好类,再把乐乐换下来的脏衣服泡进盆里。
乐乐背着书包从房间里出来,看到我,小心翼翼地问:“妈妈,你今天还生气吗?”
我勉强笑了笑,摸了摸他的头,“不生气了。快吃早饭,要迟到了。”
乐乐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外公,突然凑到我耳边,用极小的声音说:“妈妈,你是不是不喜欢外公?为什么你总对他皱眉头?”
孩子无意识的话语,像一把最锋利的刀,精准地刺进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我愣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是啊,我什么时候开始对父亲这么不耐烦了?是因为他越来越慢的动作,越来越差的记性,还是因为那台永远在35分贝的电视机?我总觉得他不理解我,不关心我,可我,又何尝去关心过他呢?
送完乐乐去幼儿园,回家的路上,我鬼使神差地把车开到了陈阳公司楼下。我把车停在对面的马路边,像个见不得光的私家侦探,死死地盯着公司门口。
我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或许只是想给自己一个死心的理由。
中午十二点,陈阳从大楼里走了出来。他身边,跟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她穿着一条米色的连衣裙,长发飘飘,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他们并排走着,阳光洒在他们身上,看起来那么和谐,那么刺眼。
我看到陈阳很自然地接过女孩手里的文件袋,还侧过头对她说了些什么,逗得她咯咯直笑。然后,我看到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精致的丝绒盒子,递给了那个女孩。
是宝格丽的盒子。
我的血一下子冲到了头顶,视线瞬间模糊。我死死地踩住刹车,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我看着那个女孩惊喜地捂住嘴,然后给了陈阳一个大大的拥抱。
一切都证实了。我的怀疑,我的不安,都不是空穴来风。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把车开回家的。一路上,我闯了两个红灯,被后面的车按了无数次喇叭。回到家,我把自己摔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放声大哭。
我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丈夫的背叛,父亲的疏离,连我自己,都快不认识自己了。我像一个贪婪的、永远也填不满的黑洞,拼命地向外索取着爱,却一次次地被推开。
我恨陈阳的欺骗,也恨自己的无能。为什么我活得这么失败?
哭累了,我从床上爬起来,开始疯狂地收拾东西。我要离婚,我一秒钟都不想在这个充满谎言的家里待下去了。我拉开衣柜,把陈阳的衣服一件件地扔在地上,然后又去拉那个我们共用的抽屉。
抽屉被卡住了,我用力一拽,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在一堆杂物下面,我看到了一个陈旧的木盒子。我认得,这是我爸的东西。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把这个盒子放到了我们的卧室。我打开盒子,里面是一些发黄的信件,还有一本同样陈旧的助听器。
助听器的一角已经摔坏了,看得出是旧伤。我拿起它,心里忽然涌上一股复杂的情绪。
我拿起那些信,是妈妈写给爸爸的。信里的字迹娟秀,充满了爱意。
“老林,今天女儿在学校评上三好学生了,她第一个跑回来告诉你,你却因为厂里加班不在家。她有点失落,但我知道,她心里是为你骄傲的。”
“老林,你又忘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不过没关系,你给我带回来的那根烤红薯,比什么礼物都甜。我知道你心里有我。”
“老林,你的耳朵越来越不好了。我让你去医院,你总说没事。你是不是怕花钱?我偷偷给你在抽屉里塞了五百块,你明天必须去!”
信的最后,还有一张医院的诊断单。是父亲的,诊断结果是“神经性耳聋,不可逆”。日期是五年前。
我拿着那张诊断单,手抖得厉害。原来,五年前,他的耳朵就已经……而我,竟然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抱怨他的电视声太大,却不知道,那巨大的声浪,是他努力想要抓住这个世界的唯一方式。
35分贝,那不是他世界的音量,而是他世界里,唯一剩下的音量。
我蹲在地上,抱着那个木盒子,哭得泣不成声。我一直以为自己是缺爱的那一个,可原来,我才是那个最吝啬给予爱的人。
我决定去找父亲谈谈。我走进他的房间,他正戴着老花镜,费力地用一根针线,缝补着乐乐的一件旧外套。
“爸。”我轻轻叫了一声。
他抬起头,看到我,有些意外,“怎么了?”
我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把那张诊断单递给他。“爸,对不起。”
他看了看诊断单,又看了看我,沉默了很久,最后只是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手背。“都过去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哽咽着问,“为什么不换个新的助听器?”
“旧的这个,是你妈给我买的。舍不得扔。”他低声说,浑浊的眼睛里泛起一层水光,“坏了,就听不见了。听不见也好,心里清净。”
他顿了顿,又说:“蔓蔓,我知道你最近心里不舒坦。陈阳那孩子,我看着他长大的,他不是那种人。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摇摇头,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有些爱,像迟钝的旧手机,不是没有信号,只是你没有耐心等它连接。”父亲的声音很轻,却像重锤一样敲在我的心上。
我开始反思,我和陈阳之间,真的走到了绝路吗?还是,只是我被自己的不安和猜忌蒙蔽了双眼?
下午,我决定去一趟数码城。我给我爸买了一款最新、最智能的助听器,据说可以连接手机,调节不同的场景模式。
回到家,我把助听器拿给我爸,他愣住了,摆着手说不要,“太贵了,我用不着这么好的。”
“爸,这个你必须收下。”我态度坚决。
我花了一个多小时,耐心地教他怎么使用。怎么连接手机蓝牙,怎么调节音量,怎么切换“安静模式”和“嘈杂模式”。他的手指很笨拙,总是在屏幕上点错地方。我一遍遍地教他,没有丝毫不耐烦。
当我帮他戴上新的助听器,打开开关的那一刻,他浑身一震。
“蔓延,”他看着我,眼睛里充满了惊奇,“我能听见……我能听见窗外的鸟叫了。”
我的鼻尖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我还能听见,”他侧过头,仔细听了听,“厨房里,水龙头像是在滴水。”
我点点头,“嗯,有点漏水,我待会儿就去修。”
他笑了,那是妈妈走后,我见他笑得最开心的一次。他像个得到了新玩具的孩子,对这个重新变得清晰的世界充满了好奇。
“原来,”他感慨道,“我错过了这么多声音。”
看着他脸上的笑容,我心里的坚冰,仿佛也融化了一角。
晚上,我没有再提离婚的事。我给陈阳发了条信息:今晚早点回家,我有话跟你说。
他很快回复:好。
我做了一桌子菜,都是他喜欢吃的。父亲戴着新助听器,坐在客厅看电视。这一次,电视的音量是15,一个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数字。
乐乐放学回来,好奇地看着外公,“外公,你的电视今天怎么这么安静?”
父亲笑着摸了摸乐乐的头,“因为外公的耳朵,修好了。”
七点半,门铃响了。我走去开门,陈阳站在门外,手里提着一个蛋糕。
“今天不是谁的生日。”我说。
“我知道,”他走进来,把蛋糕放在餐桌上,“道歉用的。”
我们坐在餐桌前,谁也没有先开口。父亲和乐乐很识趣地回了房间。
“对不起。”我们几乎同时说道。
我愣住了,他也愣住了。
“你先说。”他说。
我深吸一口气,把白天看到的一切,我的怀疑,我的痛苦,都说了出来。说到最后,我还是没忍住,声音带上了哭腔。
他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等我说完,他才开口,声音里充满了疲惫和歉意。
“对不起,林蔓,是我不好,没有跟你解释清楚。”他揉了-揉后颈,这是他一贯的标志性动作,每当他感到压力或者不知道如何表达时,就会这样。
“那个女孩,是我表妹,姗姗。她刚从国外回来,你知道的。”
我点点头。
“她丈夫出轨了,正在闹离婚。她一个人,心情很不好。我作为哥哥,总得安慰安慰她。”
“那条项链……”
“是给她的。她下周生日,我想让她开心一点,重新开始。这事她不想让家里长辈知道,怕他们担心,所以我也没告诉你。”
“那你身上的香水味……”
“是姗姗的。那天她哭得很伤心,我抱了抱她。”他看着我,眼神真诚,“林蔓,对不起,让你误会了。我只是觉得,这是她的私事,我不好多说。”
他的解释合情合理,可我心里还是有个疙瘩。
“那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淡?回家也和我没话说?”
他沉默了。
良久,他才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公司最近在做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我是负责人,压力很大。每天焦头烂额,回到家,就想安安静静地待一会儿。我以为……我以为你会懂的。”
他的话,像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
我以为他不再爱我,他以为我能懂他。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却活在两个世界里。
“我们用前半生向父母索取,用后半生去偿还一份永远也还不清的沉默。”我突然想起了父亲白天说过的话。而我和陈阳,我们是不是也正在用沉默,来消耗彼此的爱?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聊他的工作压力,聊我的不安,聊我们之间越来越少的沟通。我们像两个医生,小心翼翼地解剖着我们濒临死亡的婚姻。
没有争吵,没有指责,只有平静的叙述。
聊到最后,我问他:“陈阳,你还爱我吗?”
他没有立刻。他站起身,走到我身后,从背后轻轻地抱住了我。“我不知道怎么说那些好听的话。我只知道,每次加班到深夜,想到家里有你和乐乐在等我,我就觉得没那么累了。”
他的下巴抵在我的头顶,暖暖的。
“这个家,不能没有你。”他说。
我的眼泪,一滴一滴,落在了他的手背上。
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眉头又皱了起来。是公司打来的。
他接起电话,走到阳台。我看着他的背影,高大,却也疲惫。
挂了电话,他走回来,脸上带着歉意。“公司出了点急事,我得过去一趟。”
“去吧。”我说,“路上小心。”
他点点头,拿起外套就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又停下,转过身,快步走回来,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
“等我回来。”
门关上了。我站在原地,摸着额头上残留的余温,心里五味杂陈。
我忽然意识到,我一直想要的,不过就是这样一个拥抱,一个亲吻,一句“等我回来”。我需要的,是这种被看见、被在乎的感觉。
可我,又何曾真正地去看过他,去在乎过他的疲惫和压力?
我走进厨房,想倒杯水。却看到水池边,放着一个剥好的柚子,每一瓣都去了皮,去了白筋,整整齐齐地码在盘子里。是我最喜欢吃的样子。
我知道,这是陈阳剥的。他知道我嫌剥柚子麻烦,每次都会默默地帮我弄好。
这就是他的爱。笨拙,沉默,却无处不在。
婚姻里最奢侈的,不是我爱你,而是我懂你那些说不出口的疲累。我一直追求着前者,却忽略了后者。
接下来的几天,我和陈阳之间有了一种微妙的默契。他依然很忙,但每天都会抽出十分钟,跟我说说公司的事。我不再追问他几点回家,只是会在他进门的时候,递上一杯温水。
我们没有刻意地去修复什么,但那些裂痕,仿佛在这样无声的关怀中,一点点地愈合了。
周末,我大扫除,整理家里的旧物。在书房的角落里,我发现了一个落满灰尘的箱子。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妈妈的日记。
我盘腿坐在地上,小心翼翼地翻开那本已经泛黄的日记本。
妈妈的字,还和信里的一样娟秀。
“1990年6月1日。今天蔓蔓四岁了,老林给她做了一架木头小马,她高兴得不得了。老林嘴上不说,我知道他熬了好几个通宵才做好的。这个男人,爱都藏在手里,不在嘴上。”
“1998年9月15日。今天和老林吵架了,因为他又不记得我们的纪念日。我气得回了娘家。晚上,他骑了两个小时的自行车来接我,手里还提着一袋我最爱吃的糖炒栗子。看着他满头大汗的样子,我就什么气都消了。这个笨蛋。”
“2005年3月8日。女儿长大了,开始有心事了。她总觉得爸爸不爱她,因为爸爸从没对她说过一句‘我爱你’。我该怎么告诉她,她爸爸的爱,都在她每天早上喝的那杯热牛奶里,都在她每一次晚归时,门口为她亮着的那盏灯里。”
我一页一页地翻着,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日记本上,晕开了一片片墨迹。
我终于在日记的最后一页,找到了那句话。
那是妈妈写给她自己的,也是写给我的。
“如果有一天,你总觉得自己很缺爱,记住这句话:别总向外要,要学着自己给。给别人你的关心,给生活你的热情,给你自己一份看见爱的能力。当你学会了给予,你就会发现,你早已被爱包围。你就赢了。”
别总向外要,要学着自己给。
我反复默念着这句话,像是在念一句咒语。那一刻,我醍醐灌顶。
我一直以来的痛苦,不就是因为我总是在向外索取吗?我向父亲索取关心,向陈阳索取浪漫,我把自己当成一个等待被灌溉的花瓶,一旦外界停止输送,我便觉得自己会枯萎。
可我忘了,我自己也可以是水源。
原来不被爱是一种错觉,感受不到爱才是真的顽疾。我病了很久,今天,终于找到了药方。
那天下午,我把父亲和陈阳叫到客厅。我把我找到的妈妈的日记,读给他们听。
我读得很慢,读到最后,我们三个人都红了眼眶。
父亲握着我的手,老泪纵横,“你妈……她什么都知道。”
陈阳坐在我身边,紧紧地搂着我的肩膀。他什么也没说,但我知道,他懂了。
傍晚,我们一家人去公园散步。夕阳的余晖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乐乐在前面追着鸽子跑,我和陈阳牵着手,慢慢地走在父亲身后。
父亲戴着新助听器,饶有兴致地听着周围的一切。他指着一棵大树,对我说:“蔓蔓,你听,有蝉在叫。”
我笑着点点头。
“你小时候,最喜欢夏天。因为可以听蝉叫,可以吃西瓜。”父亲说。
“爸,你还记得。”
“怎么会不记得。”他转过头,看着我,目光温和,“你的每一件事,我都记得。”
我看着父亲鬓角的白发,和他眼角的皱纹,心里涌上一股暖流。
爱不是索要和证明,而是看见和给予。我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明白这个道理。
从公园回来,陈阳接到了他表妹姗姗的电话。电话里,姗姗的声音听起来轻松了不少。她告诉我们,她已经决定离婚,并且找到了新的工作,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挂了电话,陈阳对我说:“姗姗说,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上次,让我也谢谢她。”
我愣了一下,才想起上次我们吵架后,我让陈阳转告姗姗,谢谢她让我看清了自己的问题。
陈阳笑着说:“她说,是你的话点醒了她。让她明白,幸福不是靠别人给的,要靠自己去争取。”
我笑了。原来,在我学会给予的同时,我也在被这个世界温柔地回应着。
生活回归了平静,但又有些什么不一样了。
家里的电视音量,有时是15,有时是20。父亲会根据不同的节目,自己调节。偶尔他忘了,声音大了,我会笑着提醒他一句,他也会马上调小。那台曾经让我无比烦躁的电视机,现在成了我们之间温情互动的道具。
陈阳不再是那个沉默的丈夫。他会和我分享工作中的趣事和烦恼,我也会和他聊聊乐乐在学校的情况,或者我新学的菜色。我们的话题,从“你应该”和“你为什么不”,变成了“你今天怎么样”和“我跟你说件好玩的事”。
他的口头禅还是那句“行了,我知道了”。但现在,当我对他说“爸的降压药快没了”时,他说“行了,我知道了”,意味着“我马上去买”;当我抱怨工作累时,他说“行了,我知道了”,意味着“辛苦了,快歇歇吧”;当我们为了一件小事争执时,他说“行了,我知道了”,意味着“别吵了,听你的”。
同一句话,在不同的情境下,有了不同的温度。
我也不再是那个充满怨气的妻子和女儿。我开始学着关心父亲的身体,陪他下棋,听他讲过去的故事。我开始学着理解陈阳的压力,在他疲惫的时候,给他一个拥抱,而不是一句质问。
我不再计算着谁爱谁更多,不再用付出来衡量感情的深浅。
我发现,当我不再执着于索要爱的时候,爱,反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向我涌来。
父亲会在我加班晚归时,给我留一碗热汤。
陈阳会出差时,每天雷打不动地和我和乐乐视频。
乐乐会用他稚嫩的画笔,画我们一家三口手牵手的样子,画上还有一个大大的太阳。
这天晚上,又是一个普通的周末。
父亲坐在沙发上,戴着老花镜,看他喜欢的京剧节目,嘴角带着一丝笑意。乐乐趴在地毯上,聚精会神地拼着他的乐高。陈阳在厨房里切水果,是我最爱吃的哈密瓜。
晚饭后,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22。京剧的唱腔婉转悠扬,混着厨房传来的切水果的声音,和乐乐偶尔发出的欢呼声,构成了一曲最动听的家庭交响乐。
我坐在他们中间,心里一片宁静。
我拿起手机,点开陈阳的微信对话框,指尖在屏幕上犹豫了很久。
我输入了一个字:“我”。
然后,我抬起头,正好对上陈阳从厨房里探出头的目光。他看见我在看他,对我扬起一个温柔的笑容,然后指了指果盘,用口型对我说:“马上好。”
我的心,瞬间被填得满满的。
我看着屏幕上那个孤零零的“我”字,笑了笑,然后按下了删除键。
有些话,不必说出口。
有些爱,早已融化在每一个平凡的日落黄昏里。
我放下手机,走到父亲身边,轻轻地靠在他的肩膀上,就像小时候一样。他拍了拍我的背,什么也没说。
但我知道,我们都懂。
文档上传者
热门标签
相关文档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