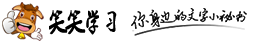欢迎来到98聘
写作《严厉的爱作文》小技巧请记住这五点。(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10-01 17:11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严厉的爱”的作文,需要关注以下几个关键事项,以确保文章立意深刻、结构清晰、情感真挚:
"一、 理解“严厉的爱”的内涵:"
"核心定义:" 首先要明确“严厉的爱”不是简单的“打骂”,而是指父母或长辈出于对子女或晚辈的深切关爱和期望,采用严格的要求、纪律甚至批评、惩罚的方式,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成长、改正错误、培养良好品格和独立能力。这种爱往往伴随着高要求和严标准。 "辩证关系:" 理解“严厉”与“爱”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严厉是手段,爱是目的;没有爱的严厉是冷酷的压迫,没有严厉的爱则可能放任自流,不利于长远发展。
"二、 选题与立意:"
"具体化:" 避免泛泛而谈。选择一个具体的场景、事件或人物经历作为切入点,让“严厉的爱”变得有血有肉。例如: 父母对你学习或某项技能的严格要求。 老师对你的纪律或品行的严格管理。 某种严厉的祖辈教育方式。 "明确观点:" 确定你想要表达的核心观点。是肯定严厉爱的积极作用?是探讨严厉爱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爱你,严厉的战老师|烟台中小学生习作园地
栖霞市实验小学3年级10班 苗永成
指导教师:语竞
从幼儿园到三年级,我遇到了许多老师,但是有一位老师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她就是我一二年级的数学老师——战老师。
她高高的个子,有着一头披肩长发,美丽极了。她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像能看穿我们的小心思一样。每当我做错事,那双眼睛就会严肃地盯着我。
记得有段时间,我在做数学题时,明明计算都对了,却总是把答案抄错,考试因此丢了很多分。我自己还不太在意,觉得只是小毛病。战老师发现后,非常严厉地批评我。她皱着眉头说:“粗心不是小问题,这是学习态度不端正!”我当时有点难过,但也明白了老师是为了我好。
从那以后,我每天做完作业,都会像战老师提醒的那样,认真检查三遍。考试时我也提醒自己一定要细心!最终在二年级期末考试中数学取得了全班第六的好成绩。
如今我已经上三年级了,但战老师的教导我一直记在心里。谢谢您,战老师!您的严厉像一盏灯,照亮了我前进的路。祝您教师节快乐!
为激发中小学生的写作兴趣,给他们提供一个展示才华的平台,烟台市融媒体中心大小新闻教育频道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征集习作,内容不限,体裁不限,字数不限,只要能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情感即可。欢迎同学们踊跃投稿,也欢迎各位老师荐稿。作品可以配发小作者的生活照。
投稿邮箱:121157218@QQ.com
提醒:投稿时请注明小作者姓名、学校和班级,以及“习作园地”字样。
责编:刘岩
畸形的爱(短篇小说)
妈熬的鱼汤,总比晓雯的少一股腥味。
这事我没敢跟晓雯说。婚姻里有些真话,是不能拿到台面上来的,像桌子底下的灰,你知道它在,但只要不趴下去看,就能假装家里很干净。
妈是礼拜天下午过来的,带着她那锅刚从菜市场活杀的鲫鱼,和我五岁女儿豆豆最爱的酱蹄髈。她有我们家的钥匙,门锁“咔嗒”一声,她就站在了玄关,像一个无需通报就能随时视察领地的将军。
晓雯正在客厅地垫上陪豆豆搭积木,闻声回头,脸上的笑意僵了零点五秒,才重新堆起来:“妈,您来啦。”
“嗯,给豆豆送点吃的。”妈换上那双她专属的暗红色棉拖,径直走向厨房,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屋子,“家里一股味道,窗户也不开,年轻人就是不讲究。”
我赶紧起身去开窗,试图用这个动作化解弥漫在空气中的尴尬。冷风灌进来,晓雯下意识地拢了拢女儿的衣服。
妈的鱼汤,永远是奶白色的,浓稠得像化开的玉。她盛了两碗,一碗给豆豆,一碗给我,唯独没有晓雯的。这不是疏忽,是一种无声的宣告。她说:“晓雯不爱吃鱼,一股子腥味,她闻着难受。”
晓雯低着头,给豆豆擦了擦嘴角的油,轻声说:“是,妈记性真好。”
我看着她顺从的侧脸,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知道,她最爱喝鱼汤,尤其是鲫鱼汤。刚结婚那会儿,她总缠着我,让我学着做给她喝,说那是她小时候的味道。可自从我妈第一次评价她做的鱼汤“腥味太重,差点火候”之后,她就再也没碰过。
饭后,妈没急着走,她拿出随身带着的小抹布,开始擦拭电视柜。那块抹布,像她的权杖,所到之处,皆是她的领地。她一边擦,一边状似无意地问:“陈阳,你们上个月水电费怎么用了这么多?我看了单子,比上个月多了快一百块。”
我还没想好怎么,她又转向在厨房洗碗的晓雯:“晓雯啊,不是妈说你,过日子要精打细算。你那个洗碗机,一度电呢,费水又费电,哪有手洗的干净?”
晓雯的背影顿了一下。我知道,那个洗碗机是我偷偷给她买的生日礼物,因为她的手一到冬天就容易皲裂。
“还有豆豆身上这件衣服,”妈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扫过来,“我看不像去年的款吧?小孩子家家,长得快,衣服不用买那么好的,穿穿亲戚家旧的就行,干净暖和就成。”
空气仿佛凝固了。我看到晓雯关了水龙头,慢慢转过身,手上还沾着泡沫。她看着我,眼神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那眼神像一把锥子,扎在我心里最软的地方。
那天晚上,妈走了之后,晓雯一句话也没说。她给豆豆洗了澡,讲了睡前故事,然后自己默默地进了浴室。我听到里面传来很轻很轻的、压抑着的抽泣声。
我站在浴室门口,手抬起来,又放下。我知道我该进去,抱抱她,说几句安慰的话。可我的脚像灌了铅。我怕,我怕她会问我:“陈阳,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答不上来。
因为我知道,在我和晓雯的世界里,我妈是那股永远不会散去的、鱼汤的腥味。它提醒着晓雯,她是个外人;也提醒着我,我永远是那个没断奶的孩子。而这锅名为“爱”的汤,正在慢慢烫死我的婚姻。
第一章:钥匙
那把钥匙,是矛盾的根源。
房子是婚后我和晓雯贷款买的,我妈象征性地出了五万块钱,名义上是“赞助”,实际上是取得了对这个家永久的“视察权”。交房那天,装修公司送了两把钥匙,我给了晓雯一把,另一把,在我妈殷切的目光下,自然而然地交到了她手里。
“妈拿着,方便。万一你们俩出差或者忘了带,我还能过来浇浇花,通通风。”她笑得一脸慈爱,晓雯当时也没说什么。
我们都以为,“方便”只是偶尔。没想到,它成了日常。
妈退休后,时间多得像海绵里的水。她几乎每天都会在我们上班后过来一趟。起初是帮我们收拾屋子,把我们随手乱放的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晓雯还感激过,说:“妈真是爱干净。”
可渐渐地,事情变了味。
晓雯买的一束鲜花,第二天可能会被换成妈认为“好养活”的绿萝。她新买的香薰机,会被收进柜子,理由是“这东西闻多了对身体不好”。她放在床头柜上的一本英文小说,会被我妈换成《老年养生大全》,还特意跟我说:“让晓雯也看看,提前预防。”
最让晓雯无法忍受的,是她的衣柜。
有一次,晓雯周末想穿一件新买的吊带裙,打开衣柜却怎么也找不到。最后,在最角落的箱子里翻了出来,吊牌还挂着,却被叠得皱皱巴巴。妈的声音像背景音一样响起:“那件衣服布料太少了,穿出去像什么样子。我给你们收好了,等以后家里有客人的时候当抹布用。”
晓t雯那天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把那件裙子扔进了垃圾桶。
我试图跟妈沟通过。“妈,”我斟酌着词句,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像是在撒娇,而不是质问,“您以后过来,先给我们打个电话呗。有时候晓雯在家休息,您突然开门进来,她会吓一跳。”
妈正在拖地,她停下来,直起身子,用那双仿佛能洞察一切的眼睛看着我:“怎么,我来自己儿子家,还要预约?陈阳,你是不是觉得妈烦了?嫌妈老了,管得宽了?”
她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妈这辈子,没别的盼头,就盼着你好。你爸走得早,我一个人把你拉扯大,吃了多少苦……”
又是这样。每一次我想建立边界,她都会迅速地退回到一个含辛茹苦的寡母角色里,用她前半生的苦难,来堵住我所有想说的话。这招百试百灵。我立刻就溃不成军,上前扶住她:“妈,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就是怕您累着。”
“只要你们好,妈就不累。”她拍拍我的手,脸上露出胜利者宽容的微笑。
那次沟通,以我的完败告终。
真正让“钥匙”问题爆发的,是晓雯的日记本。
晓雯有写日记的习惯,用一个带密码锁的本子。那个本子,她一直放在床头柜最下面的抽屉里。那天晚上,她想写点东西,打开抽屉,却发现本子被挪动了位置,密码锁的滚轮上,有被人拨动过的细微划痕。
她坐在床边,拿着那个本子,手都在抖。她没哭,也没闹,只是看着我,一字一句地问:“陈阳,这个家,还有什么是属于我的吗?”
我百口莫辩。
我冲动地拿起电话,想打给我妈,质问她。可号码拨到一半,我又怂了。我能想象到电话那头的场景:她会先是震惊,然后是委屈,最后是痛心疾首地控诉,说她只是打扫卫生时不小心碰到了,我们怎么能这么想她,我们太让她寒心了。
最终,电话也没打。
那天晚上,我和晓雯分房睡了。我躺在客房的床上,闻着陌生的被褥气味,第一次感到了恐慌。我意识到,这把钥匙,锁住的不是房门,而是我的婚姻。它像一把悬在我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掉下来,把我和晓雯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切,劈得粉碎。
我辗转反侧,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必须把钥匙拿回来。
第二天,我破天荒地请了半天假,去了我妈家。我没提前打招呼。我想用她对待我们的方式,来让她体会一下那种边界被侵犯的感觉。
我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门。
妈正在客厅里,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地给豆豆织毛衣。看到我突然出现,她愣住了。
“阳阳?你怎么这个点回来了?单位没事?”
“妈,”我深吸一口气,把练习了一路的开场白说了出来,“我来拿点东西。”
我没说拿什么,径直走到她面前,摊开手:“妈,我们家的钥匙,您给我吧。”
妈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她手里的毛衣针“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她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受伤,仿佛我不是在要一把钥匙,而是在要她的命。
“陈阳……你这是什么意思?”她的声音在发颤。
“没什么意思,”我强迫自己不去看她的眼睛,“晓雯觉得……我们还是自己管钥匙比较好。您想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去接您。”
“是晓雯让你来的,对不对?”她突然激动起来,声音拔高了八度,“我就知道!她就是嫌我这个老婆子碍眼!她就是想把你从我身边抢走!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凭什么被她这么作践!”
“妈!跟晓雯没关系,是我的意思!”
“你的意思?”她冷笑一声,眼泪滚了下来,“你会有这个意思?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还不了解你?陈阳,你太让妈失望了。为了一个外人,你这么对自己的亲妈……”
她开始哭,那种压抑了几十年的、带着巨大委屈的哭声,像一把钝刀,在我心上来回地割。我知道,她又在用她的苦难绑架我。我知道这是她的武器。可我,还是心软了。
就在我快要投降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晓雯。
我走到阳台去接。
“怎么样了?”她的声音很平静。
“在……在谈。”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晓雯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决绝的语气说:“陈阳,今天你要是拿不回那把钥匙,我们就换把锁吧。连同我们的婚姻,一起换掉。”
电话挂了。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车水马龙。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这不是一把钥匙的问题,这是一场战争。一场关于边界、尊重和家庭主权的战争。而我,不能再当逃兵了。
我走回客厅,捡起地上的毛衣针,放到我妈手里。然后,我跪了下来。
“妈,”我看着她,眼泪也忍不住了,“对不起。我知道您为我付出了多少。但是,我已经长大了,我有了自己的家,有自己的妻子。我爱您,我也爱她。我不能因为爱您,就去伤害她。这个家,需要有界限。不是为了把您推开,而是为了让我们所有人都活得更舒展。”
“求您,把钥匙给我。就当是……成全您的儿子吧。”
妈呆呆地看着我,眼泪流得更凶了。我们母子俩,就这么相对无言,任由眼泪淹没了一切。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自己会跪到地老天荒,她才颤抖着从口袋里,掏出了那串钥匙。
她没有递给我,而是直接松开了手。
钥匙掉在冰冷的地板上,发出一声清脆又沉重的声响。
像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第二章:账本
拿回钥匙后,家里安静了大约半个月。
这半个月,是我和晓雯婚后最轻松的一段时光。我们可以在周末睡到自然醒,不用担心一睁眼就看到我妈在客厅里忙碌的身影。晓雯重新买回了香薰机,整个屋子都弥漫着她喜欢的橙花香味。她甚至还从床底下翻出了那件被我妈嫌弃的吊带裙,虽然没穿出去,但她把它熨烫平整,挂在了衣柜最显眼的位置。像是在宣告一种主权的回归。
我妈没有再不请自来。她只是每天晚上准时打来电话,问我吃了什么,穿得暖不暖,豆豆有没有听话。对晓雯,她绝口不提。这种刻意的忽略,比争吵更让人窒息。
我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平静在那个周六的家庭聚会上被打破。我小姨过生日,在外面订了包间,我们全家都去了。
席间,气氛还算融洽。我妈抱着豆豆,给她夹菜,讲故事,俨牲一个慈爱的奶奶。晓雯也表现得体,给我妈和我小姨都敬了酒,说了不少祝寿的吉利话。我一度以为,“钥匙事件”已经翻篇了。
饭吃到一半,小姨开玩笑地对我说:“陈阳啊,最近是不是发财了?看晓雯手上那个镯子,得不少钱吧?”
我心里“咯噔”一下。晓雯手腕上戴的是上周我刚给她买的生日礼物,一个细细的翡翠镯子。价格不菲,是我攒了小半年的私房钱。我没敢告诉我妈。
晓雯的笑容也有些不自然,她下意识地想把手缩回去。
我妈的目光,像X光一样扫了过来。她放下筷子,拿起晓雯的手,仔仔细细地端详着那个镯子。包间里的灯光照在翠绿的镯子上,反射出一种冰冷的光。
“成色是不错,”我妈的声音听不出喜怒,“晓雯,这个得一两万吧?”
晓雯没说话,只是看着我。
我头皮发麻,硬着着头皮说:“妈,没多少钱,就是一个心意。”
“没多少钱是多少钱?”我妈不依不饶,“你们俩,一个月工资加起来也就两万出头,房贷车贷,豆豆上幼儿园,哪样不要钱?还买这么贵重的东西,日子不过了?”
她的声音不大,但足以让整个包间的亲戚都听见。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身上。小姨尴尬地打圆场:“哎呀姐,年轻人嘛,浪漫一下。陈阳疼老婆,是好事。”
“疼老婆不是这么个疼法!”我妈的声调猛地拔高,“这是打肿脸充胖子!过日子,要脚踏实地!我们那个年代,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才有了今天。他们倒好,挣一个花两个,以后怎么办?老了喝西北风去?”
晓雯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最后变成了毫无血色的苍白。她猛地站起来,手腕上的镯子因为动作太大,磕在了桌沿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
“妈,”她看着我妈,眼睛里闪着水光,声音却异常坚定,“这个镯子,是我和陈阳自己的钱买的。我们怎么花,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有我们的生活方式,也许不符合您的标准,但我们自己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说完,她转身就走出了包间。
我愣在原地,脑子一片空白。这是晓雯第一次,当着所有亲戚的面,公开反驳我妈。
我妈也惊呆了,她大概从没想过,一向温顺隐忍的儿媳妇,会突然爆发出这么大的能量。她的脸涨成了猪肝色,指着我的鼻子骂:“陈阳,你看看!你看看你娶的好媳妇!这就是你疼出来的!翅膀硬了,敢跟我顶嘴了!”
我追出饭店的时候,晓雯正站在路边等车。晚风吹起她的长发,她的背影在霓虹灯下显得格外单薄。
“晓雯……”我走过去,想拉她的手。
她躲开了。
“陈阳,我们谈谈吧。”她转过身,路灯的光照亮了她脸上的泪痕,“我受够了。真的,我一天也忍不下去了。”
那天晚上,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晓雯把这几年积压的所有委屈,像倒豆子一样,全都倒了出来。从我妈嫌弃她做的菜咸了淡了,到干涉她给豆豆报哪个兴趣班;从私自扔掉她的东西,到今天当众让她难堪。
“你知道最让我绝望的是什么吗?”她看着我,眼睛里是碎裂的光,“是你的态度。每一次,你都让我忍。你说她是你妈,她不容易,她没有坏心。陈阳,没有坏心,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伤害别人吗?不容易,就可以成为不尊重别人的理由吗?”
“我嫁给你,是想和你组成一个新的家庭。可在这个家里,我感觉自己永远像个外人,像个需要被你妈时刻审查、改造的入侵者。而你,这个本该和我并肩作战的丈夫,却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推到她面前,让我独自承受。”
她的话,像一把把刀,插进我的心脏。我无力反驳。因为她说的,都是事实。
“我们分开一段时间吧。”最后,她平静地抛出这句话。
“不行!”我几乎是吼出来的。我无法想象没有她的日子。
“那你想怎么样?”她反问我,“继续这样过下去?直到我所有的热情和爱,都被消磨干净,然后我们变成一对怨偶吗?”
我沉默了。
就在我们僵持不下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我妈。
我犹豫着,接了。
电话那头,我妈的声音带着哭腔:“阳阳,你快回来。妈心里难受……妈喘不上气……”
我心里一紧,也顾不上和晓雯争执,拉着她就往家赶。
等我们火急火燎地赶到我妈家,却发现她好端端地坐在沙发上,既没有喘不上气,也没有任何不适的迹象。桌子上,摊开着一个本子。
看到我们进来,她指着那个本子,用一种极其悲凉的语气说:“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怕你们年轻人手松,不会过日子。我帮你们记了记账,你们看看,哪些地方是不该花的,以后注意点。”
我拿起那个本子。上面密密麻麻,用工整的小楷,记录着我们家近三个月的所有开销。从每一笔水电燃气,到晓雯买的每一件衣服,每一支口红,甚至豆豆吃的一根冰淇淋,都赫然在列。每一笔“不必要”的开销后面,都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叉。
晓雯买的那个翡翠镯子,被记录在最后一页,后面的那个红叉,画得力透纸背。
我拿着那个账本,手抖得厉害。这哪里是账本,这分明是一份起诉书。起诉着晓雯的“奢侈浪费”,也起诉着我的“识人不清”。
晓雯看了一眼,笑了。那是一种比哭还难看的笑。
她什么也没说,转身走到门口,打开门,回头看着我。
“陈阳,现在,你还要我忍吗?”
那一刻,我看着我妈那张写满“我都是为你好”的脸,再看看晓雯那张写满绝望的脸,我心里那个叫“孝顺”的堤坝,终于,彻底决堤了。
我走到我妈面前,把那个账本,一页一页地,撕得粉碎。
“妈,”我看着她震惊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们的日子,不用您费心了。从今天起,您过您的,我们过我们的。”
第三章:谎言
撕掉账本,我和我妈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我们搬了家。没有告诉我妈新地址。那是我第一次,对她撒了谎。我说公司外派,要去邻市待一年。她不信,闹了一场,说我不孝,说晓雯是,把她的儿子勾走了。我狠下心,挂了电话,拉黑了她的号码。
我知道这很残忍,但就像医生刮骨疗毒,不断臂,就得死。
新家不大,但很温馨。没有了无处不在的审视和评判,空气都是自由的。晓雯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她开始在阳台上种满了花花草草,周末的早晨,我们会一起做饭,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给她的侧脸镀上一层金边。那一刻,我觉得,为了这样的生活,之前的一切决绝,都是值得的。
豆豆也很快适应了新环境。她上了新的幼儿园,交了新的朋友。只是偶尔,她会冷不丁地问一句:“奶奶为什么不来看我了?”
每当这时,我和晓雯都会相视无言。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跟一个五岁的孩子,解释成人世界的复杂和无奈。我们只能告诉她:“奶奶身体不舒服,在家里休息。”
谎言,有时是保护,有时是更深的伤害。我们选择了前者,却没想到,它会以另一种方式反噬。
平静的生活过了大约半年。一天,我下班回家,看到豆豆坐在沙发上,怀里抱着一个崭新的芭比娃娃,正是我妈之前答应要给她买的那个限量款。
我心里猛地一沉。
“豆豆,这个娃娃哪来的?”
豆豆看了我一眼,眼神有些躲闪,她把娃娃抱得更紧了:“是……是爸爸你昨天给我买的呀,你忘啦?”
孩子的声音清脆,却像一声惊雷在我耳边炸开。我昨天加班到深夜,根本没有给她买过什么娃娃。
这是我的女儿,第一次对我撒谎。
我看向晓雯,她对我摇了摇头,示意我不要逼问。
晚上,等豆豆睡着了,晓雯才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原来,我妈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了豆豆幼儿园的地址。她每天下午,都会在幼儿园门口等豆豆放学。她不敢让我们知道,就偷偷地塞给豆豆各种零食和玩具,然后嘱咐她:“千万别告诉爸爸妈妈,这是我们俩的小秘密。”
今天这个芭比娃娃,就是我妈送的。豆豆太喜欢了,没忍住带回了家。为了不违背和奶奶的“约定”,她只能选择对我撒谎。
我坐在黑暗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愤怒、无力、还有一种深深的悲哀,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防火墙,被我妈用这种“爱”的方式,轻而易举地撕开了一个口子。她绕过了我,直接把“战场”转移到了我的孩子身上。
她在教我的女儿撒谎。她在用一种看似温情的方式,腐蚀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
“我们必须跟她谈谈。”晓雯的声音很冷静,但微微颤抖的手,暴露了她的情绪。
第二天,我们请了假,在幼儿园门口,等到了我妈。
看到我们出现,她先是一愣,随即脸上露出了那种熟悉的、委屈又倔强的表情。她手里还拎着一袋豆豆爱吃的草莓蛋糕。
“你们来干什么?”她把蛋糕藏到身后,像个被抓住了错处的孩子。
“妈,我们谈谈吧。”我拉着她,走到附近一个僻静的公园。
“我就是想孙女了,我看看她,犯法吗?”她先发制人,声音里带着哭腔。
“您想豆豆,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带她去看您。您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为什么要教她说谎?”晓雯忍不住开了口,她的声音在发抖。
“我说谎?”我妈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我那是跟孩子亲近!你们不让我见,我只能用我自己的办法!我疼我自己的孙女,有什么错?”
“错就错在您不尊重我们!”我终于忍不住吼了出来,“这个家,我和晓雯才是豆豆的父母!我们有权决定怎么教育她!您不能越过我们,把您的意志强加在她身上!您以为您给的是爱吗?不!您给的是负担,是让她在我们之间做选择的痛苦!”
“你……”我妈指着我,气得说不出话来,“你这个不孝子!为了这个女人,你连自己的亲妈都不要了!”
“我不是不要您!”我红着眼睛看着她,“我是想要一个正常的家!一个有边界、互相尊重的家!妈,您爱我,我知道。但您的爱,太重了,重得让我喘不过气,重得快要压垮我的家庭了。爱不是占有,不是控制,爱是得体的退出啊!”
“得体的退出……”我妈喃喃地重复着这句话,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她踉跄了一下,扶住了旁边长椅的靠背。
那一刻,我看到她鬓角的白发,在阳光下那么刺眼。她不再是那个无所不能、永远强势的母亲,她只是一个害怕被抛弃的、孤独的老人。
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
就在这时,我妈的手机响了。她颤抖着手,接了电话。是小姨打来的。
电话那头,小姨的声音很焦急,我隐约听到“医院”、“检查”、“不太好”之类的字眼。
我妈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她挂了电话,看着我,眼神里是前所未有的慌乱和恐惧。
“陈阳……”她的声音像游丝一样,“我……我可能生病了。”
第四章:病房外的走廊
我妈被确诊为乳腺癌,早期。
拿到诊断书的那一刻,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之前所有的争吵、怨怼、决绝,在“癌症”这两个字面前,都变得微不足道。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她是我的妈妈,她生病了。
住院手续是我和晓雯一起办的。晓雯表现得出乎意料的冷静和能干。她跑前跑后,联系医生,安排床位,没有一句怨言。我妈看着她忙碌的身影,眼神很复杂,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动了动嘴唇,什么也没说。
手术安排在三天后。那三天,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三天。
医院的走廊,永远弥漫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混杂着若有若无的焦虑。我和晓雯轮流守夜。白天,晓雯会煲好汤送过来,一口一口地喂给我妈喝。我妈很抗拒,说没胃口,晓雯也不勉强,就放在一边,等汤凉了,再去热,再端过来。
有一次,我妈大概是实在过意不去了,就着晓雯的手,喝了两口。然后,她偏过头,对我说:“陈阳,你出去一下,我跟晓雯说几句话。”
我心里一紧,以为她又要挑剔什么。我担忧地看了晓雯一眼,晓雯对我安抚地笑了笑,点了点头。
我走到病房外的走廊上,心神不宁。我靠着冰冷的墙壁,听着里面隐约传来的交谈声。我听不清她们在说什么,只能看到晓雯坐在床边,微微俯身,我妈躺在床上,侧着头。那个画面,竟然有种奇异的和谐。
过了大概十分钟,晓雯出来了。
“妈说什么了?”我急切地问。
晓雯看着我,眼神有些湿润。她说:“妈跟我道歉了。”
我愣住了。
“她说,对不起。她说她知道以前做得不对,太想抓住你了,反而把所有人都弄得很累。”晓雯吸了吸鼻子,“她还说,如果……如果她这次过不去,让我好好照顾你和豆豆。”
我的眼泪,在那一刻,决堤了。
我从没想过,骄傲了一辈子的母亲,会以这样一种方式,低下了她高贵的头颅。这场病,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海啸,摧毁了她所有的盔甲,露出了里面最柔软、最脆弱的内核。
手术那天,我们等在手术室外。红色的“手术中”三个字,像烙铁一样烫在我的心上。时间被无限拉长,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
小姨也来了,她拉着我的手,跟我讲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
她说,我爸刚去世那会儿,我才十岁。我妈一个女人,在纺织厂上班,白天踩缝纫机,晚上回来还要给我做饭辅导功课。有一次,我半夜发高烧,她一个人背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跑了三里地才到医院。她说,我妈这辈子,没为自己活过一天,她的世界里,只有我。
“陈阳啊,”小姨拍着我的手背,语重心长,“你妈这个人,嘴硬心软,爱的方式不对。她不是坏,她就是怕。她怕你娶了媳妇忘了娘,怕自己老了,没人要了。你……多体谅她。”
我听着,眼泪无声地往下流。我体谅她吗?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地站在她的角度,去理解过她的恐惧和孤独。我只看到了她令人窒息的控制,却没看到那控制背后,一个寡母对唯一的儿子,那种近乎绝望的依赖。
手术很成功。医生说,因为发现得早,癌细胞没有扩散,后续只要坚持化疗和放疗,治愈率很高。
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我妈从麻醉中醒来后,第一眼看到的是守在床边的晓雯。
她看着晓雯,嘴唇嗫嚅了半天,才发出微弱的声音:“水……”
晓雯立刻拿起棉签,蘸了温水,一点一点地湿润着她的嘴唇。动作轻柔,又耐心。
我妈的眼角,滑下了一滴泪。
我走过去,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冷,又干枯。我把她的手贴在我的脸上。
“妈,”我哽咽着说,“都会好起来的。以后,我们都在。”
那一刻,在医院苍白的灯光下,我们一家三口的手,第一次,真正地握在了一起。没有隔阂,没有怨怼,只有劫后余生的庆幸,和血浓于水的温暖。
我突然明白,有些墙,不是用来推倒的,而是用来开一扇门的。而这场病,就是那把打开门的钥匙。它让我们都看到了彼此的软肋,也让我们学会了,如何用一种更温柔的方式,去拥抱对方。
第五章:一碗粥
化疗的副作用很大。
我妈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吃什么吐什么,整个人迅速地消瘦下去,像一片被秋风抽干了水分的叶子。看着曾经那么强势、那么精神的母亲,变得如此脆弱,我心如刀割。
出院后,晓雯主动提出,把我妈接到我们新家来住,方便照顾。
我有些犹豫,我怕好不容易缓和的关系,会因为同住一个屋檐下,再次变得紧张。
晓雯看出了我的顾虑,她说:“陈阳,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她不是那个控制欲强的婆婆,她只是一个需要我们照顾的病人。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把她推开。”
我看着晓wen,心里充满了感激和愧疚。
妈住进了豆豆的房间,豆豆暂时跟我们挤一张床。小丫头很懂事,她说:“让奶奶住我的房间,奶奶生病了,要睡公主床才会好得快。”
妈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我们家的生活节奏。
晓雯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和照顾我妈的责任。她变着花样给我妈做吃的,南瓜小米粥,山药排骨汤,鲫鱼豆腐汤……都是些清淡又有营养的。可我妈胃口极差,常常是晓雯忙活了一上午,她只吃两口就再也咽不下去了。
“还是淡了点……”有一次,她喝了一口粥,皱着眉头说。
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生怕晓雯会不高兴。
没想到,晓雯只是笑了笑,说:“妈,医生说您现在不能吃太咸的。您要是觉得没味,我给您放两滴香油?”
我妈没说话,算是默许了。
晓雯转身去厨房拿香油,我看到她的背影,突然觉得有些恍惚。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如果是以前,面对这样的挑剔,晓雯可能会沉默,会隐忍,但那份委屈是藏不住的。但现在,她的脸上,只有平静和坦然。
我后来问她:“妈那么说,你不生气吗?”
她正在给我妈按摩浮肿的小腿,头也没抬地说:“有什么好生气的?她是个病人,病人有情绪是正常的。再说,可能是我做的确实不合她胃口。”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长大的不只是我,还有晓雯。她不再是那个会因为婆婆一句话就暗自垂泪的小媳妇,她变得更强大,也更宽容了。
化疗的痛苦,把妈的棱角都磨平了。她不再对我们的生活指手画脚,大多数时候,她只是安静地坐在阳台的摇椅上,看着窗外发呆。
有一次,我看到她戴着老花镜,在费力地研究豆豆的一本故事书。
“妈,您看什么呢?”我走过去问。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合上书:“没什么。就是……豆豆总让我给她讲故事,我怕我讲不好。”
我拿起那本书,是《猜猜我有多爱你》。
那天晚上,我看到我妈坐在豆豆的床边,用她那有些沙哑的嗓音,一字一句地给豆豆念着:“小兔子对大兔子说,我爱你,从这里一直到月亮那里。大兔子说,我爱你,从这里一直到月亮那里,再……绕回来。”
豆豆在她怀里,睡得香甜。
我靠在门框上,看着这幅画面,眼睛有点酸。我记忆中的母亲,永远是忙碌的,是严厉的,她会逼我做做不完的习题,会因为我考试没考好而大发雷霆,但她,好像从来没有这样温柔地,给我讲过一个睡前故事。
原来,她不是不会,只是她把所有的温柔,都藏在了那身名为“坚强”的铠甲之下。而现在,病痛卸下了她的铠甲,也释放了她的温柔。
关系的转机,发生在一个雨夜。
那天,我妈化疗的反应特别大,吐得昏天暗地。半夜,她突然开始发高烧。我们赶紧把她送到医院急诊。
折腾到凌晨,烧才退下来。医生说没什么大碍,就是化疗后的正常反应,注意观察就行。
从医院回来,天都快亮了。晓雯一夜没睡,眼睛熬得通红,却还在厨房里忙碌着,给我妈熬粥。
我妈躺在床上,看着她,眼神里充满了愧疚。
“晓雯,”她突然开口,声音很虚弱,“对不起。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晓雯端着粥走过来,坐在床边,舀起一勺,吹了吹,递到我妈嘴边:“妈,说什么呢?我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我妈重复着这三个字,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以前……我对你那么不好……我……”
“妈,”晓雯打断了她,把勺子又往前递了递,“都过去了。您先把粥喝了,养好身体最重要。”
我妈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她张开嘴,把那勺粥,喝了下去。
喝完一碗粥,她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她拉住晓雯的手,说:“晓雯,以后……这个家,你做主吧。妈老了,也糊涂了,以后都听你的。”
晓雯反手握住她的手,笑了,眼角却有泪光:“妈,这个家,不是谁做主。是我们大家一起,把它过好。”
窗外,雨停了。一缕晨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了进来。
我知道,我们这个家,天亮了。
第六章:老照片
我妈的身体,在晓雯的精心照料下,一天天好了起来。
化疗结束后,她又经历了几十次放疗。那段日子很辛苦,但她都咬牙挺过来了。她的头发,也慢慢地长出了一层短短的绒毛,像刚出生的婴儿。
家里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和以前那种死气沉沉的平静不同,现在的空气里,多了一种叫“温情”的东西。
晓雯会拉着我妈一起看她喜欢的电视剧,一边看一边跟她讨论剧情。我妈一开始还端着,说这些情情爱爱的没意思,后来也看得津津有味,还会为了男主角的选择跟晓雯争论不休。
豆豆成了她们之间最好的粘合剂。她会缠着奶奶给她讲故事,也会拉着奶奶陪她玩过家家。她给我妈安排的角色,永远是“最美丽的王后”。
一个周末的下午,我整理书房,无意中翻出了一个旧箱子。里面,是我家所有的老照片。
我把相册拿到客厅,我们三个人,加上豆豆,围坐在一起,一张一张地翻看。
有我穿着开裆裤,被我妈抱在怀里的照片。照片里的她,那么年轻,梳着两条大辫子,笑得一脸幸福。
“妈,您那时候真好看。”晓雯由衷地赞叹。
我妈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好看什么呀,那时候,又黑又瘦。”
还有一张,是我爸抱着我,我妈站在旁边。那是我家里,为数不多的,一张全家福。照片里的我爸,眉目英朗,看着我的眼神里,充满了爱意。
看到这张照片,我妈的眼圈红了。
“你爸要是还在,看到你现在成家立业,豆to都这么大了,该多高兴啊。”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照片上的人,像是在抚摸一个易碎的梦。
我默默地揽住她的肩膀。
晓雯翻到了下一页,那是一张我上大学时,我妈来学校看我的照片。在学校的大门口,她穿着一件不合身的旧外套,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笑得有些拘谨。而我,站在她身边,穿着时髦的牛仔裤,表情里,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不耐烦。
看着这张照片,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刺了一下。我想起来了,那天,我妈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硬座火车来看我。我带她去吃了食堂,她一个劲儿地说好吃,比家里的香。临走时,她塞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她几个月省吃俭用攒下的一千块钱。而我,送她到火车站,看着她挤上那趟拥挤的绿皮火车,心里想的却是,终于可以回寝室打游戏了。
那时候的我,是多么的自私和浅薄。我享受着她毫无保留的付出,却吝于给她一点点的耐心和温柔。
“这张照片……”晓雯看着我,眼神里有些复杂。
我低下头,声音有些沙哑:“那时候,我不懂事。”
“不怪你,”我妈却摇了摇头,她看着照片里的自己,像是看着一个陌生人,“那时候,是妈做得不好。我总觉得,我为你付出了所有,你就应该按照我给你设定的路走。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娶个我满意的媳妇……我把我的愿望,都强加在了你身上。我忘了问你,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她转过头,看着我和晓雯,眼神里是前所未有的清明和歉意。
“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把对你爸的思念,和我自己人生的不如意,都转化成了一种对你的控制。我以为那是爱,现在才知道,那是一种枷锁。不仅锁住了你,也锁住了我自己。”
“阳阳,晓雯,”她拉起我们俩的手,叠在一起,“妈对不起你们。以后,你们就按你们喜欢的方式去过。妈不掺和了。妈只想看着你们好好的,看着豆豆健康长大,就够了。”
客厅里很安静,只有相册翻页的沙沙声。窗外的阳光,暖暖地照进来,落在那些泛黄的老照片上,也落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上。
那一刻,我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彻底地放下了。
不是原谅,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需要原谅的。我们每个人,都曾被困在自己的角色里,母亲被困在“伟大”里,我被困在“孝顺”里,晓雯被困在“隐忍”里。我们都用自己以为正确的方式去爱,却弄得彼此遍体鳞伤。
而现在,我们终于从那些角色里走了出来,开始学着,如何以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人的身份,去爱另一个人。
第七章:晨光
我妈最终还是决定搬出去住。
这是她自己的决定。她说,病好了,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她说,她想过几天自己的日子。
我们没有强留。我们知道,这是她送给我们这个小家庭,最珍贵的一份礼物——空间和自由。这也是她送给她自己的一份礼物——独立和新生。
我们在同一个小区,给她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小房子。离我们很近,走路五分钟就到。
搬家的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惠风和畅。
我们没有请搬家公司,东西不多,我和晓雯一趟一趟地搬。我妈跟在后面,指挥着这个放哪里,那个放哪里,精神头十足,又恢复了当年那个“将军”的风采。但不同的是,她的指挥里,没有了命令,多了商量。
“这个柜子,放窗边行不行?我想在上面养几盆花。”
“晓雯,你看这个沙发套的颜色,配不配墙的颜色?”
晓雯都笑着说:“妈,这是您的家,您说了算。”
安顿好一切,已经到了傍晚。夕阳的余晖,透过干净的玻璃窗,给这个小小的屋子,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
我妈坚持要给我们做一顿饭,说是“暖锅”。
她做了她最拿手的鲫鱼汤。汤还是那么奶白,那么浓郁。她给我们每个人都盛了一碗。
我喝了一口,味道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晓雯也喝了一口,然后笑着对我说:“妈熬的鱼汤,就是比我的好喝,一点腥味都没有。”
我妈听了,脸上乐开了花,嘴上却说:“哪有什么诀窍,就是多放两片姜,多熬一会儿罢了。”
我看着她们俩,一个笑得真诚,一个笑得满足。我知道,那句曾经哽在我喉咙里,不敢说出口的真话,现在,终于可以坦然地摆在桌面上,变成一句温暖的玩笑。那股曾经弥漫在我们家,代表着隔阂与矛盾的“腥味”,也终于,烟消云散了。
吃完饭,我们陪她坐了一会儿。豆豆在陌生的环境里有些兴奋,跑来跑去。我妈就跟在她后面,嘴里念叨着:“慢点跑,别摔着。”
临走时,我妈送我们到门口。
她拉着我的手,又拉了拉晓雯的手,说:“快回去吧。豆豆明天还得上学呢。我这儿没事,你们不用惦记。”
我们走到楼下,我回头看,看到她还站在门口,冲我们挥手。楼道的灯光,勾勒出她瘦小的身影,显得有些孤单,但更多的是一种安详。
回去的路上,晓雯靠在我的肩膀上,轻声说:“陈阳,你知道吗?我今天,才真正地觉得,我有一个婆婆了。”
我握紧她的手,没有说话。但我知道,我也是。我今天,才真正地觉得,我有一个完整的家了。一个有爱,有尊重,有距离,也有牵挂的家。
第二天一早,我还是不放心,想去看看我妈。
我走到她家门口,正准备敲门,门却从里面打开了。
我妈穿着一身运动服,精神抖擞地准备出门。
“妈,您干嘛去?”
“我去公园跳广场舞啊!”她扬了扬手里的一个小组扇,“你刘阿姨介绍的,说可有意思了。我得去学学,不然以后连个伴儿都没有。”
我看着她,突然就笑了。
她也笑了,拍拍我的肩膀:“行了,快上班去吧。别跟个小老头似的,啰里八嗦。妈好着呢!”
说完,她就哼着不成调的小曲,走进了清晨的阳光里。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那个曾经用爱将我牢牢捆绑的背影,那个我一度想要拼命挣脱的背影,此刻,在晨光里,却显得那么的自由,那么的轻快。
我突然想起她在我爸照片前说的话。她说她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忘了问我想要什么。其实,我又何尝问过她,她想要什么呢?也许,她想要的,从来不是控制我的生活,而只是害怕,在我的生活里,彻底失去位置。
爱,从来不是一道是非题,而是一道关于距离的计算题。太远,会疏离;太近,会窒息。我们一家人,用了那么多年,付出了那么惨痛的代价,才终于,找到了那个最合适的距离。
我转身,迎着朝阳,向家的方向走去。我知道,一个新的故事,已经开始了。而这一次,我们每个人,都将是自己故事里,真正的主角。
文档上传者
热门标签
相关文档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